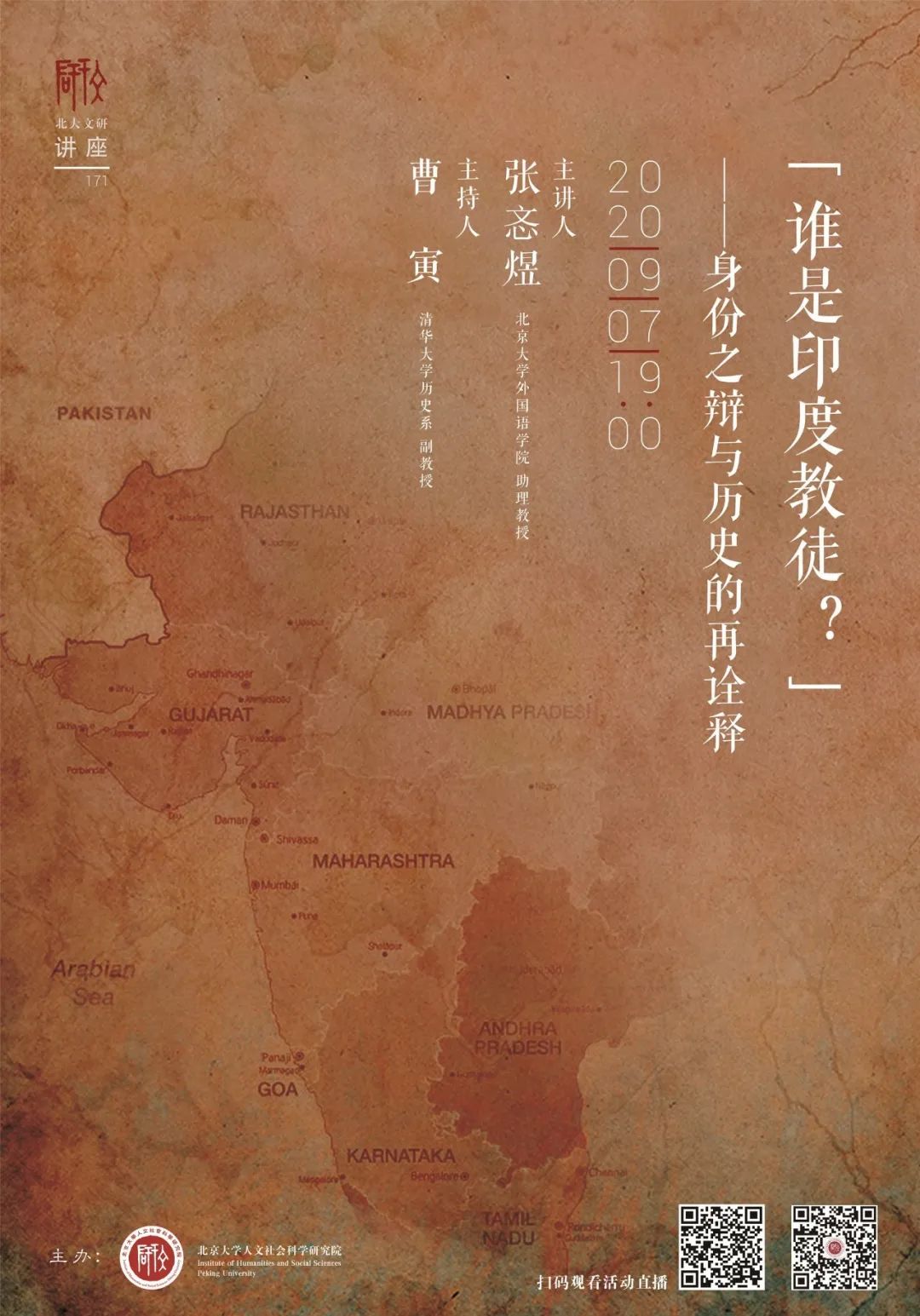
2020年9月7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七十一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谁是印度教徒?’——身份之辩与历史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主持。
谁是印度教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印度教徒身份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不同声音从各自身份认同出发,形成不同观点,并不断重新诠释印度历史,导致各种身份认同的严重对立。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宗教界、作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纷纷参与,模糊了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的界限。印度国内不同地区以及国内外的联动,又使争论成为一个多层次的知识现象。在本次讲座中,张忞煜老师首先回溯“印度教徒”(Hindu)这一概念的历史,探讨它来自古老传统抑或现代建构,进而介绍并反思印度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中的Hindu概念,最后探讨了印度身份政治与历史书写等重要问题。
从词源上讲,“Hindu”是伊朗语词,最初指“河”,后来特指“印度河”,再后来渐渐拓展到指称印度河流域(及以东)地区及居民。迄今为止,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古印度各地居民如此自称,更无法证明Hindu在古代曾被用作宗教信众集体称谓的情况。关于“Hindu”,过去两百年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出现于19世纪,认为“Hindu”不管作为“印度教徒”还是“印度人”,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身份概念。包括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等东方学家、殖民史学家、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及宗教研究者均持该观点;第二种观点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认为“印度教”(Hinduism)和作为宗教身份的“印度教徒”(Hindu)皆为19世纪欧洲东方学介入以来所建构的概念。该观点明显受到后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研究强调现代建构的影响。
近一个多世纪,印度史方面有不少新史料面世,尤其是铭文及地方语言文献。再结合以往受到较多关注的宫廷波斯语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1世纪之后,“Hindu”已具备族群身份认同含义,常与另一族群称谓“Turk”(突厥人)对立。而具有宗教自觉意识及身份认同的“印度教徒”概念的出现,则不晚于16世纪。宫廷波斯语文献主要反映的是印度穆斯林王朝的视角。11世纪后,波斯化的突厥穆斯林王朝进入印度次大陆,苏丹的宫廷文人创作了很多颂扬突厥人如何击败印度人(Hindu)的文学作品。穆斯林王朝的军事扩张被宫廷文人视同为伊斯兰教扩张,被征服的印度人则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敌人。此种宫廷文人以宗教征服为核心的王朝史叙事,长期影响了人们对印度历史的认知。另一方面,铭文及地方语言文献反映了印度拉其普特王公的视角。对印度王公而言,突厥人的到来不过是又一轮的“蛮夷入侵”,突厥人和波斯人、萨迦人、希腊人一样被称为“蔑戾车”(Mleccha)。能够抵御妖魔的上古圣王罗摩成为印度王公的崇拜对象,南印度的毗舍耶那伽罗王朝统治者便自称罗摩、印度人。可以说,突厥穆斯林为印度带来的不仅是军事征服,还有“突厥人”和“印度人”对立的身份认知。

拉其普特王公与入侵者战斗
穆斯林王朝统治印度次大陆,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治下的印度人到底属于什么行政类别?他们将印度人、犹太人、基督徒均视为受保护的顺民,纳税后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又是什么呢?穆斯林学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印度人在偶像崇拜上的分歧。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学者认为,印度人是“崇拜偶像的不信道者”,反对苏丹和印度王公、商人合作;较开明的观点则认为,印度人和穆斯林一样是“一神论者”,偶像崇拜只是帮助底层民众信仰神的一种方式。开明的穆斯林学者往往与婆罗门学者来往较多。可以说,16世纪对印度人宗教的开明理解,是一种基于婆罗门知识精英的印度教观。
但是,当时还存在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16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一定经济权力的下层人士开始不满足于低种姓的社会地位。例如出身于北印度低种姓纺织工家庭的穆斯林诗人格比尔便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理念和实践均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自己既非“Hindu”,也非“Turk”,而是以纺织工、蔑戾车或首陀罗自居。像格比尔这样新出现的宗教导师,在民间有很多支持者。综上可知,11世纪的突厥穆斯林入侵,令“突厥人”和“印度人”成为一组对立的族群概念。16世纪先后,“印度教徒”概念的雏形已经出现,可以从三个视角界定:从婆罗门的角度而言,印度教徒是敬婆罗门、守瓦尔纳行期法的人;在穆斯林知识精英的眼中,印度教徒是以婆罗门为代表的异教徒或一神论者;而低种姓学者认为,印度教徒是指以婆罗门为代表的高种姓,并不包过低种姓。
以上是宗教方面的情况,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政治和族群方面。根据梵文和铭文史料,16世纪后南印度基于语言、地域的族群认同超越了广义的“Hindu”认同,这与毗舍耶那伽罗帝国的衰亡密不可分。同时,北印度西部的拉其普特王公成为次大陆上以“Hindu”自居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17世纪,马拉塔人希瓦吉(Shivaji,约1630—1680)崛起,缔造了独立于莫卧儿帝国的马拉塔王国。能言善辩的婆罗门学者帮希瓦吉“重新发现”家族的族谱,证明其祖上是13世纪因穆斯林入侵而从拉贾斯坦南迁而来的拉其普特王公后裔,从而使希瓦吉家族成功“刹帝利化”,以此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原来服务于拉其普特的印地语宫廷诗人,在希瓦吉的赞助下,套用拉其普特王公颂诗的主题和形式,为其创作歌功颂德的叙事诗,这也在无形中为希瓦吉和拉其普特王宫之间建立起想象的联系。

希瓦吉(Shivaji,约1630—1680)
到了18世纪上半叶,宗教学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提升,莫卧儿—马拉塔战争在历史记忆中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战争色彩,一方是兼具世俗和宗教权威的皇帝哈里发,另一方则是将家族纳入“罗摩等上古刹帝利——拉其普特王公——希瓦尔家族”谱系的印度教王公。这是英国进入印度之前的情况。可想而知,英国殖民者面对的并非白纸一张。当时的东方学家,首先要吸纳印度本土的观念和实践,具体体现在司法行政领域的族群划分,即将印度人划分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成为之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被视为不同民族的源头。其次他们又接受了穆斯林的乌莱玛学者和印度婆罗门知识分子各自对印度历史、宗教的理解,将“伊斯兰征服”、“宗教战争”写入历史。这是英殖时期对印度传统的延续性一面。
当然还有另一面。以詹姆斯·密尔为代表的殖民史学,又有着与印度传统叙事不同的“殖民现代性”。密尔坚信,以功利主义哲学为指导,可以书写一部“批判性的历史”,其成果即三卷本的《英印史》。印度历史被密尔分为印度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英治时期三大阶段,他对印度教的态度非常负面。由于英国政府高效的行政管理、教育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逐渐培育出的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印度知识分子群体,殖民史学对印度历史的解读得以大范围传播。虽然《英印史》饱受东方学家的批评,但最终成为印度公务员考试的参考书,印度双语知识精英不得不通过密尔的书来了解自身历史。
于是,新兴的印度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加入了东方学家的批评密尔《英印史》的行列,并积极争夺对印度历史的解释权。1900年,国大党创始人之一的拉纳德(M. G. Ranade)撰成《马拉塔的崛起》(Rise of the Maratha Power),以著作的形式回击了密尔的殖民主义史观。密尔将英殖统治视为莫卧儿帝国的继承者,拉纳德则认为在以莫卧儿为代表的“外来穆斯林统治者”和英殖统治之间,还存在一个以马拉塔为代表的“本土印度教徒统治者”阶段。拉纳德力图避免将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视为对立的民族,而是强调一个动态的“民族塑造”的过程,即马拉塔帝国治下的民众,首先形成印度教徒民族(Hindu nationality),然后以其爱国精神感染穆斯林及其他人群,最终凝聚为真正的印度民族(true Indian nation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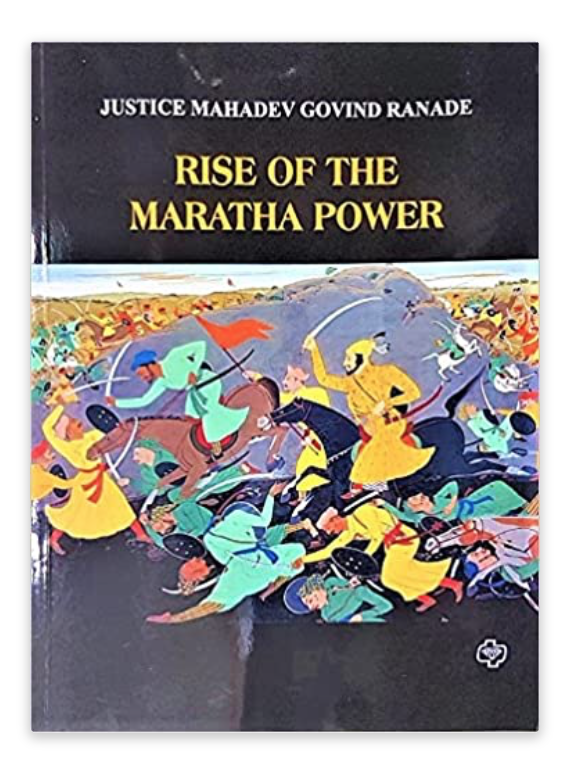
Rise of the Maratha Power 书影
1923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奠基人萨瓦卡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的《印度教徒特性的要素》出版,呈现了一种右翼的、保守而狭隘的历史观。他认为,印度教徒特性不等于印度教,后者应从属于前者。以印度为祖地和圣地的人方才是“Hindu”。从此界定出发,萨瓦卡尔重新诠释历史,他批评佛教使“Hindu”民族丧失尚武精神,强调种姓制度的重要意义,并大量引用所谓中世纪印地语叙事诗来赞扬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拉其普特王公和希瓦吉。
此外,印地语文学批评家也形成了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书写。如《格比尔集》编者希亚姆孙达尔达斯便重塑了格比尔的形象,宣称格比尔之所以主张“不拜偶像”,只不过是一种面对伊斯兰教冲击的权宜之计,目的是帮助印度教徒民族坚定信仰。修格尔的经典之作《印度语文学史》进一步以民族主义思想为基,将历史上有极大差异、来自不同阶层的思想家串联起来,构造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类似的历史书写及观念,深刻影响了主要受印地语教育的普罗大众。
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尼赫鲁,其《印度的发现》代表着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的“世俗民族主义”立场。但相对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尼赫鲁的历史观与其说是“世俗主义”,不如说更偏向多元主义。一方面,他强调印度文化的多元性,认为印度教并不等于印度文化;另一方面,他指出印度教内部也充满多样性,无法以特定教义来概括。
在对“Hindu共同体”的认知上,民族主义者强调印度教徒作为一个共同体。反对民族主义主张的主要有两个群体:认为阶级冲突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出身高种姓),与饱受种姓歧视之苦的低种姓和达利特(“贱民”)。两者都否认存在一个统一的印度教共同体,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种姓歧视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低种姓和达利特思想家虽然接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不满高种姓马克思主义者对种姓问题的回避,他们认为种姓矛盾包含阶级矛盾。印度独立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宗教身份认同问题,与民族主义史学针锋相对的还是低种姓和达利特的历史书写。
20世纪20年代,达利特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发起“最初的印度人运动”(Ādi Hindu Movement),主张“去印度教化”,认为包括达利特在内的被压迫大众才是“印度最初的居民”、“最初的印度人”,高种姓其实是后来的。这一“两种族论”,主要强调高种姓对低种姓的压迫和两者之间的对立。著名的达利特领袖、被誉为“印度宪法之父”的安倍德卡尔博士(B. R. Ambedkar,1891—1956)同样试图摆脱Hindu的身份,但反对“两种族论”,不认为首陀罗和达利特是非雅利安人,这两个群体只是因为与婆罗门的矛盾而被边缘化了。达利特学者及社会活动家不断挖掘被高种姓主导的主流文化叙事所遮掩的历史,推动了达利特史学的诞生。

安倍德卡尔(B. R. Ambedkar,1891—1956)
印度独立后,低种姓可以接受高种姓的教育,第一代达利特知识分子深受国内外左翼思潮影响,宣传建有马克思主义和安倍德卡尔主义的激进主张,形成“达利特大众”(Dalit bahujan)的概念——“达利特大众”包括首陀罗、达利特、部落民在内的一切受压迫者,属于“非再生族”,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瓦尔纳构成的 “再生族”才是“印度教徒”(Hindu)。达利特运动兴起之初,便与西方自由派保持密切互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训练、反对传统史学研究的精英主义的“庶民研究小组”较早关注到达利特运动。在西方受到良好史学训练的印度学者也将达利特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不仅重新探索以往被忽略的达利特运动史,还通过发掘地方文档、地方语言文献等新史料,推动了印度史的研究。拥有更加扎实的历史学研究背书的达利特大众身份认同,在今天印度身份认同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力量。
“谁是印度教徒?”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因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界定不同,“Hindu”存在三种不同的解读:约11—16世纪,“Hindu”被更多的表述为广义的“印度人”,和入侵的“突厥人”对立。某种意义上,当代右翼的多数主义在试图复兴这一解读;约16世纪以来,从地方语言文献可以看到来自印度教徒的解读,其中,从精英视角看来,“Hindu”是受婆罗门教法之人,而从大众视角看来,“Hindu”则是上层高种姓的宗教身份;现代政治语境中的“Hindu”主要有两种,19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主义者将“Hindu”界定为宗教文化共同体,而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发展的达利特大众批评,则认为“Hindu”是剥削大众的再生族。
最后,从“Hindu”概念的历史变迁这一具体事例,张忞煜老师讨论了身份政治对印度历史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爱说“印度没有历史”,然而如果深入探索第一手材料,学者有时反而会感叹印度有“太多历史”。和印度现代化历程相伴而生的是殖民地时期以来的身份认同政治,以及不同社群对自身历史书写的需求。随着历史变为平民化的知识生产活动,“身份认同导向的历史书写”成为一种常态。在历史书写方面,印度有两个特殊的情况:首先是多语种并行,不同语种之间互相联系又不尽相同,以英语发表学术论文的精英化的史学家共同体在将知识传递给缺乏英语教育的普通民众方面,未必能够竞争过更加了解地方语言和文化生态的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另类历史学家;其次则是历史研究的高度政治化,如近年来的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ICHR),由于政治的干预,专业的历史学家被迫让位于民族主义学者。自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印度的历史已不再是印度国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全球化的知识活动,东方主义、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潮与本土的政治活动和文献材料相结合,形成各式各样的历史书写。同时,印度的身份政治也不再是印度自身的问题,而是全球身份政治浪潮中的一朵格外引人注目的浪花。

张忞煜老师讲座直播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