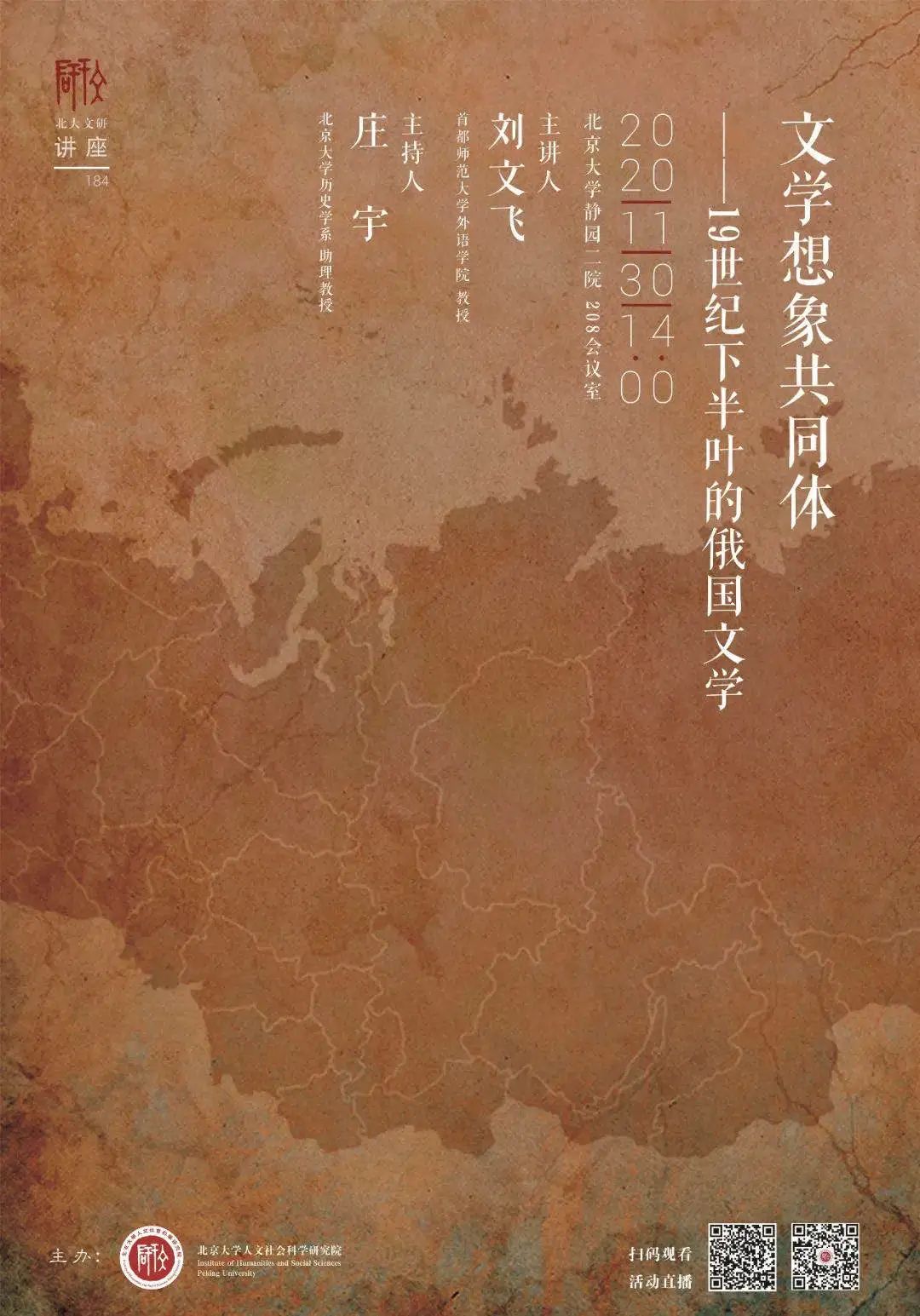
2020年11月30日下午,文研院“文明之间”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文学想象共同体——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主持。
围绕着“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这一主题,刘文飞老师从文学中心主义、俄罗斯性、批判现实主义、俄罗斯化、文学的想象共同体五个关键概念展开了探讨。
首先,刘文飞老师简要介绍了俄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溯源了文学中心主义出现在俄国的缘由,以及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原因。刘文飞老师指出,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具备广义与狭义两种内涵。 广义上,这个概念指文学在俄国的社会、历史与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有的、鲜见于其他国家的崇高地位,如诗人叶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所言:“诗人在俄国是大于诗人的。”狭义上,这个概念指文学同与之相邻的其他艺术体裁、门类相比而言,具备一种独领风骚的地位,这从列宾、柴可夫斯基等人对托尔斯泰所抱持的崇高敬意中可见一斑。刘文飞老师认为,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很可能就形成于19世纪中期,即始于普希金崇拜。普希金1836年去世后,莫斯科于1880年在市中心树立了普希金纪念碑,而在此之前,俄国拥有的只是帝王将相的纪念碑。从1799年出生的普希金到1828年出生的托尔斯泰,在30年之间,俄国文学的巨匠密集诞生,基本属于同时代人,结果是在1880年左右,整个欧洲对俄国的评价、认识与概括发生了从负面到正面的突转。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从普希金纪念碑落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各自演讲中不约而同、高度相近的主旨中可见一斑——二者均认为,俄国拥有了普希金这样的诗人,便意味着俄罗斯人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了文学、文化和文明,并因此可以骄傲地面对世界与欧洲。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俄国文学之腾飞背后的关键推动力,是当时的俄国作家们希望证明俄罗斯人是有审美情趣的文明民族这一共同情感诉求。
广义上,这个概念指文学在俄国的社会、历史与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有的、鲜见于其他国家的崇高地位,如诗人叶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所言:“诗人在俄国是大于诗人的。”狭义上,这个概念指文学同与之相邻的其他艺术体裁、门类相比而言,具备一种独领风骚的地位,这从列宾、柴可夫斯基等人对托尔斯泰所抱持的崇高敬意中可见一斑。刘文飞老师认为,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很可能就形成于19世纪中期,即始于普希金崇拜。普希金1836年去世后,莫斯科于1880年在市中心树立了普希金纪念碑,而在此之前,俄国拥有的只是帝王将相的纪念碑。从1799年出生的普希金到1828年出生的托尔斯泰,在30年之间,俄国文学的巨匠密集诞生,基本属于同时代人,结果是在1880年左右,整个欧洲对俄国的评价、认识与概括发生了从负面到正面的突转。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从普希金纪念碑落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各自演讲中不约而同、高度相近的主旨中可见一斑——二者均认为,俄国拥有了普希金这样的诗人,便意味着俄罗斯人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了文学、文化和文明,并因此可以骄傲地面对世界与欧洲。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俄国文学之腾飞背后的关键推动力,是当时的俄国作家们希望证明俄罗斯人是有审美情趣的文明民族这一共同情感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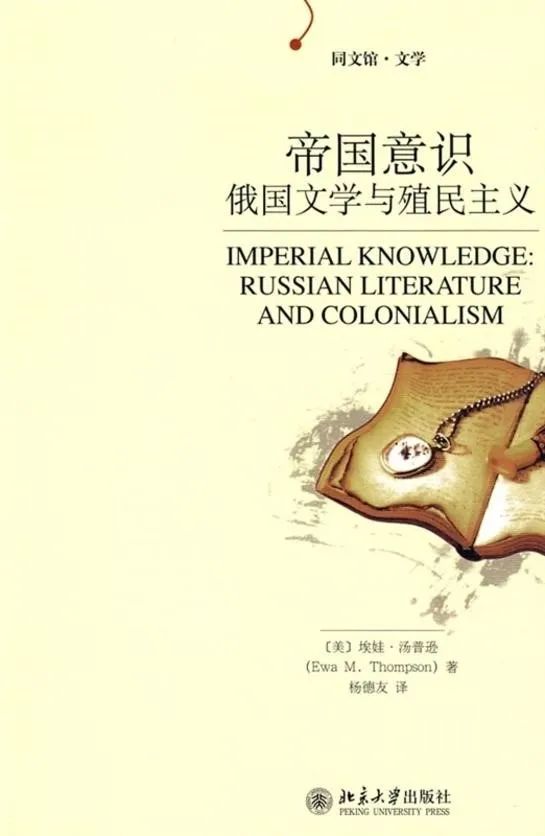 接着,刘文飞老师从俄罗斯性(Russianness)这一概念入手,展开第二部分的讨论。刘文飞老师指出,俄罗斯人具有丰富而鲜明的民族性格,包括高度的聚合性、忍耐精神、东正教的宗教感与使命感,以及慷慨好客、多愁善感等。其中,俄国民族性中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其极端性,即两极之间强烈的分化与对立,如刚与柔、粗与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与共存。而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也同俄罗斯性纠缠在一起,其间俄国文学高度关注对于俄罗斯性的探讨,并且主要着眼于俄罗斯性中相对其他民族而言的正面色彩。进一步讲,正如艾娃·汤普逊(Ewa M. Thompson)在《帝国意识——俄国文学和殖民主义》中所指出的,俄国文学中的殖民色彩与后殖民色彩在英语词汇“Russian”的三重含义中得到了鲜明展现,例如“Russian Writer”可以同时翻译为俄罗斯作家、俄语作家、俄国作家,而这个词汇本身同时包含了其民族身份、写作语言与国家归属的意涵。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在客观上将俄国中非俄罗斯民族的人与俄罗斯民族混在了一起,使通过文学表达出来的俄罗斯性具有了超民族(super-nation)、超种族的属性,俄罗斯性也因此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所追求的灵魂。
接着,刘文飞老师从俄罗斯性(Russianness)这一概念入手,展开第二部分的讨论。刘文飞老师指出,俄罗斯人具有丰富而鲜明的民族性格,包括高度的聚合性、忍耐精神、东正教的宗教感与使命感,以及慷慨好客、多愁善感等。其中,俄国民族性中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其极端性,即两极之间强烈的分化与对立,如刚与柔、粗与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与共存。而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也同俄罗斯性纠缠在一起,其间俄国文学高度关注对于俄罗斯性的探讨,并且主要着眼于俄罗斯性中相对其他民族而言的正面色彩。进一步讲,正如艾娃·汤普逊(Ewa M. Thompson)在《帝国意识——俄国文学和殖民主义》中所指出的,俄国文学中的殖民色彩与后殖民色彩在英语词汇“Russian”的三重含义中得到了鲜明展现,例如“Russian Writer”可以同时翻译为俄罗斯作家、俄语作家、俄国作家,而这个词汇本身同时包含了其民族身份、写作语言与国家归属的意涵。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在客观上将俄国中非俄罗斯民族的人与俄罗斯民族混在了一起,使通过文学表达出来的俄罗斯性具有了超民族(super-nation)、超种族的属性,俄罗斯性也因此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所追求的灵魂。
讲座的第三部分,刘文飞老师讨论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情况。整体上看,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作家创作手法中的主流,而以往的文学史往往会强调这些作家持不同政见、与政府相对立的冲突性特征。对此,刘文飞老师指出,实际上,19世纪下半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官方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呼应之处。例如,当时俄国作家批判现实的总命题是针对不完美的现实与优秀的俄国人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而展开批评,希望形成合力,让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值得尊重的国家,而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应如何设计”“俄罗斯人在世界上应扮演何种角色”这类问题,作家群体与沙皇的思路与抱负很可能是一致的。苏联时期所书写的文学史倾向于突出沙皇对文学家的迫害,而实际上,赫尔岑流放期间在流放地官至副省长,普希金离世后的五万卢布欠款更是由沙皇自行代其偿清。此外,如今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当时能够出版,就已经证明了俄国的书刊审查制度并非严格得密不透风。因此,当时俄国的文学、作家和沙皇、当局之间的对立,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尖锐。
在讲座第四部分,刘文飞老师讲述了俄国文学在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俄罗斯化”指用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来同化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进程。一方面,俄国文学具有强大的涵盖性,其中无论是作者还是塑造的人物,读者都很难看到俄罗斯人之外的种族形象。如汤普逊所说:“俄罗斯国家是多民族的,但是俄罗斯文学是单民族的。”因此,文学中存在一种悄无声息的俄罗斯化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俄国文学的广泛影响力,对于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聚居区,文学又在民族同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俄罗斯化的推动工具。在现在已经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联邦境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比如高加索地区,当地居民对俄罗斯人心怀不满的同时,又对普希金心悦诚服。马丁·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在《俄罗斯一千年》中提出,作为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俄国维持运转所依赖的主要驱动因素有三,即中央集权、军事扩张与东正教信仰。考虑到俄罗斯语言与文学在维护国家整体、塑造国家历史以及俄罗斯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刘文飞老师认为,俄罗斯语言与文学可以被看作与另外三者并置的“第四种因素”。
 最后,刘文飞老师围绕着俄罗斯“文学的想象共同体”这一概念展开讨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资本主义、印刷术、语言这三种要素加强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并恰好举了俄国语言为例:直到俄语地位得到确立、资本主义在俄国开始流通后,俄罗斯人才得以建构他们自己的想象共同体。以此为基础,刘文飞老师进一步指出,鉴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化通常被看作始于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而印刷术与图书发行在俄国的兴起也始于19世纪下半叶。如果将资本主义、印刷术和语言看作民族想象共同体形成的前提的话,那么俄国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只可能在19世纪的下半叶。此外,刘文飞老师认为,考虑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初衷、表达方式和所追求的目的,以及它在表达俄罗斯性、推行俄罗斯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俄国文学可以被看作俄罗斯人在19世纪下半叶构建自己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在安德森所言的“语言”之外,“文学”也是想象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因素。
最后,刘文飞老师围绕着俄罗斯“文学的想象共同体”这一概念展开讨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资本主义、印刷术、语言这三种要素加强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并恰好举了俄国语言为例:直到俄语地位得到确立、资本主义在俄国开始流通后,俄罗斯人才得以建构他们自己的想象共同体。以此为基础,刘文飞老师进一步指出,鉴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化通常被看作始于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而印刷术与图书发行在俄国的兴起也始于19世纪下半叶。如果将资本主义、印刷术和语言看作民族想象共同体形成的前提的话,那么俄国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只可能在19世纪的下半叶。此外,刘文飞老师认为,考虑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初衷、表达方式和所追求的目的,以及它在表达俄罗斯性、推行俄罗斯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俄国文学可以被看作俄罗斯人在19世纪下半叶构建自己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在安德森所言的“语言”之外,“文学”也是想象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五个概念的探讨,刘文飞老师在结论中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潮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积极的互动关系,两者相互抱合、互相塑造,构建了俄罗斯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学的,它一方面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持续的塑造作用。这种“文学的想象共同体”戴有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具,充当了俄罗斯化的有力工具,借助对俄罗斯性的阐释和构建,最终导致了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使俄罗斯人在19世纪下半叶构建了一个关于本民族的审美乌托邦。最后,刘文飞老师表示,作为来自异族的读者与研究者,面对俄国文学、尤其面对作为俄罗斯人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文学时,既不应采取完全崇拜的态度,也不应带有傲慢或偏见,而应该带有充分的警觉和少许的批判,以平视的方式进行阅读与研究。唯有如此,方可获得更为丰富的收获与发现。
基于以上五个概念的探讨,刘文飞老师在结论中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潮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积极的互动关系,两者相互抱合、互相塑造,构建了俄罗斯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学的,它一方面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持续的塑造作用。这种“文学的想象共同体”戴有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具,充当了俄罗斯化的有力工具,借助对俄罗斯性的阐释和构建,最终导致了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使俄罗斯人在19世纪下半叶构建了一个关于本民族的审美乌托邦。最后,刘文飞老师表示,作为来自异族的读者与研究者,面对俄国文学、尤其面对作为俄罗斯人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文学时,既不应采取完全崇拜的态度,也不应带有傲慢或偏见,而应该带有充分的警觉和少许的批判,以平视的方式进行阅读与研究。唯有如此,方可获得更为丰富的收获与发现。
评议环节,听众向刘文飞老师踊跃提问。对于俄、德两国在构建民族文学的过程中从民间搜集素材的路径异同,刘文飞老师认为,当时的俄国在文学、艺术上借鉴法国最多,在科学上、学术上则借鉴德国为重,例如先前讨论的“俄罗斯性”这一概念,很可能也是从费希特所提出的“德国性”借鉴而来。18世纪下半叶,德语文学的兴起部分得益于当时德国作家有意识地向民间故事汲取养分的尝试,而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认为俄国文学对这一路径存在着借鉴与学习。例如,托尔斯泰、普希金笔下的正面形象往往同俄国的“根”与“自然”存在关联,俄国文学中的许多童话亦可在西方民间文学中找到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