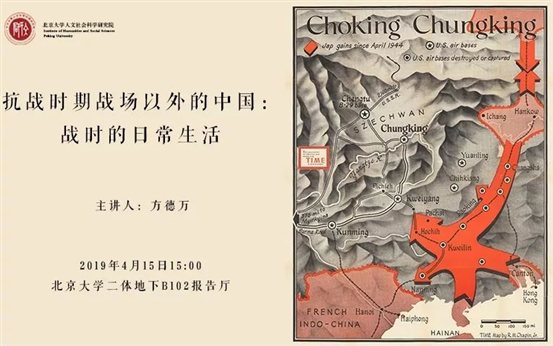
文研讲座120
2019年4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剑桥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学院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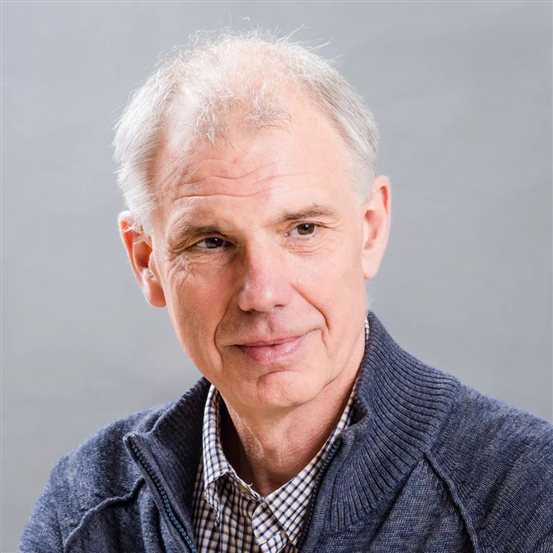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
讲座伊始,方德万教授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二战中日本投降中国的具体时间是何时?对于“1945年9月9日9时”这个答案,方德万教授解释了蒋介石给出这一时间点的两点考虑:一是“9”这个数字所表达的寓意,二是他意图将日本投降与一战停战协定的签署时间(1918年11月11日11时)联系起来,以表明中国战场是世界战场的一部分。投降仪式隐藏着相当丰富的细节。比如,冈村宁次是何应钦留学日本时的同窗,蒋介石派何应钦接受投降书的目的是向国人表明何应钦并非投降派。再如,日本当时在中国尚有大量军队,为什么选择参加这个仪式?为什么选择投降给蒋介石而非中共?事实上,从日军司令部和东京的电报中,我们可以获知,日方这样做一方面出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未来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中日贸易,投降蒋介石更可靠;另一方面,日本视苏联为战后的最大威胁,如果要敌对苏联,则不应与中共合作。但胜利者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国民政府的主要部队相当腐败,与其说是胜利者“要求”日本投降,不如说是胜利者“需要”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之后,人们的情绪普遍高涨,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但是一片欢乐气氛之中也有例外,这体现在一些日记和回忆录当中。例如齐邦媛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9月9日,她参加完庆祝活动回家后,便想起了自己的男朋友、已牺牲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不由得悲从中来。方德万教授希望用这个例子表明,此时,人民对未来的态度依旧迷茫。人民在战场以外的思想状态与精神史有密切关系。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中已经揭示:战争与人民的感觉息息相关。如果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么它必然会失败。因此在二战中,英国、苏联等国的领导都进行社会调查以掌握民情。

讲座现场
历史研究者不能将战场和战场之外的社会分开。方德万首先以两位精英阶层的代表为例,陈克文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日记以及齐邦媛的回忆录。陈克文生于广西,毕业于广州师范大学,早年对国民革命非常热心。抗战前他在南京居住了十年左右,1935年进入行政院任职,此间对国民政府的未来持极其乐观的态度。陈克文交游广泛,与戴季陶、梁漱溟、曹禺等人都有往来。国民政府在重庆时,这些精英阶层表现得非常活泼,流连于咖啡厅等娱乐场所,这是战时重庆的一个侧面。陈克文的阅读面很广,涉及俄国小说、达尔文的理论、曹禺的戏剧、冯友兰的新理学等等,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阶层。不仅如此,陈克文还曾翻译过一本历史教科书,其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欧洲的历史是从贵族和新教镇压下慢慢解放的历史,而在解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因是知识分子。所谓“进步”的过程,就是普通人民变得自觉、自由。这也是陈克文对中国当时状况的看法,秉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脉络。然而抗战开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他激烈批判孔祥熙的腐败,认为一旦中国战败,孔祥熙便是罪大恶极的元凶。直到1949年蒋介石请他前往台湾时,他拒绝了这一要求。陈克文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固然与之在内战中的最终失败有关,但这样的转变在抗战初期便出现端倪——他在南京前往武汉的过程中,便对国军撤离有所不满,他认为军队应该留下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

齐邦媛
齐邦媛笔下的历史则呈现了另一种样态。齐、陈二人在年龄与身份方面差别很大。国民政府在重庆时,陈克文已有40余岁,齐邦媛却还是个在南开中学上课的女学生。她热爱中国文学,熟读《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红楼梦》,也熟悉现代诗人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作品,对俄国文学、法国文学都青睐有加。中学毕业后,齐邦媛进入了武汉大学,当时的老师是朱光潜先生。齐邦媛最喜爱的还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等人的作品。这说明当时的大学继续保持着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对接,这和战争成王败寇的伦理截然有别。齐邦媛认为,中国正在牺牲一部分青年人来抵抗日本,但是也在保护一部分青年人来传承教育,让文化得以延续至未来。齐邦媛自己便是后者中的一员,她战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除了在台湾身体力行地从事教育外,她写回忆录的目的便是要把战争的记忆带给当代的青年。
除了以上二位的日记和回忆录,方德万教授还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史”类教科书相当流行,教育部要求学生务必修中国通史的课程,也受到了很多学生的欢迎。学生接受中国史教育、历史学家编写教材,两方都经历了一个对中国史性质和价值重认识和重新思考的过程。然而。历史学家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们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走到后方,缺乏编写教材的资料。另一方面,笼罩在30年代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也对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


钱穆(左)与雷海宗(右)
钱穆和雷海宗是历史学家中的两位突出代表,二者在抗战前都研究中国史。抗战影响了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史的感觉,这一点在二者的代表作中有所体现。钱穆接受的是传统中式教育,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撰写《国史大纲》时,常怀有“最后的中国人写中国史”的恐惧感。他以比较的方法对比西方和中国的历史,认为西方的进步是在战争和革命时期,中国的进步是在和平时期;西方的文明是军事化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是和平、稳定而进步的文明;西欧有典型的封建制度,中国则很少有封建制度等等。钱穆更认为,历史要获得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平时期地方区域的积累,革除积弊,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权力集中。与之针锋相对的是雷海宗,他强调中华文明的恢复仰赖强有力的领袖,且中华文明必须有军事化的过程,必须有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也正因此,雷海宗所属的“战国策派”常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雷海宗还批判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更不主张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分期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认为,由最初到公元4世纪左右,这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而由公元4世纪至今,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中国经历了抗战,中国文明也许还会恢复,这便是第三个复兴的时期。与以上二者不同,被称为“历史学派斗争最后的胜利者”的范文澜,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范文澜认为历史有客观的规律,当然,这一规律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最后,方德万教授指出,在欧洲、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来了解老百姓的态度。但在中国推行类似的社会调查的困难在于,老百姓的识字率较低,而报纸的报道又不一定客观,这给历史学家研究战场以外的底层百姓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以说,应当综合利用佛寺道观等场所的材料、日本对中国战时经济的掌握情况等多方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

王奇生教授(左)作评议
评议阶段,王奇生教授总结道,方德万教授本次的议题非常有价值。后人看历史往往已知历史的结局,在回望抗战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乐观的滤镜,这与亲历者当时的感受很不一样。陈克文的日记显示,他直到1944年都不知道战争何时才能结束,丝毫没有乐观感。包括抗战前期的陈寅恪、胡适等人,也都抱着悲观的态度。王奇生还提及了《王鼎钧回忆录》,与齐邦媛一样,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学生的生活。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教授有半数以上加入了国民党,如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就曾经担任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主委。至1944年左右,知识分子亲国民党的倾向有了明显的转变,失望情绪高涨。王奇生教授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需要关心战场外的日常生活,还需关心战场上的日常生活。如抗战时期的师长丁治磐,他的日记就反映了一位国军将领在战时最关心的问题——草鞋、逃兵等等。而这些情况又可以与国民党基层政权、征兵制度串联起来,同样也是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讲座最后,方德万教授与王奇生教授就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问题、大学生参军问题、中国近代音乐史等方面与在场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