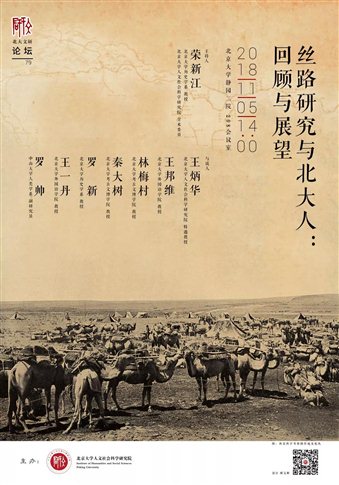
文研论坛|第79期
2018年11月5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丝路研究与北大人”专题展览正式开展。当天下午,来自北大历史学系、外国语学院、考古文博学院、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老中青学人齐聚静园二院,参加由文研院举办的 “丝路研究与北大人:回顾与展望”论坛。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炳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段晴教授、王一丹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研究员罗帅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荣新江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缘起和与谈学者的情况。他定义这次论坛不仅仅是各位学者探讨研究成果的平台,也应是诸位学者分享研究和考察心得的平台。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 王炳华
王炳华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在新疆考古第一线工作40年的经历和心得。他指出,从新疆考古发现来看,丝绸之路的存在并不明确,它更多地是一个观念上的存在,但这一观念所反映的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实际。远古时期,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中心都有独具特色的物产,这些物产吸引了其他文明的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文明之间早期交流的形式。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变迁使欧亚大陆人口流动加剧,承载着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人”的流动推动了欧亚大陆早期文明相互交流。王炳华教授认为,人的交流是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口流动的研究能够深化对丝绸之路的了解。
接着,王炳华教授指出,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的西传并非始于西汉,天山峡谷和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发掘出的、带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特性的丝绣、铜镜、漆器等能够证明:早在战国和秦王朝时期,华夏文明就通过这条概念上存在的道路自发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了交流。而到了西汉以后,这种自发的状态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从好的方面来讲,政府的管理保证了后勤的供应和沿途的安全;但同时,在政府管理之下,统治者会在交流中追逐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并因此导致与异己者的矛盾,例如汉王朝和匈奴对新疆地区的争夺、唐王朝和高昌及西突厥的矛盾冲突等等。精神文化的交流有时也会导致冲突的出现,如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势力的更替等等。在此基础上,王炳华教授指出,丝绸之路之上并不只有玫瑰花,更多的是血与火。满怀诗意的文化交流的背后有着非常尖锐的非文化性冲突,这些都是做丝路研究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1979年,王炳华教授在新疆古墓沟遗址发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古史中心教授 罗新
罗新教授随后分享了自己在丝绸之路上的足迹。他分享了自己在年轻时期和王炳华教授一同环行塔里木盆地、探寻新疆诸遗址,并在此过程中聆听其讲授的经历。罗新教授感谢王教授对自己之后的研究,尤其是对蒙古高原研究的深远影响。
接着,罗新教授对我国的中亚研究史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我国中亚研究曾受制于时代,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诸多研究者真正地走到中亚,在跨国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而到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中亚研究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已有成果的前提下,罗新教授认为,我国的中亚研究实际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日本、欧洲相比积累有限,且少有学者能够掌握多种语言,解读多种史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应当进行一些只有中国学者才能完成的特别研究。具体而言,罗新教授建议道,中国的研究者首先要真正置身于所研究的区域,获得实地的史料。其次,应当掌握足够的语言工具,最重要的是要利用旧有成果,结合多重文献,寻找过去文献中的可疑之处,从而展开新颖的研究。对此,罗新教授举例进行了说明:他自己在研究中发现关于中亚的诸多记载中都没有鸟类的踪迹,同时在耶律楚材写于中亚的诗中最多的字是“寂”,似乎他在中亚的生活中很难听到鸟的啼叫声,这和古代中亚温暖湿润的气候状况有所矛盾。这一情况反映的问题在之前就没有人研究过,类似这样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应当被研究者们所注意。

2006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古突厥阙特勤碑遗址合影。前排左四罗新,右二张帆。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教授 王邦维
王邦维教授就学科的发展史发表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丝绸之路研究在北大由来已久,在较早的时期被称为西北史地研究、边疆研究、中外交通研究等等。北京大学之所以较早关心丝绸之路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清末民初诸学者的家国情怀和学术追求。清末民初的丁谦、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陈垣等老先生就是这些先驱的代表。王邦维教授指出,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研究者受到了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西方学者的刺激,较早地介入到了西北研究之中,中国西北调查团的考察研究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一时期史语所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阶段是抗战时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有以向达先生为首的一大批学者不计成本地坚持进行西北考察。第三阶段是抗战结束后到六十年代文革之前,这一时期研究的条件仍旧相当受限,政治环境也阻碍了学科发展,但有《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蛮书校注》等一系列研究成果问世,向达、宿白等具有战略眼光的老一辈学者都在这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耿世民教授、张广达教授的研究以及《大唐西域记》的校注等等都是相当前沿的成果。
王邦维教授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北大学术是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的。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当前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国外,但仍存在着一些缺陷:语言学习不够、研究积累不足、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以及对各部族历史的研究不足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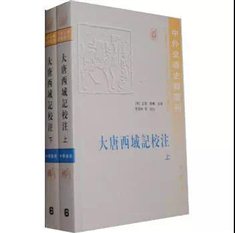
季羡林先生主持、王邦维等参与的《大唐西域记校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林梅村
林梅村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历程。他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因该年中国史专业没有招生而进入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学习了梵语并进行了大量的出土文献研究,1994年在季羡林教授和宿白教授的引荐下重回北京大学任教。
林梅村教授接着分享了近期考古学界的大事件和由之引发的思考。在最近青海都兰古墓热水墓区破获了一场盗墓大案,盗墓者共盗走了600多件金器,这些金器能够反映出都兰地区吐蕃、吐谷浑以及汉族文明的交融,这一发现也证明曾被认为是粟特国的何家村的考古发现如今也确定有很大一部分是吐蕃和西突厥的。林梅村教授还举了郑芝龙航海图、英国学者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收藏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文化的例子以说明未来的研究方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阿尔泰山西侧的,在C-14检测下时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古代文化,这里的青铜文明很发达,且青铜的锻造工艺和铸造工艺同时存在,通过对这一文化的研究能够发现中国早期的青铜文明受到了史前丝绸之路上其他文明的影响,能够帮助解答中国青铜时代的谜题——青铜器铸造为何跳过了锻造阶段,而直接进入了较为先进的铸造阶段。林梅村教授以自身的研究经历建议我国的学者要在西文期刊上发文章,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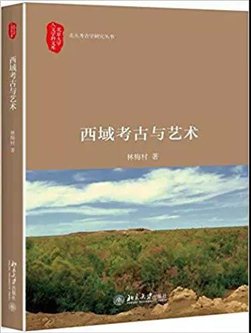
林梅村著《西域考古与艺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教授 段晴
段晴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强调:语言研究和丝路研究也是密不可分的。她指出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概念。例如印度一词就由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共同构成,伊朗在古代也是一个文化和语言概念,和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概念的区分需要语言学的介入。
段晴教授随后将自己的研究感悟分别进行阐述:首先,对古代的研究和对未来的预测一样,都充满着不可知和奇迹。其次,她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有很多误区和束缚: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会认为“会书写的文明就是伟大的文明,而不会书写的文明一定就相对落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书写只是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比较适合于统治,但文明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第二个误区是我们的研究常常过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认为古代周边各文化都是蛮族,经常忽略掉诸如斯基泰人(Scythians)为代表的其他伟大民族。这也使得我国文明的探源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被限制在了二里头文化之内,这是相当不可取的。
段晴教授认为,在历史学界,尤其是边疆史领域的研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破除“大宋疆域观”,既要把清明上河图看作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也要把新疆考古发掘的地毯同样看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段晴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的研究依旧很艰苦,不仅要破除诸多束缚,而且要掌握大量的语言,要打破和中亚南亚间的鸿沟般的文化差异。段晴教授强调说,语言学是一门相当严密的学科,现在北大的语言布局已经比较完备,有能力应对接下来研究中的挑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 王一丹
王一丹教授从波斯语和伊朗学学术史的角度进行讲述。她首先阐述了波斯语和历史系的渊源以及波斯语系的系史。早在北大东方语言学系成立之前,历史学系的邵循正教授就已经开始使用波斯语研究蒙元史,随后的张广达教授也用了波斯语去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中亚史。而独立的波斯语系直到1957年才成立,早期波斯语系的专业传统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一致,比较重视语言文学的研究。在此期间,波斯语系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波斯语的文学名著、对文学进行研究和译介、编撰《波斯语大词典》。真正系统地进行伊朗学研究则迟至九十年代才开始。
在伊朗学研究的创建中,叶奕良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90年成立了北大伊朗学研究所,并呼吁伊朗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要扩展为一个关于古今各种讲伊朗语的地区的学问。1992年,叶奕良教授主办了第一届“伊朗学在中国”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此后每五年举办一次,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学科传统。除此之外还组织了多次赴伊朗考察,也是在叶教授的带动下,形成了跨学科、跨国界合作的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是伊朗学在北大发展中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
王一丹教授接着展望了伊朗学研究的未来。她认为,伊朗研究当前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打通伊斯兰化之前和之后的界限,只研究了伊斯兰化之后的东西,只看到了波斯语的材料,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都没有被关注到。未来的研究方向就是要克服这方面的局限。

2012年,叶奕良、王文融夫妇与王一丹、荣新江在伊朗霍尔木兹考察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研究员 罗帅
罗帅副研究员分享了从北大早期丝路研究中获得的感悟。首先,北大的丝路研究一开始就源于北大人的爱国精神,他们的研究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主权,现代的丝路研究也应当具有足够的现实关照。其次,北大早期的丝路研究很注重实地考察,这值得敬佩和学习。再次,向达先生为丝路研究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他组织实地考察、编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研究兼顾海路和陆路……这些工作为北大之后的研究定下了基调和架构,后辈学者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罗帅副研究员对未来丝路研究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要拓展实地的工作,多在国外建立一些考古和研究基地;其次,要加强丝绸之路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实现从丝绸之路研究到“丝绸之路学”的推进;最后,要拓展年轻人才的学识和视野,建立新思维,从而突破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束缚。
讨论环节,在场听众和诸位学者首先就丝绸之路中的文学研究问题进行了探讨,荣新江教授表示,现今对丝路文学的研究较少,未来应该对这方面进行更多考量。林梅村教授回答了关于都兰墓葬发掘的提问,他认为,从都兰的新发掘可以看出,吐蕃的金银器工艺要优于唐朝,且受汉文化影响较少,更多地承接了两河流域的文化积淀。
论坛最后,荣新江教授表达了“在回顾中展望”的期许,希望能够通过回顾北大与丝绸之路研究的过往,推动未来在北大,乃至北大之外丝路研究的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