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同期其他邀访学者,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大历史学系陆扬、苗润博等出席并参与讨论。以下为虞云国老师的报告提纲。
一、历史观:“本人是倾向多元论的”
历史观可谓是史家的灵魂。刘子健认为:历史实相已然逝去,无法再现,而造成历史的因素复杂多元,过程驳杂纷繁,后人不能通过重演或试验来观察历史。至于史学研究所取资的史料不过是各种形态的纪录,充其量“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不是全貌”。

虞云国老师在讲座现场
既然借助史料记录获知的历史,不能据为定论,自然引出与历史观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史学是否属于科学范畴?其二,史学的功用是什么?刘子健认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
正是立足于史学并非科学,只是测度的根本立场,刘子健反对一元论的历史观。他指出:解释历史,“只有多元的互关性,没有一元的决定性”;各因素间“只有相对的重要,没有绝对的重要”。相对于一元论的历史观,他主张多元论的历史观。他提倡对历史作多方面与多角度的研究,认为任何研究结论都不是定于一尊的独断论。这种反对一元论与独断论的历史观,直接影响到他的史学方法。在他看来,史学研究就是不同史家的多方推论与比较综合,应该具有兼容性。他还别出机杼地翻用盲人摸象的寓言,讨论过这种兼容性。
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在刘子健看来,史学研究必然具有开放性。基于多元论,他明确反对史学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与不易之论,主张史家论点“不必等到研究完成才发表”,应该仿效现代科学,“研究正在继续,就提出报告,已经是相当普遍的惯例”;这样,“在研究正进行中,就可以得到指正,建议和启发,有助于研究”。在史学研究中,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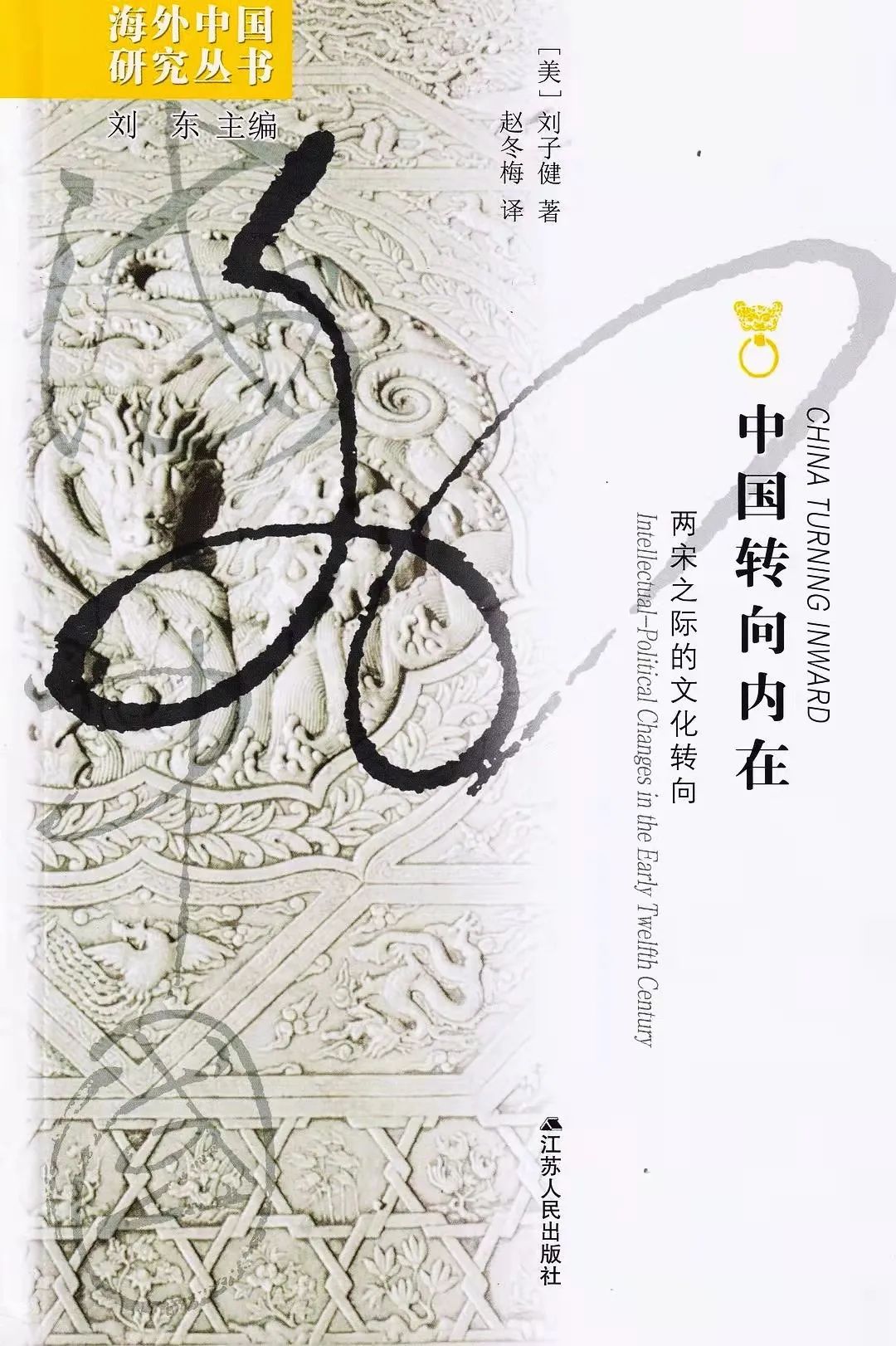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多元论的历史观让刘子健史学充满了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力于多元史观的开放性启示,他认为,“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得出了两宋之际政治文化转向内在的大判断。
既然史学研究只是一种测度,其中既蕴涵了史家对历史的一种看法,也必然投射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某种关怀。在刘子健史学里,这种关怀表现得尤其灼热。他提议史学界应抽出力量研究传统文化中能适应现代潮流的东西,而“探讨活的国史,动的通史”,正是历史学家不容推脱的责任。在研究中国文化中的信仰时,他就试图为现代化的社会道德与社会信仰推论出两项原理。强调多元复合、新旧复合,反对一元化倾向,是其推论的立论基础。根据研究所得,刘子健呼吁:“理想的文化,端在一与多,谋求平衡”,也表达出他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关切与隐忧。这种现实关怀体现了刘子健的价值观,是其多元论史观的自然发抒。在《中国转向内在》里,他研究的是中国为何转向内在的历史课题,关注的却是中国如何不再转向内在的现实问题。
二、 学问:“首先要学会提出问题”
刘子健是战后首批留美的华裔学人,很早便留心美国文史上的各种治学方法,并且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上。他相当重视史学方法,认为应该随着时代往前走,尝试新路子。他将史学方法分为沿用的方法、创用的新法与借用的看法。所谓沿用的方法,即既有的传统考证方法。所谓创用的新法,即西方近现代史学新开出的方法,但他对西式的方法并不盲从与迷信。他倡议中国史家应该结合中国史料的特点,在方法论上,向其他各国提示自己新贡献。在史学方法上,刘子健更擅长“借用的看法”,也就是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观点与分析方法移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
在史学方法上,刘子健有过一段总论性的精彩阐述,其中的“因题制宜”与“因问求法”,强调的都是提出研究问题的头等重要性。尽管在他所有探讨史学研究的论述中,未见有“问题意识”的夫子自道,但他却是把“提出问题”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他明确表示问题在前,方法在后,同时批评那种只知学习而不知发问的倾向。他认为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应该在问题形成后再去寻找与探讨。他还以西方科学为例,说明所有伟大发展都是从“问”出发的。
刘子健认为,提问题应该注意一要大,二要新。对史学问题的大小两种类型,他有独特之见。至于新问题,则往往是原先研究所忽略的边缘性问题。大问题与新问题完全可以也应该统一。
如何才能提出有意义的大问题与新问题,刘子健认为,一是指科际整合,二是指比较研究,三是指多元史观。他以前辈史学大家为例说明了解决史学大问题的意义。他自己也确实善于提问题,而且善于提大问题与新问题。大问题提出后,他主张可以有三种做法。
三、“先建议一个分析的格局”
刘子健认为,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步。第二步亟需解决的是构建一个看待问题的架构,他有时也表述为“分析的格局”或“分析模式”。他认为,推进史学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对既有史料的考订与整理,一是对既有史实提出新的分析与新的综合。他本人更推重后者。先建议一个分析的格局,有两个好处。但史家建构的“分析模式”,既非唯一的,又不是定论。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同的史家尽可以提出各自的分析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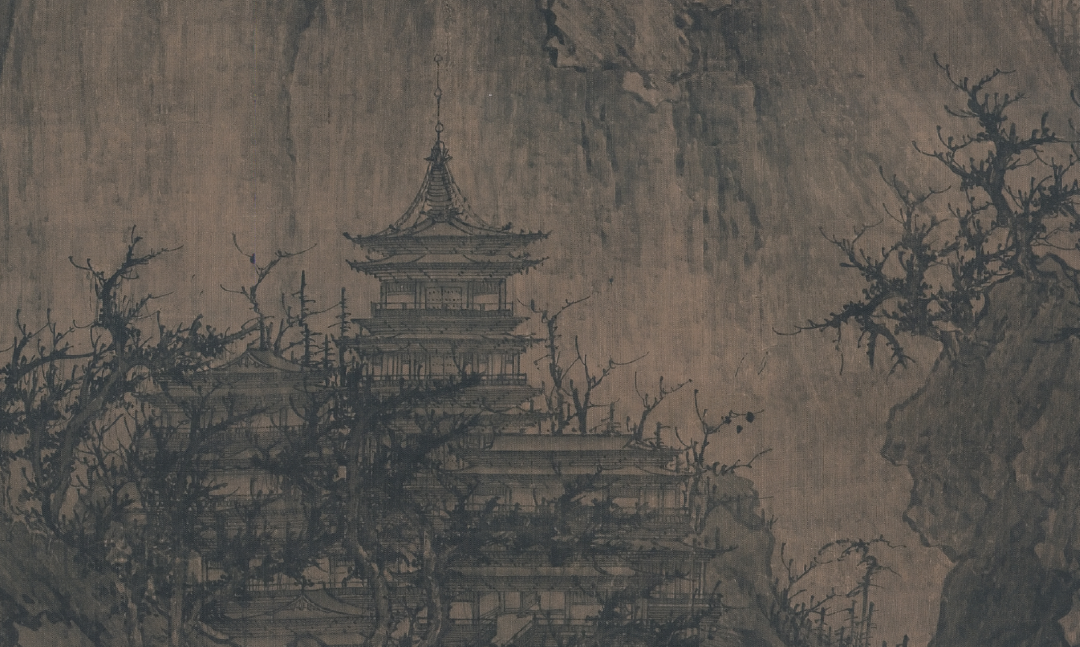
(宋)李成《晴峦萧寺图》(局部)
绢本设色,111.4cm×56cm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
如何才能出色地构建分析模式呢?刘子健主张以多学科触类旁通的思维与视野去探寻适合特定问题的分析模式。他自己在研究中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及其新政》《封禅文化与宋代明堂祭天》等。在研究南宋政治时,他借助政治学方法,提出了“包容政治”的命题,并将其推展到其他领域。
刘子健认为,史学研究融合社会科学多学科方法有两种作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制度史与政治史,故尤擅借助行政学的理路去建构分析模式,这当然因为政治与制度的运作与国家行政关系最为密切。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刘子健提示他们应该知道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与思考方式,注意辅助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帮助。
四、模式与类型在分析的格局中的作用
在运用“分析的格局”探讨具体问题时,刘子健注重不同层级的分类操作,其用意在于从纷繁的史实中寻找出特殊目标。他曾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例说明分类的作用。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刘子健认为,分类体系应该也可以是多元的。他指出旧史家的分类构想的主观性与公式化,损害了史料价值,强调要尝试一种新的分类方法。
这种新分类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模式与类型两种层级。他有时候也有欠严密地把类型表述为模式,但很显然模式囊括问题的广度与深度明显超过类型。提出新模式或新类型时,必须首先定义其内涵。在《王安石及其新政》里,他将北宋晚期的官僚划分为各种大类型,其下再细分若干小类型,都要言不烦给出类型概念的基本界定。
刘子健在分析的格局下创建的模式,是用来把握宏观大问题的,模式显然属于最高层级的分类。这里所说的模式与他有时将“分析的格局”也称作“分析模式”不是同一范畴,而是从属于“分析模式”的。他在研究中提出的这类模式主要有两个:一是“南宋文化模式”,二是君主官僚政体的运行模式。他一再审慎说明,分类模式只是方便研究的一种参照。另外,他还提过“国家被异族所征服,而汉文化延续不衰”的中国历史模式。
在具体研究中,刘子健更多区分不同集合的类型。例如,中国历史上信仰体系的四种类型,北宋君主权力运用及其应对困难表现的四种类型,南宋式乡绅的新类型,等等。他在对官僚士大夫的类型区分上,尤其别出机杼,并且取得应该设定相关的条件。在他看来,以标准的多元化与特征的相对性尝试划分官僚类型,“不过是一种新方法的试验”。这种新分类方法的试验在他那里是得心应手的。为了区别主导国家官僚系统的文官,他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底层吏役划为吏役次官僚的特殊类型,深入分析了这一类型在王安石新政中如何决定行政部门实际运营,并导致新政失败的。

(宋)赵佶《听琴图》
绢本设色,147.2cm×51.3cm
故宫博物院藏
五、史料批判与历史写作
刘子健对史料学有独特之见,最大特点就是批判性解读与运用,杨联陞称赞他“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
在史料上,刘子健主张从基本史料入手。他提出,史料搜集也有经济学上的报酬递减律,这既与刘子健素所遵行的从大处入手的历史观有内在关系,也与他客居美国时期纸本史料的分布现状有关,后人不应误读与误解成他漠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刘子健对个案研究也持类似见解。针对应否多做个案研究再作归纳,一个个案能否对大问题作出结论等质疑,他明确主张,历史研究同样应该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这里显然也适用报酬递减律。他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对宋代士大夫进行研究,也只集中于几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作为不同类型的典型个案,提出申论,作出解释。
刘子健的历史论著写作,其弟子概括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一,论旨明确,开门见山;其二,取材精审,懂得割爱;其三,谋篇布局,紧凑严密;其四,文字精简,锻炼传神。

虞云国老师受聘文研院“访问教授”
在开放多元的历史观的主导下,刘子健在史学方法上将善于发现与提出史学领域的大问题与新问题置于学问的首位;然后根据问题,因问求法,建构一个最适用既定问题的分析的格局;在运用分析的格局时,史无定法,借鉴一切可资利用的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善于引入模式与类型等多层级的分类概念,帮助分析问题与解释问题;在批判性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在历史写作中贯彻论旨明确、取材精审、组织严密与文字精简等原则,完成超越前人启发来者的史学论著。这就是刘子健史学的精髓与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