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研讲座139 2019年9月20日下午,“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讲本场讲座从当前贸易摩擦中的一个细节说起。在美国政府不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部分企业实施技术断供的背景下,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并不欢迎互加关税、禁止或限制科技交流与贸易——他们合作应对来自国家行政权力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很多美国企业都在想办法分担关税或绕过法令障碍寻求解决方案。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一案例启发我们意识到全球化其实存在两个本位:一个是由政治家、政府所构成的国家本位,另一个则是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所构成的市场本位。这两个层面并不符合同一逻辑,需要区分开来研究思考。
基于这一思考,周其仁教授在讲座中依次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讨论了全球经济开放过程中小国的带动作用;第二部分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组织、国家政府所发生的重要变化;第三部分讨论了市场竞争的输赢与发生贸易战之间的内在逻辑;第四部分重点回应了如何应对贸易战的问题。
在第一部分关于“开放与大国小国”的讨论中,周其仁教授指出,贸易战是在全球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微乎其微,就不会有贸易战,而回顾战后的全球贸易与经济的格局,可以发现当前的开放局面最开始是由一些小国率先开放所带动起来的。
讲座第二部分,周其仁教授指出,只要放开行政力量对贸易来往的限制,形成全球性的市场,各国就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当然,这背后也伴随着产业组织方式、国家政府职能的重要变化。首先,各国企业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的专业性和效率。这些公司无论其母国大小,只要能够经营全球市场就有成长为跨国经营、体量庞大的全球公司的潜力。诸如荷兰、瑞士、丹麦等国土和人口体量非常小的国家都拥有不少知名的全球企业,它们与大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结果并无二致。再如,华为公司的快速发展也是改革公司适应全球化、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的结果,这是当代企业组织变革中的殊途共归。
其次,“市场拓展无远弗届”。企业的生产不再是国界内的行为,每天全球来往频繁的各种水陆空运输方式将全球各地资源连接在一起。公司经营、产业组织、商品生产早已超越了国界,构成了所谓的全球供应链。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依然非常清晰且严肃,但是这些政治建构越来越为人们的来往服务、提供便利。今天的国家政府不仅仅是发挥传统上保护国内秩序的职能,还要参与全球治理、来往贸易、跨国家治理。上述现象说明,在交易定理、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这些基本的经济底层逻辑起作用的情况下,人类连接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总全球化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来自于竞争,但是市场竞争并不总意味着双赢。在第三部分的讨论中,周其仁教授认为,市场竞争只有在“签约”的情况下才会双赢,而没有合约情况下的竞争就会产生输家。对于市场竞争中的输家而言,有两种行为策略应对失败:一种是反求诸己、提高生产效率再次参与市场竞争,另一种则是集结起来诉诸政治权力,限制、惩罚市场竞争中的胜出者。比如上世纪80年代,江西省政府一度封锁赣粤省界,打击粤商高价收购江西农民猪肉。国内各地区之间尚且会发生贸易摩擦,在缺乏全球政府协调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就更容易出现争端。
“通而不平”的全球化是国际贸易、经济甚至部分政治冲突的根源。“通”带来全球范围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平”则带来摩擦和冲突。作为先行者的工业区(比如美国的“锈带”地区)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很容易被具有比较优势的后发者所超越,当这些地区转型、再学习不力的情况下,就容易成为反对贸易、反对全球市场的政治力量,并可能支配国家的政治意志引起国际之间贸易冲突。
面对这些冲突与麻烦,周其仁教授在第四部分的讨论中指出,正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贸易战没有赢家,也不可能有赢家,应对贸易战的办法只能是摆脱它。各国都有维护本国意识形态、保护本国利益的本能和冲动,一旦进入相互对抗的漩涡,不断推动贸易战的升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会造成冲突局势与大众情绪的失控。所以,贸易战是无法打赢的。单边自由贸易策略是摆脱贸易战的一个可能的途径,这意味不用等待达成双边协定,而是通过本国单方面的降税减税来撬动其他各国跟随打破关税林立的局面。贸易战与军事活动不同,主动加税的主要结果并不是对对手的打压而是对本国利益的损害,减税才能吸引全球的技术与资源富集,进一步促进本国的发展。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战后有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是主动降低关税的,在经验上支撑了单边自由贸易策略。
面对着特朗普政府的高度不确定状态,周其仁教授认为,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协议的达成。因为国家政权之间达成协议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且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被动等待
此外,周其仁教授还指出,华为的案例也启发我们不能只盯住政治主体的行为,还要关注市场主体的行为。在当前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和组织也在通过海外建厂、启用“技术备胎”、寻找替代等手段,重新连接市场,突破贸易战带来的限制和障碍。
最后,周其仁教授总结道,在当前一段时期,国家层面的全球化进程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还会非常顽强地向前推进。从长期来看,来自上层建筑、国家权力的力量不会比底部的力量强。真正强大的力量是无数普通人的经济利益,是各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是人们的交流来往和互通互联。他认为,这些底部的力量才是未来的确定性和希望所在。
讲座提问环节,关于如何看待《美国工厂》纪录片的问题,周其仁教授表示,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工厂选址的做法是错误,最终还是要由企业根据比较优势来确定,特朗普政府缺乏能够真正干预美国企业回国的实际手段。对于如何评价“进口替代战略”,周其仁教授指出,“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的情境下是合理的,也是战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能够使得国家拥有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但是,这样的战略具有先天的弊端,不利于生产效率提高、人民富裕和经济增长。中国建国初期就是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培养起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转向了开放。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回应进口替代战略的问题,以提升自己的经济效率。任何一个政策都是利弊具备的,不能因为一个政策的长处就长期忽视其短处——执行时要充分研究如何结合替代政策以化解其内在矛盾和问题。
(撰稿:包堉含) |


.png)

 从历史来看,大国一般会比较保守,倾向于选择走关税保护下进口替代之路,美国、德国、巴西等国都曾经通过关税保护来促进国内的工业化发展。依靠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扶植国内产业发展的做法,在二战后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潮流中成为了一项主导的经济政策。
从历史来看,大国一般会比较保守,倾向于选择走关税保护下进口替代之路,美国、德国、巴西等国都曾经通过关税保护来促进国内的工业化发展。依靠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扶植国内产业发展的做法,在二战后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潮流中成为了一项主导的经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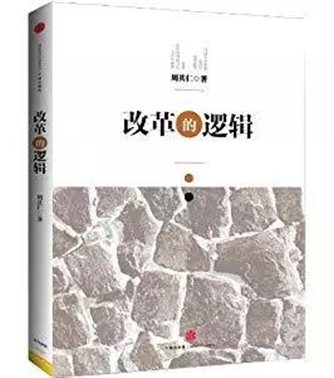 会对市场预期和投资造成较大的影响,最终损害自己的经济发展。在美国以外,中国还有广阔的全球市场,正如欧洲日本已经达成了零关税协议那样,中国可以选择主动与欧洲、
会对市场预期和投资造成较大的影响,最终损害自己的经济发展。在美国以外,中国还有广阔的全球市场,正如欧洲日本已经达成了零关税协议那样,中国可以选择主动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