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6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米歇尔·福柯《性史》(1978)”。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讲座伊始,基恩教授回顾了前两讲的核心要点。他表示存在两种颇为不同的政治观:第一种以施密特为代表,认为政治是一个追求权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定义盟友和敌人,并牵涉抗争、暴力、军队和警察,最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谁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是一种新霍布斯主义式的理解;第二种是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式政治观,认为政治并非暴力、敌人、战争这些对立性因素,而是关乎如何处理由个体以非暴力形成的公共群体所产生的权力问题,并涉及权力的分配问题,最终需要回答的是如何追求好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基恩教授认为,福柯的政治观与上述两种均不同。本场讲座中,基恩教授希望能通过《性史》来引出第三种政治观以澄清西方语境中的“政治”(politics)概念,并启发对自身所处语境的思考。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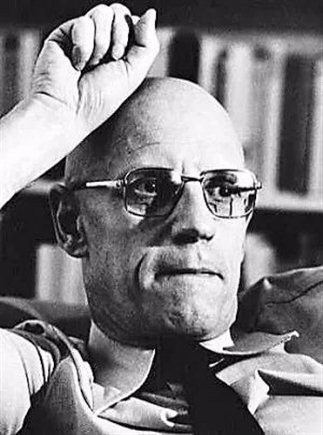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
福柯生于1926年,于1984年患艾滋病去世。1969年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去世。除《性史》外,他还著有多部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等等。福柯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从1970年代开始为边缘群体的权利发声,并出现在妇女运动、人权运动等各类社会运动中。他本人是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性史》自我思考的产物。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在该书中的观点也被时人简化为“人本身就是政治的”这一广泛流传的口号。
基恩教授表示,福柯在《性史》中的研究方法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萨特作为理解其思想的背景不可或缺。不只是在研究兴趣上类似,福柯对自己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强的批判,但他对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思考持怀疑态度,从而拒绝了萨特式的主体特权——他称之为“先验自我”。其二,从《词与物》中就体现出的“回归语言”(the return of language)在《性史》中延续了下来,语言成为他研究的重要对象。受索绪尔启发,福柯认为,人讲话的过程就是展现主体性的过程,而语言本身又与知识关系密切。其三,他对于历史学的批判性思考。在其早期作品中,福柯提出了考古学(archaeology)方法,主张回到过去,通过深挖过去的结构来理解古代语境中的人的塑造方式。之后,他认为这一方法存在缺陷,不能很好地解释一种话语如何向另一种话语转换的问题。于是,福柯又提出了谱系学(genealogy)方法,目的在于检视语言的结构,进一步考察权力、知识以何种方式塑造了人类过去的生活。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批判了“性压抑假说”(repressive hypothesis)。当时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过去的人们羞于谈论性和身体,性行为也不能作为餐桌上的主题,即使一位年轻女性怀孕也不能谈论。简而言之,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性一直是被压抑的,即身体和人们对于身体的欲望受到权力的压制。但福柯认为,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
从18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西欧社会并非如此。在福柯看来,“性”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不断出现在各种话语中,如基督教忏悔仪式中对性细节的大量描述以及心理学对年轻男孩或女性的诊断。这些都是知识不断介入的过程,人们试图探寻性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关于性的新术语不断被发明,例如对同性恋的分类、恋兽癖等等,直到最近发明的LGBTI(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人士)。现代西方社会并非在压抑性,而是对性始终抱有热情和幻想,关注性并试图对其进行分类,最终发现了关于性的“真理”。
基恩教授继而谈到,为了进一步挑战“性压抑假说”,福柯认为有必要构思一种新的“权力本质”(the nature of power)来澄清性与压抑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现代形式的权力不必然在本质上压抑性,而是主体生产性的,所以才声称“在政治思想和分析中,我们依然没有砍掉过国王的头”。当谈及政治和权力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国王、王后、有权力的人和国家。正如施密特所认为的那样,政治和暴力、夺取生命有关,政治强迫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然后人们使用暴力反抗。
但从性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关于政治和权力的观点并不成立。福柯列举了四种性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女性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的教育化、生育行为的社会化、性倒错的精神病学化。这些对权力提供了全新诠释:其一,每个人的全部生活,从卧室到战场,都充斥着权力关系,没有人能够逃脱;其二,权力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它既是一种垂直关系,也是一种水平关系;其三,权力会侵袭所有人并限制人们的活动,没有什么在权力之外。
总之,“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它拥抱一切,而是它来自一切”。无论我们在讲话、投票还是工作,权力都在每个人的一切关系中起作用。这意味着当我们谈及身体和性时,同样也无法脱离权力。我们的身体、我们表现出的性态、我们从接吻中获得的快感都在权力之中。权力可以塑造人的认同、塑造人的身体。施密特认为权力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因为有权力的人可以夺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阿伦特则认为当人们成为公共的一份子时才会产生权力,而谈及身体也只是强调劳动属性。与二者不同的是,福柯认为人类的身体才是我们理解权力和政治的核心。

约翰·基恩(JohnKeane)教授
主体权力的观念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人们会说“一个人很有权势”、“我没有权力”或者“川普拥有权力”等等,但这些是对权力的误解。权力往往将自己隐藏起来,制造出伪装、沉默和隐秘的假象。作为一种关系,权力无处不在,它没有内部也没有外部,存在于所有组织中。即使是最小的权力,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资本国家中,权力限制身体,但也可以因此被改变。而就性来说,各种性态并非给定的,是可以改变的,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追溯的自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身体的就是政治的”。在后来的系列演讲“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生物政治的诞生”(1978-1979)中,福柯用“治理”(government)代替“权力”(power),以“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作为分析权力的合理性、技巧和支配(governing)的手段。
基恩教授强调,若以这种政治观重新看待性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性政治”。《性史》是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运动的批判。人们当时认为,性是自然和健康的,只要摆脱来自于文化道德、社会经济的束缚,就可以获得性解放。但福柯认为,这些人误把性当做对抗权力支配的方式,而忽视了权力的无所不在——即使那些带有抵抗意味的性活动也仍有权力因素在运作。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还区分了东西方对于性的不同理解方式。与西方对性进行分类、限制和分析不同的是,在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社会中,性被视作一种艺术。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允许或禁止某种行为,性快感也不是服务于真理和科学的。
但基恩教授还指出,福柯在第一卷中并没有谈及理想中的“性政治”,而这也是读者特别希望了解的问题。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自我的呵护”中,福柯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像阿伦特一样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却发现古希腊人一方面通过道德规则对性进行自我限制,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外部约束而实际上相当宽松。希腊人的性活动很开放,《会饮篇》里提及有年轻男孩参加的酒会、异性恋、同性恋、婚内婚外恋;但同时又强调恰当克制的必要性。希腊人的性活动不受政府的约束,可以说是自由的。但福柯认为,比道德规则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呵护。在希腊罗马人看来,性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要以身体的美和通过别人获得的快感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可以说,这对希腊人来说已上升到“生存美学”的层面。
这一点对福柯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福柯肯定了这种关系,并通过《性史》为一种新的政治观奠定了基础,即身体的政治学与个人的政治学。他既没有写人们吃的食物,也没有写人们穿的衣服,更没有写人们因环境破坏所遭受的个人危机,但他提醒每一个人都可以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中。不应存在一种单一的性规则,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还是跨性别者,每个人都可通过对自身身体和他人的练习达到对自我呵护。在尊重他人时,政治变成了对身体的关注已经对自我的呵护。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意义上的自我呵护,从而有益于让每个人获得幸福生活。
讲座现场
讲座最后,基恩教授强调了福柯对“革命”的批判。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一起追求新秩序固然是好的,但福柯批判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那种以军队、警察为对象来反抗统治权力的做法。往往,这种反抗所面对的是一种易变的、暂时性的力量,且最终只会在商业贸易、大学和其他组织中制造社会裂痕。基恩教授表示,按照福柯的权力观,真正的反抗应是网状的:人们紧紧围聚在一起,且每个人都在其中抵抗“生物-权力”(bio-power)——人们正是在这些权力组织中求生存的。理解政治意味着身体、自我关系以及在和他人关系中的自我呵护。这也是福柯对于政治的第三种理解至今依然如此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