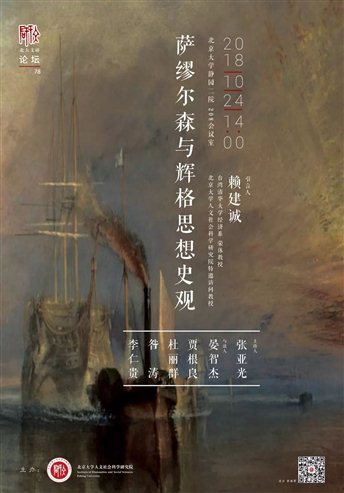
文研论坛 |第78期
2018年10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萨缪尔森与辉格思想史观”。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赖建诚作引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晏智杰、杜丽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出席并参与讨论。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是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不仅于1970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还一生躬耕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讲坛,培养了数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1961年,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讲演中发表了关于运用辉格史观进行思想史研究的见解,引起了学界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高度关注。经济学家的思想史观问题,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
论坛开始前,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向赖建诚教授颁发了特邀访问学者聘书,并对赖建诚教授两个月以来的来访交流表示感谢。赖建诚教授高度评价了文研院严谨踏实的治学氛围和兼容并包的研究气质,并对文研院给予的学术关怀和支持表示感谢,并期待未来能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向赖建诚教授颁发特邀访问学者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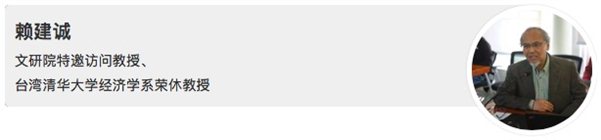
论坛伊始,赖建诚教授首先介绍了该主题的缘起。他指出,萨缪尔森是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但其思想史研究成果却鲜少受到关注。1946至2007年间,萨缪尔森发表了近百篇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论文。就数量而言,比绝大多数思想史研究者一生所发表的篇数还多;就质量而言,大多发表在重要期刊。除这些论文外,萨缪尔森还完成了约60篇有关知名经济学者的传记评论。这些文献都是系统性分析萨缪尔森思想史研究贡献及方法论的珍贵材料,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探讨。近年来,《剑桥经济学刊》有关萨缪尔森辉格史观的评述专刊、牛津大学出版的萨缪尔森两卷本传记,说明了经济学界、思想史学界对萨缪尔森观点洞见的重新追溯和审视。

萨缪尔森文集原版书影
(Paul A. Samuelson.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M]. M.I.T. Press, 1966.)
接着,赖建诚教授简要介绍了辉格史观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内涵。这一术语最早起源于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辉格的历史诠释》,基本观点是将历史看作一系列由落后迈向先进、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不可逆的进步故事,亦称“绝对主义”或“理性重构”。在思想史研究中,辉格史观表现为运用现代概念、观点和方法重塑过去的思想论断,力图厘清思想由谬误迈向真理的历史脉络,使之成为更正确、更能为当下服务的思想。与之相对的则是“相对主义”或“历史重构”,强调思想观点与其所在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配套性,倡导回归原有的历史环境,设身处地地考察思想提出的真正指向和意涵。
赖建诚教授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萨缪尔森运用辉格史观进行思想史研究的评价。他指出,萨缪尔森是一位极其高产的经济学家,以至于其出版商都不得不承认“很难跟上他的生产速率”。但通览其有关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分析理路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对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的论断,他都倾向于将所研究的经济理论赋予现代意义,即直接运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加以嵌套,而对思想本身的内容及时代意义着墨太少,甚至并不在意。尽管他周密完整的数学定性和逻辑推理为数理经济分析方法铺就了康庄大道,吸引了许多有自然科学基础的学者参与其中,但却遭到了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广泛批评。就连萨缪尔森本人也坦陈:“当我在天堂遇见圣彼得时,我最严重的罪行,就是采用辉格史观研究科学史。”赖教授认为,萨缪尔森的做法,正如西方谚语中对“工具主义”的批判那般:“当你手里拿着一把铁锤时,你看到的都是钉子。”单一的辉格史观或死板的数学分析抛弃了思想观点背后的个人成长背景、社会和时代特色,致力于追求形式美感和逻辑完整性,是买椟还珠、削足适履之举,难以真正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而注重时代差异和文化背景的历史重构方法,才能更真实地理解历史论断的本来面目,把握思想观点的精髓所在。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赖建诚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晏智杰教授对赖建诚教授的评述表示赞成。首先,萨缪尔森的思想史观问题是大陆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学界)历来忽视的一个命题。虽然萨缪尔森所著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在专业教学中影响广泛,但学界对他的自述及思想史研究却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因而,这一命题可谓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其次,辉格思想史观的核心内涵是以今论古,把既定的思想方法套在古人身上,使之演变为现在的面目。倘若从这一角度认识,那么,这一史观是否对国内经济思想史界,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研究产生过影响?这一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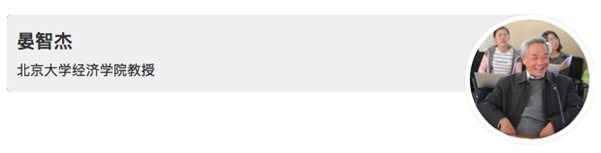
晏智杰教授例举过去学界对阶级斗争史观、社会形态五段论的教条引用说明,学者们对辉格史观的最大批判在于,这一史观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惟有尽可能地挖掘当时的历史环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才能给予历史人物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还展开论述了萨缪尔森运用辉格史观研究思想史的四个实例。例如,在1978年的论文“规范化古典政治经济学模型(Canonical Classical Mode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萨缪尔森试图构建一个一般的框架,描摹李嘉图、米尔、马尔萨斯、马克思、亚当·斯密之间的共同点,但这些人时代、阶级、学术立场和观点各不相同,除了都涉及供求分析外,其余观点都是相异的。对各派观点都强调发掘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恰恰是辉格史观的弱点所在。再如,萨缪尔森认为,魁奈的“经济表”为日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许多后继学者都受其影响颇深。事实上,魁奈的这一创见并非意在为后续理论铺路,更多地表达了对法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深切困惑与担忧。但在数学分析面前,观点的历史温度悄然消失了。最后,晏智杰教授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学工具进行规范表述是可取的、不排斥的,但经济规律是不能通过数学模型发现的,更需要对历史、对社会进行深度考察和分析。

接着,贾根良教授也对萨缪尔森的辉格史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他对萨缪尔森运用辉格史观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事实上,巴特·菲尔德《辉格的历史诠释》一书很早就收到了来自历史学、科学史学等领域的批评,但萨缪尔森在两次美国经济学会的讲演中却将其作为正确的方法加以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讲,进行跨学科的互动和交流是极为必要的。其次,辉格史观的鲜明特征是单纯利用数学工具研究思想史,忽视其背后的社会背景,这样做难以真正地理解思想史。上世纪60年代,在萨缪尔森提出其方法论见解的同时,西方学界就出现了有关知识史的研究,强调宗教、文化、哲学等各种思潮对一种经济学说的提出或某一经济学家思想形成过程的影响,并在后来发展成了学界史。贾根良教授提出,相比于辉格史观和知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能更适合研究思想史,其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的认识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纲领,但更多的研究工作还有待后续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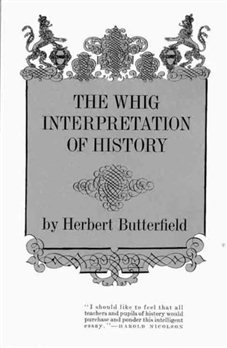
巴特菲尔德《辉格的历史诠释》原版书影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M]. G. Bell and Sons, 1931.)
再次,辉格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观点创新,阻碍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按照“进步的辉格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就与考古学划了等号,且研究内容是“死人的错误见解”。这无疑窒息了学科的发展创新,甚至有些欧美国家曾试图将经济思想史学科划归到历史学、考古学的学科目录下。时至今日,西方学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归属问题仍存在广泛争议。这不能不引起学者的深思和警醒。最后,贾根良教授表示,应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强调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包括许多对立的学说和研究范式,但辉格史观却试图运用单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去刻画全部的经济理论,其最终结果便是禁锢了思想发展的多元性、巩固了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在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经济学家系谱图中,最终只留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位置,而其他非主流的、异端的经济学派都消失了。若无争鸣,何谈学科发展?贾根良教授结合国内经济学界的现状进一步指出,当前国内学界也存在着西方经济学主流化倾向,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甚至比西方更稳固,极不利于国内经济理论的迭代创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学亟待一场革命的到来,应当鼓励多元化的研究体系,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推进,为经济学领域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和创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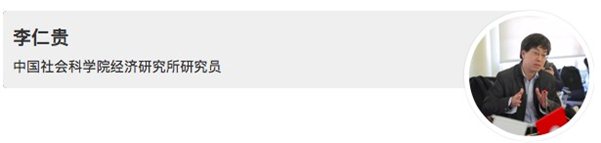
李仁贵研究员结合自己担任《经济学动态》期刊编审的经历,对论坛主题进行了横向扩充。他提出,当前国内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确实存在式微态势,甚至没有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期刊。就《经济学动态》来说,留给思想史研究的版面也相当有限,且大多摘录介绍前沿经济思想的文献进行刊登。这种形势对于该学科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李仁贵研究员关于国内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现状及专业学术期刊定位的反思,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共鸣和讨论。此外,李仁贵研究员还结合自己长期对西方经济学者谱系研究的经验,细致讲述了萨缪尔森的成长环境、家庭环境、师生关系等背景资料,为本次论坛的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背景信息,使得萨缪尔森作为经济学界泰斗的形象愈益丰满。他更是运用了“历史重构”的方法深入挖掘历史人物所在社会环境、设身处地考察理论创建的原初含义的生动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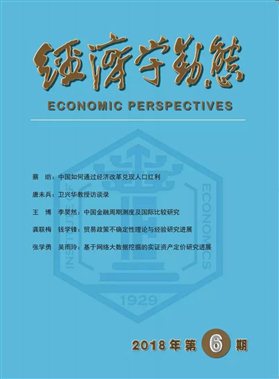
期刊《经济学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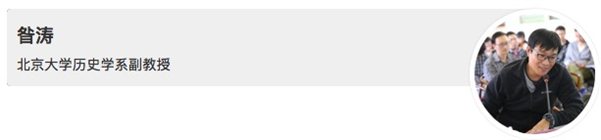
昝涛副教授则从自身专业背景出发,分享了自己对辉格史观这一方法论的认识。他指出,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工具等前沿分析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热潮,并不只出现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而是人文社科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历史学界也曾掀起过一场争论,即计量史学是否会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更深层次地说,历史学在长期求证一个问题: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而言,“科学主义”曾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话语体系甚至最高标准,一切学术研究都要向这一研究范式靠拢,以至于历史学也必须极力声称——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及变化的科学,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及变化,故而历史学也是科学。而极力证明自身学科科学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危机的重要表征。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昝涛副教授将萨缪尔森与其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进行了类比。他表示,相对于萨缪尔森的辉格思想史观,亨廷顿始终坚持“理性主义”。正如阿贾米在纪念亨廷顿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之贡献终生的领域——政治学,已经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夺了。他们是相信‘理性选择’的人,靠模型、数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话来写作。”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也评论说:“他也从来不相信‘理性选择’,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亨廷顿的著作横跨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带着厚重的沧桑感,凝聚着人文素养,也渗透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包括环球旅行的观感。他的学风属于那一代人,正统、保守,却包藏着尖锐甚或偏颇的风骨。”值得欣慰的是,当今历史学正在倡导批判史学的方法论,即以求真为研究的最高标准。而是否获得大多数人的欢迎、能否带给现代人见解,则是第二位的。昝涛副教授最后表示,历史学家应是“真相的看门狗”。虽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像萨缪尔森一样运用辉格史观重构历史的人是多数派,但愿意做“看门狗”的少数派,更值得人们敬佩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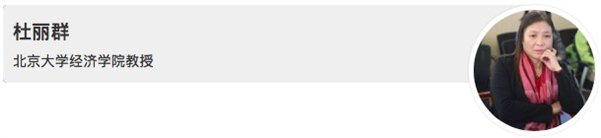
杜丽群教授结合自身教学和科研的体会发表了见解。杜丽群教授提出,方法论是贯穿经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重要问题。随着现代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的完善升级,当然会有推陈出新的方法有待开拓和应用,但“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两种方法论是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落脚点。广义上来讲,很难评价某一种方法论的绝对优劣;但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上说,“历史重构”方法更能帮助现今的学者回归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也是本次论坛的核心命题和要旨。接着,杜丽群教授又表达了自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现状与前景的展望。她指出,近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确实面临着其他分支学科的挑战,但得益于经济学院“以史论见长”的传统,加之陈岱孙、晏智杰等前辈对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与传承,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未来可期。继承光荣传统、推动学科革新,也是新一代学者的使命所在。
互动环节,与谈学者耐心解答了到场师生提出的问题,包括辉格史观的含义界定、萨缪尔森辉格史观分析与经济分析的区分、萨缪尔森自述作为史料研究的优越性、如何复兴和利用经济思想史学科等内容。
最后,晏智杰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指出,辉格思想史观有两大特点,即功利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以自以为正确的理论和原则去规范过去、描写过去、改造过去,给历史“穿上现代的西装”。这不仅难以让史学研究接近真相,也难以引领实践走上健康、科学的良性轨道。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共同探讨辉格史观及其影响是极其必要的。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正面临大转折,也正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提出全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并结合本国国情特色加以改造;而经历40年的试错和发展,倘若仍不能提出中国本土的理论,就很难解决本土的现实问题。回溯漫长的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危机往往是重大理论革新的契机。没有所谓的重商主义破产,很难想象亚当·斯密革命;没有30年代大危机,很难想象凯恩斯革命;站在时代的转折点,学界才更应该对中国经济学、思想史的开创性贡献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