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7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彷徨之始——《破恶声论》的内部矛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荣休教授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主持并评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长聘副教授季剑青、长聘副教授陆胤、助理教授胡琦与谈。本次活动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

讲座伊始,胡志德从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技术的态度引入话题。鸦片战争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尽管产生了对于西方技术和工业的兴趣,但思想层面仍存在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二元结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期待以西学知识弥补技术劣势,从而抵抗西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于全社会是一个重大打击,此前稳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二元思维结构在部分群体中开始动摇。例如在严复等人看来,西方的部分思想确实优于中国本土。胡志德强调,从甲午到“五四”是中国知识界极度不稳定的一个时期,这在世界文化中都是较为少见的现象。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在社会层面深刻动摇了原有的思想结构。一直到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主导的年轻知识分子群体才建立了新的知识权威,使得西学更具优势。

▴
鲁迅与内山完造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
上海新月亭合影(1936年2月11日)
胡志德表示,正是甲午至五四时期思想界的不稳定结构,让此一期间生成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理论充满怀疑的热忱和蓬勃的生命力,鲁迅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胡志德看来,这一期间思想逐步成熟的鲁迅,其实一直是一个“晚清人”,他和其他的“五四人”有所区别,《朝花夕拾》和《野草》中都可以找到众多具有晚清特质的“不稳定因素”。鲁迅在留学归国前夕,在革命刊物《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也是其中的一篇。胡志德认为,鲁迅这几篇作品都有尼采反对群众社会的色彩。有别于1927年收入《坟》的《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没有在鲁迅生前结集出版,而是在其去世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因此没有引起相对热烈的讨论。实际上,三篇文章都是在批评“大众的专制”,鲁迅认为表述相同的众声,仍然是一种“沉默”与“寂寞”(solitude/silence)。《摩罗诗力说》从文学家的角度论述西方文学家对“大群”的批评,《文化偏至论》则从思想家的角度进行批判。在鲁迅看来,物质文明在欧洲兴起后已经有许多批评,但传入中国后还未能引发警醒与审视。鲁迅因此感觉十分“寂寞”,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声音去反对此种情况。

▴
鲁迅为文集《坟》设计的封面
已有关于《破恶声论》的讨论多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胡志德认为,应当对这篇作品进行诗学和文学的解读。《破恶声论》在语言上更加生涩曲折,这可能与鲁迅的有意选择相关。相比之下,《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更加重视欧洲的社会现象、思想形态,重视要学习欧洲,借此可领导民众反对专制现状;而《破恶声论》则有意避免对欧洲文明的评价,没有相近的表述。从诗学和文章学的角度来阅读,《破恶声论》全文弥漫着一种在悲观与乐观之间来回摇摆的“彷徨”之态。
接下来,胡志德对《破恶声论》进行了详尽的文本分析。在《破恶声论》开篇,鲁迅通过“寂漠为政,天地闭矣”传递出自己的绝望之感,但笔调随后转折略显乐观:“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在鲁迅看来,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内曜”和“心声”,才有着如此“黮暗”“伪诈”的现状。“心声”的谐音“新声”和“新生”,同时指向“新的声音”和“新的生命”,后者正是周氏兄弟早年意图在东京创办但未能落实的文学刊物《新生》。在鲁迅这里,“心声”是破“黮暗”、离“伪诈”的关键要素:“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因为有“个人”的出现,“大觉”(觉悟)就会很快出现。“朕归于我”的说法体现了鲁迅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胡志德认为,这里的“主体性”颇具能动色彩,应当翻译为“subjective agency”,而非“subjectivity”或其他。然而与此同时,鲁迅又指出,如果个体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就要比外面野蛮的声音还要厉害,就会更加“寂寞”(“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关于如何区别“个体的声音”与“群体大众的声音”,鲁迅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
梁启超著《新民说》
《破恶声论》随后转向了一种与梁启超《新民说》类似的乐观论调,旨在探讨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如何能够结合而克服危机:如果有志士仁人“相率赴欧墨,采掇其新文化,而纳之宗邦”,“则中国之人,庶赖此硕士而不殄灭”。然而,随即鲁迅又给这一乐观的论调泼了冷水,“虽然,日月逝矣,而寂寞犹未央也。上下求索,阒其无人,不自发中,不见应外。”换言之,在这篇文章中,每每在似乎要得到一个确定性结论之际,都要伴随出现一个矛盾的注解。这无疑凸显了甲午战后知识分子内心的认识论危机,并标识了“个人声音”及其起源和本真性的不稳定状态。
通过详尽的文本分析,胡志德指出,文意层面鲁迅的态度前后摇摆,和其他的文本也或有矛盾,这种变动正体现出鲁迅对于自身“个别声音”的探索。研究者多注意到鲁迅在《〈呐喊〉自序》和《故乡》中的悲观与矛盾与辛亥革命失败之间的关联;但正如汪晖指出的那样,《破恶声论》与鲁迅五四时期的散文和小说中呈现出的相似的矛盾和摇摆,也不可忽视。
在胡志德看来,《破恶声论》在语言文字上的生僻,要追溯至章太炎的影响。鲁迅同章太炎对于文言的追求相近,很重视文风和风格,而这一面向很容易被解读者忽略。类似的侧重早在严复和吴汝纶的翻译讨论中便有所体现。英文学界也同样认为风格(style)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胡志德认为,晚清以来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人重视修辞、风格,看重语言和思想的关联,如严复的“信达雅”;另一部分只把文字当做功利的内容,如梁启超,并不在乎文字的好坏,只在乎其功用。在晚清特殊的境况中,民族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前者。这也构成了鲁迅的“困惑”与“折磨”——既要保留自己旧有的文化背景,同时接受新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上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此外,在文本和风格层面,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鲁迅先后多次提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对鲁迅的影响,更多反映在文本风格上,而非具体内容。有学者认为,鲁迅完全“陷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诱惑”,在写作中“隐匿”了自己其他的特质。胡志德认为这种判断或有不妥,鲁迅可能只是在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
鲁迅像,曹白刻
带着上述对《破恶声论》文辞和思想的基本判断,胡志德再次回到鲁迅的文本,指出其中现代主义的成分。在他看来,对当下社会现状的怀疑,对语言文字表现力的怀疑,对未来的不确定,正是鲁迅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如此观察鲁迅后续的作品,《狂人日记》中业已出现了“内声”,但却无人在意,其“孤独”的探讨也是对于《破恶声论》主题的延续,狂人的声音从何而来也没有答案,照应了“天地闭”的论述;而《故乡》中对少年闰土的回忆和激赏,《野草》《朝花夕拾》对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涉及,也延续了《破恶声论》中“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话题。有学者认为,赫胥黎进化论和尼采个人主义的矛盾正是鲁迅张力的来源,这种张力到了《野草》阶段,引发了强烈的内爆。
最后,胡志德以《野草》中《好的故事》一篇作为本次讲座的结束,指出鲁迅行文中的整体性、主体性,也具有美学上“崇高”的呈现。在他看来,鲁迅的创作至始至终都蕴含着对“完美的景”的追求,这是鲁迅的“负担”,也是魅力所在。
与谈环节
随后,论坛进入与谈环节。高远东老师表示,关于《破恶声论》,自己此前更多重视其中思想的“理性表达”,即鲁迅对中国近代、现代化方案所谓六种“恶声”的批判,有别于胡志德对这一文本之文学性的重视。高远东老师认为胡志德对于《破恶声论》文学化语言的关注与解读,其方法内部也蕴含着鲁迅的特性,能够更好地展示出鲁迅自身的复杂性。尽管《破恶声论》更接近一种公共经验的文学化表述,与极端个人性的《野草》有一定区别,但胡志德把《野草》纳入对《破恶声论》的考察,便将鲁迅文学的彷徨主题贯通了起来。高远东老师补充说,鲁迅对尼采的关注与其留日时期在弘文书院学习德语的方式有关,当时的德语教材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日译本以译佛经的方式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也影响了鲁迅《野草》的表达方式。高远东老师同时指出,胡志德对鲁迅《破恶声论》的思想矛盾、语言表达的混杂和缠绕都有关注,但就鲁迅的文学姿态而言,“彷徨”之外,还有“呐喊”,这两者都是兼顾文学和行动的,如果只停留在语言或思想的层面思考,或许忽视了鲁迅文学、鲁迅创作的行动性和实践性。高远东老师最后表示,我们更宜将鲁迅的种种思考放在思想和行动的连接处,以此理解鲁迅的文学姿态,发现《破恶声论》中鲁迅积极行动的一面,以便建立起对鲁迅的总体认识。

▴
论坛活动现场
季剑青老师表示,胡志德在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强调既有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晚清已经出现动摇,由此肯定晚清的独特意义,而这与历史分期问题紧密相关。在文学研究领域,“近代”和“现代”通常都被英译为“modern”,王德威曾经将“近代”译作“early modern”,但在其他语境中,“early modern China”也用来指宋代或晚明。这种在翻译中表现得特别含混的历史分期问题该如何得到重新的审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季剑青老师还提出,胡志德最后用“modernism”来概括鲁迅文章及其文学的特点,表示在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对“现代”的批判,这为探讨留日时期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开拓了新的视野。鲁迅批判宋代以来普通文言(ordinary language),主张回到魏晋,回到周秦,从更古的世界寻找思想与文学资源,这与他对“心声”的探寻是什么关系?“心声”所对应的“扰攘”,是否就是指称这种“ordinary language”?这些都是胡志德的报告启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最后,季剑青老师还从胡志德的报告中体会到,鲁迅的彷徨源于被不同的文化力量、语言和思想撕扯,他自身努力寻求建立一种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故事》可以在象征层面理解为对鲁迅的困境与痛苦的揭示。胡志德从《好的故事》中读出“崇高”的意味,这让季剑青联想到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康德美学中“优美”“崇高”(王国维译为“壮美”)范畴的引述。“崇高”的对象在主体那里引发的反应恰恰是“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而使得统一的主体性难以建立,这与胡志德所表达的鲁迅的精神困境是相通的。
陆胤老师从自身研究出发,表示胡志德教授的论文并非在单纯意义上谈论“文学”,而更接近传统的“文章”和“文法”的讨论。如“心声”“扰攘”等概念更造成了一个比喻系统,用于鲁迅内在性追求的表达。陆胤老师指出,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已经得到公认,刘师培的影响则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尽管鲁迅在行文中有意避免骈对,但还是保留了很多骈句式的表达。此外,《河南》原刊的文本形式也值得注意,圈点并非单纯的句读,而是出于编写者对于文章内容的判断,有助于我们更好体察作者的本意。从思想史观察,胡志德提出鲁迅始终是一个“晚清人”,同样发人深省。《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堪称鲁迅的“老三篇”,是晚清文学转向内在的重要标志。鲁迅不像梁启超、张之洞那样强调文学是教化工具,而更突显文学的内在价值。这种新颖的文学观念对于五四时期的主流文学观是一种潜在的引导。
胡琦老师针对《破恶声论》的修辞问题,指出此文开头有关情感萌发的论述,从内容到骈对的形式都渊源于《文心雕龙·物色篇》。《破恶声论》以听觉(“心声”)和视觉(“内曜”)平行推衍,最后还是回到声音,这种奇(深层)偶(表层)相因的结构,也和《雕龙》多有相似。又如“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让人想起孔颖达的“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但又被赋予民族性批判的新意。正如胡志德所言,如果鲁迅的预期读者是有足够古典素养的读者,那么在进行这种论述时,读者会发现其阅读期待被突破、被超越。从写作语体上看,章太炎、刘师培、鲁迅以秦汉古字行文,似乎与明代七子的“复古”相似,但明代复古派以使用古代地名、官名等著称,而鲁迅则是将古雅的形容词、名词、动词化入笔端,复又灌注以新的思想,例如“披心”“扰攘”等皆来自汉人文章。此类处理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古文和文言的传统有着很大启发。如果从诗学的角度解读《破恶声论》和《摩罗诗力说》,我们可以追问:在鲁迅的思想脉络里,“文学”对于“心声”的达成有何特殊意义?鲁迅对于宋代以后文言文的反驳,是仅从种族的角度而言(区别于清代人),还是有更多理论上的自觉思考,认为宋以前的古文更加“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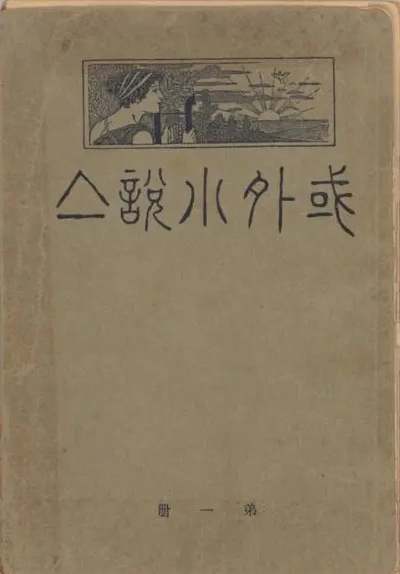
▴
鲁迅编《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最后,张丽华老师对全场发言进行总结和评议。她认为胡志德从文学和诗学的角度对《破恶声论》的阐释十分具有启发性。她特别提到,本次论坛题目中的“彷徨之始”在英文中胡志德用的是“Hesitation Prefigured”,“Prefigure”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奥尔巴赫在《新约》和《旧约》之间建立的“形象阐释(figural interpretation)”。胡志德在《破恶声论》和鲁迅的《彷徨》《野草》之间建立的关联,并不是直线式的起源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喻示、互相阐释、循环往复以共同完成鲁迅之为鲁迅的形象关联。循着几位与谈人对“心声”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张丽华老师补充道,《破恶声论》和鲁迅晚清时期对于域外小说的古文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鲁迅在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序》中有着与《破恶声论》高度相似的表述:“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在这里,“心声”的具体所指就是“域外小说”。在她看来,晚清的鲁迅和严复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从翻译的角度来看,鲁迅用古文翻译域外小说,严复以文言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其实已经是一种试图在中西语言、思想和文化之间进行调适的尝试。与胡志德的观点略有不同,张丽华老师认为,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并没有排除西方话语,其中有许多同周作人这一时期文言论文中所介绍的欧洲文学论著相似的论述,而在这些论述背后伴随着的恰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而诞生的现代“文学”观念,这一现代“文学”观念恰是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赋予“心声”的新解。
论坛最后,胡志德对上述发言进行了回应,与会学者与听众就中西文化二元对立、鲁迅个体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至此,本次文研论坛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