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丁得天老师
2020年9月29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丁得天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以敦煌为中心”。第九期邀访学者陈志平、韩琦、李丹婕、李鸣飞、陆蓓容、孟庆延、邱靖嘉、吴敏超、姚泽麟、周伟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中古时期的高僧、佛像及其道场是佛教史与石窟寺考古所关心的经典主题之一。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及相关问题持续讨论多年,虽然其分属不同的三个研究对象,但本身是一个高度关联问题的持续延展扩张。其中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讨论尤为丰富,而将番禾瑞像的“道场”——圣容寺的研究同时纳入本研究的视角,做为三段串列式的对象来考察,内容虽多,却能更直观的进行对比进而理解其背后的意涵。相关主题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等考察家带走的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与艺术品,因敦煌文献中涉及到刘萨诃文献与番禾瑞像的图像,使其成为关注对象,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尽管持续如此之久,仍有众多待破解与阐释的问题,特别是瑞像的产生与古印度舶来造像的传播、中古民间信仰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是刘萨诃研究。最早的刘萨诃研究系1960年日本安藤更生在《鉴真》中谈到的刘萨诃生平。至七八十年代陈祚龙、史苇湘、孙修身、肥田路美等陆续对其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

莫高窟第72窟西壁龛外北侧壁画及榜题(晚唐五代) 圣者刘萨诃和尚
刘萨诃信仰随其生平事迹的变化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面貌。刘萨诃法名释慧达,稽胡族,山西离石人,东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晋北、江左与河西地区。出生地吕梁地区是稽胡族聚居区,此时刘萨诃信仰仍处于崇拜“胡神”的状态,而刘萨诃 “本庙”的建立表明高僧崇拜已于此地盛行。出家后在江左各地的游行觅塔活动表明其“胡神”的身份已转变为更写实化的“高僧”。鄮县(宁波鄞州)阿育王寺、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是中华十九座阿育王塔中最早的两座,觅得二塔即刘萨诃之功。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刘萨诃信仰更多是基于对阿育王塔的崇拜,如泉州开元寺塔基中“萨诃朝塔”的图像。刘萨诃在鄮县、建康等沿海地区觅得阿育王塔,包括沪渎口石佛浮江等佛教史迹故事在东南沿海的流行,或显示出佛塔等佛教圣物自海路入华的可能性。

福建泉州开元寺东塔塔基浮雕 宋“萨诃朝塔”拓本
北凉末刘萨诃行经番禾县所做的预言可能是中古佛教史上最灵验的预言之一。由此诞生的番禾瑞像同时也将刘萨诃崇拜推向了高潮阶段,敦煌石窟及藏经洞所出文献、绢画乃至河西各地石窟所见丰富的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组合见证了这一信仰的盛行,同江左地区相似,河西地区对刘萨诃的崇拜主要附于番禾瑞像信仰中。刘萨诃的游行礼塔路线与此期佛教传播形势及入华路线亦有相近处。刘萨诃早期的生平事迹常与地狱信仰等涅槃类经典相关。涅槃类经典以佛性论贯穿始终,核心论点有涅槃四德、一阐提迦成佛、如来常住等,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刘萨诃事迹恰与此类经典宣说的义理相合,表明吕梁地区很早就传入并接受了地狱信仰。从晋北到江左觅得阿育王塔,不仅是刘萨诃求取佛法的行动实践,也表达出其最初有海路求法的可能,而凉译涅槃类经典传至南方后,西行或变成了更佳选择。

極楽寺本『六道絵』について」
日本兵库县极乐寺藏刘萨荷入冥图(镰仓时代)
刘萨诃是阿育王塔及其形制最早入华的传播者,也是小乘向大乘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且尤重实践。与其生地晋西北与江左地区的史实相比,西行河西的经历更富神异性。其预言了番禾瑞像这样中国化的佛像的出世,更重要的是为中下层百姓昭示了一条次第而上、渐次修行的成佛路径。
第二部分是番禾瑞像研究。番禾瑞像又有凉州瑞像、番禾县裂像、圣容瑞像、刘萨诃瑞像之称。其中莫高窟中唐窟的榜题称圣容瑞像,系最准确的名称,而刘萨诃瑞像易与刘萨诃“本庙”之像分歧,须加甄别。


敦煌莫高窟第237窟(中唐) 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 大英博物馆藏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番禾瑞像刺绣(盛唐)
敦煌石窟中番禾瑞像的题材及组合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单体造像或画像,如莫高窟唐代第203、300窟,榆林窟晚唐五代第17、28窟的塑像,其他如莫高窟五代及宋第26、31、76等窟的甬道顶部,西千佛洞部分窟更是直接将其绘于窟顶。所制塑像、画像的位置或有不同,但其系释迦佛本身。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盛唐的一件大幅刺绣,有番禾瑞像与二弟子二菩萨一铺五尊的排列,瑞像身光绣出嵯峨山崖,这样的配置显示了其释迦佛的尊格。

永昌县博物馆藏背屏式石雕番禾瑞像(初唐)
第二类为晚唐五代所绘大型刘萨诃及番禾瑞像故事变。现存仅此一铺,即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所绘。整图内容分上下两层,上层中为番禾瑞像立像一身,两旁胁侍一众弟子菩萨,如连环画般绘出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史迹故事;下层中有番禾瑞像一身。与之相对的北壁绘通壁弥勒下生经变,如此配置,使瑞像提升至与下生弥勒比肩的地位,巫鸿先生更是称其为“中国宗教史上思考最为深刻的一幅图像”。可见晚唐五代之际,番禾瑞像及其信仰的盛行及其地位已上升至顶峰。

莫高窟第72窟南壁刘萨诃及番禾瑞像故事变(晚唐五代)
第三类为史迹画。通常出现于晚唐五代窟的盝型甬道顶,一般与牛头山瑞像等图像组合为史迹画。如31、45、401等窟的甬道顶,榆林窟33窟的图像则绘于南壁。盝顶甬道两披通常亦绘出众多瑞像,此类组合已成定式。

莫高窟第401窟甬道顶(五代)
第四类为番禾瑞像与猎师李师仁的组合。通常为中心佛坛窟后部直通石窟顶部的背屏后方,中间绘一大幅瑞像,瑞像脚下两侧绘李师仁图像,南侧常绘李师仁骑马射鹿,北侧常绘李师仁牵马跪拜僧人。如第16、55、61窟背屏等。
这四类组合式图像内容复杂,演化时间较长,但基本上涵盖了刘萨诃与番禾瑞像所有的题材,是这一信仰在敦煌与河西地区盛行的形象表达。


莫高窟第61窟背屏南侧 莫高窟第61窟背屏北侧
(五代) (五代)
番禾瑞像相关的记载十分有限,而从实物入手,目前发现和统计到的有关瑞像的形象以唐五代宋西夏居多,与道宣所记自北魏以来持续的造像活动仍不能完全对应。圣容寺所在的古番禾县地区所出几组大型的唐代背屏式番禾瑞像,其复古的造像特征要考虑新的造像风格再次传入的可能。
三是圣容寺的研究。圣容寺最初因番禾瑞像出世而初名瑞像寺,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至此将其改名为感通寺,大约西夏时期改名为圣容寺。作为番禾瑞像的“道场”,圣容寺的建立与历史同样是刘萨诃、番禾瑞像及其信仰在漫长的时段内流传于河西走廊的集中反映。圣容寺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孙修身前往永昌当地的调查,廓清了北魏北周以来瑞像寺的建寺历史。至隋代改瑞像寺为感通寺,而武威出土碑记所载当地寺名为“感通下寺”,武威古浪县所出圣历元年(698)番禾瑞像造像碑,以及张掖马蹄寺、石佛崖,永靖炳灵寺石窟等高度还原和写实的番禾瑞像,表明感通寺在河西地区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居于寺院网络中心的地位。

九十年代圣容寺旧址及唐塔


番禾瑞像残存躯干部分 圣容寺塔(中唐)
马德在日本滨田德海所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中释读出北宋乾德六年(968)重修该寺的档案,结合近年来对圣容寺及其周边丰富的佛教窟寺遗迹的调查,使得圣容寺的历史沿革更为清晰的梳理出来。
有关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的研究尚处于动态的深入研究阶段,仍需要通过继续梳理敦煌与河西地区的石窟寺及造像,综合整理石窟建筑、图像、文献以及佛教史、中古政治史的资料来理解,特别要关注初唐时期从印度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经典与造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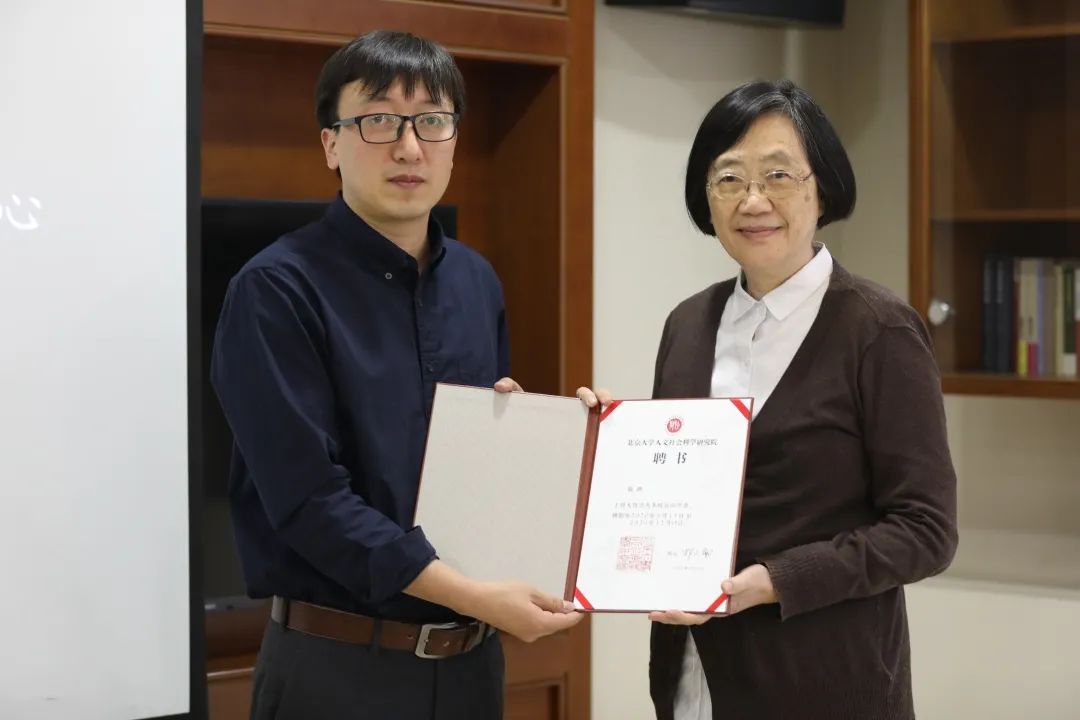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丁得天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