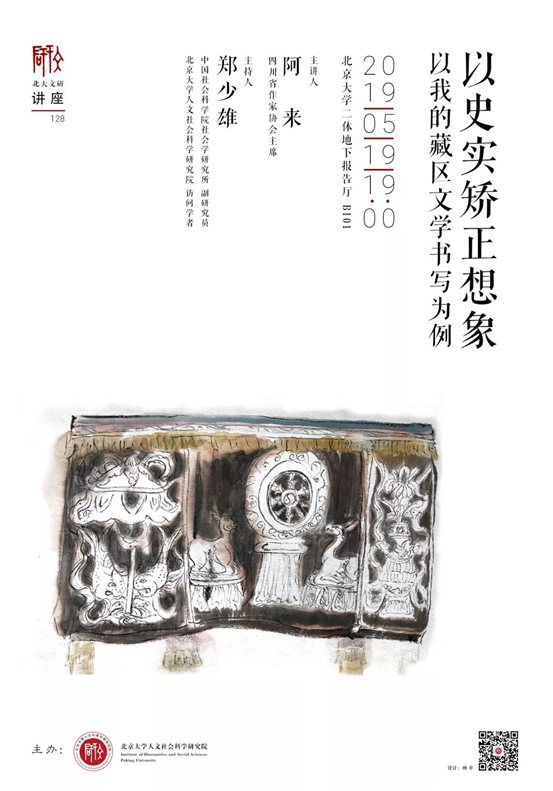
文研讲座128
2019年5月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以史实矫正想象——以我的藏区文学书写为例”。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主持。

主讲人阿来
郑少雄首先简要介绍了阿来的主要作品,强调了其背后包含的田野观察和独到的人类学关怀。郑少雄指出,在本次讲座中,阿来将回应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以宽广的文化比较视野探讨相关社会现实和社会理论。阿来的书写和思考不仅限于少数民族世界,更是与中华民族、与遥远的全球世界之间的协商和对话。
讲座伊始,阿来回顾了自己少年时代学习汉字的经历和相关的阅读体验。阿来认为,学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生不同阶段的困惑。对当时的他而言,有两个困惑一直围绕着自己。首先,作为一名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师,阿来注意到历史教育的局限性。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构成了我们存在的世界的条件和认知框架,但是抽象的历史知识无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当下的中国社会,也无法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一个村庄、社区、乡县发生的问题,才是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而历史问题则不能解决自己当下的具体困惑。阿来以《光荣与梦想》一书为例,比较了中国和美国进行历史教育的不同之处。该书从微小而具体的事件出发来讲述历史,聚焦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像中国的历史书一样从皇帝、大臣的视角讲述历史。这一特点使得人们通过历史阅读所塑造的世界观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阿来谈到写作对青年人的重要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各个专业的大学生都在从事写作。阿来认为,文学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通过文字,青年人能够表达内心深处对世界的一种豪迈的想法。同时,在具体的日常生活范围中,青年人的生活也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当这种迷茫和豪壮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文学中迷人的思想则产生了。
阿来继而谈到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82至1989年期间,阿来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陆续出版,在拿到自己作品的同时,阿来开始了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反思。阿来指出,自己在语言的审美层面着力较多,在写作中会有意识地强制自己揣摩字词句的用法。而在内容方面,他认为自己仍有不足,在这一方面,阿来提出了一个文学命题,即所谓的文学到底是书写个人还是书写集体。

讲座现场
阿来进一步谈到文学背后的族群概念。今天的文学除了审美的层次之外,更重要的是和地域、集体的关系,从而涉及到想象、民族和宗教形态的差异。阿来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写作少有批判、反思,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写作者,都更多地满足于一种文化依附关系和文化符号想象。阿来以吃生牛肉的少数民族习俗为例,反思中国边疆书写中的少数民族自卑与自满的双重心态。文化态度对于中国边疆书写有着重要影响,这种文化自卑与自满的心态既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理解的缺乏,也来自于对世界文化的陌生。
阿来强调,在这一层面上,“边疆”一词是在欧文·拉铁摩尔的概念意涵上使用的,指的是内部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这样的文化边疆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而且在一个民族内部,地域的差异也会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藏族民族认同内部的多样性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藏民族内部,无论是语言、历史,还是宗教形态和生产方式,它们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具体而言,阿来讲述了对“白马藏族”进行划分的例子。1980年代初期,应白马人的要求,国家曾组织民族学家、语言学家等对“白马藏族”再次进行族属研究,尽管存在争议,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仍将其明确为藏族的一部分。阿来借此说明,在某一民族文化内部构造的民族认同很容易带有强制性的特征,这一点在中心地带要求边缘地带进行文化认同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不仅在不同民族之间会产生误解与歧视,这一现象在同一文化内部也同样会产生。然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边缘地带往往具有更加丰富、多样、不断变化和演进的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化只有在这种变化与演进中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民族问题,后殖民理论一直影响着学术界。阿来认为,后殖民理论过于强调民族文化认同,其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满足的是传统欧洲帝国崩解以后的需求,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土壤。后殖民理论需要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来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则必然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当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就是例证。但是在中国的文化文学领域,今天仍然存在对后殖民理论的依赖,学界往往习惯于用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来简单地解释中国内部的边疆问题。
阿来的书写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阿来谈到,藏族人内部对其小说内容的一些质疑和反对也是民族内部文化认同分歧的一种体现。今天的许多社会学家的田野考察或者文学家的田野采风,忽略了普通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角落里正在发生的演变。在这些角落里,旧的东西正在消失,新的东西正在艰难缓慢地成长。书写这些事物,更重要的是书写其中新的人、人的情感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决定了他们将来面对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一个地区、一个人群面对世界的方式。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边疆地区存在两种变化的可能,一种是接受先进文化,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促进自身文化的更新;另一种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压迫下,更加趋于保守,对外在世界视而不见。阿来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摆脱想象共同体中民族内部盲目的认同强制,更重要的是,作为写作者,阿来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和批评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警惕。
提及自己作品引发的争议和反对,阿来谈到,在文化、思想界,坚持自己的见解,表达对生活、世界、文化命运的想法,同样需要勇气。否定的声音可能来自内部和外部,内部的反对源于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外部的质疑则来自于对西藏这样的神秘化的共同体更加强化的想象。当代西方对西藏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浪漫化、神秘化的趋势,这是值得警惕的。基于在藏区做考察的经验,阿来指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藏区文字资料的缺乏有关。流传在藏区的主要是口述资料,很少有文字资料,在创作过程中,阿来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官方记载和民间传说进行比较,试图去厘清基本事实。口述资料的缺点在于,每个讲述者都会渲染和添加,这也为藏民族蒙上了一层神秘化、浪漫化的面纱。
阿来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不同于传统的藏区文学,也不同于文学界对当时既有的藏区文学的预设。随后,他分享了在出版过程中的趣事,编辑对于《尘埃落定》的修改意见往往以对藏区文学的旧有想象为依托,而这正是阿来想要破除的标签。阿来认为,文学的进步是由内在观念的进步和革命来完成的。文学的革新是双重的,容易被人们发觉的是外在形式,难以觉察的是内在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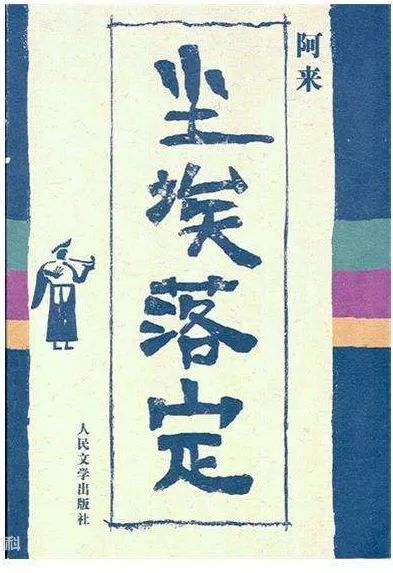
《尘埃落定》书影
阿来在书写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一个现实问题,即藏民族在唐代就几乎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状况,在此之后,是什么导致了藏区发展的停滞?阿来试图探讨一种原本具有先进性、扩张性的民族文化逐渐停滞和萎缩的原因,因此,他以藏区史诗《格萨尔王》作为范本进行讨论,创作出作品《格萨尔王》。阿来指出,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藏民族越来越佛教化,社会的一切都被纳入到简单的因果报应的逻辑轨道中,这种社会解释系统与文化生命的停滞密不可分。而在现在的宗教文化背后,恰恰缺少对西藏百姓和个人的理解。阿来强调,当我们的学术训练使得这种基本的关怀都消失了的时候,学术就不提供价值了。先有理解,才有真实,其后才有价值。
最后,阿来回顾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书写历程。他谈到,自己一路走来,恰如一部和内部想象与外部想象相搏斗的历史。作为科幻杂志编辑及负责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他启发,去克服狭隘的文化意识,从作为人的层面,超出国家、民族的层面书写人类的话语,而这是阿来一直以来的写作目标与使命。

《格萨尔王》书影
随后,郑少雄对讲座进行评议。郑少雄指出,阿来不仅是优秀的作家,也是优秀的人类学家,其探讨的藏民族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内部边疆文化的多元性、混杂性,克服了本质主义的想象,提供了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很好的理论对话。郑少雄认为,一方面,“共同体”可以有两种“想象”方式,一种是从边界来排除,另一种是从典范中心出发来构想,这两种想象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本意是通过考察民族主义之滥觞、流布来破除民族主义神话的,在第三世界反而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武器,阿来的写作历程以及遭遇,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但是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是有社会理论洞察力的,阿来对狭隘的身份认同意识有着清醒的警惕。
提问环节,阿来与现场听众就自己的创作心理、文学见解和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进行了讨论。讲座最后,阿来讲述道,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社会讨论中,都不应以差别论差别,而割裂了鲜活的现实和具体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