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g)
.png)
重审考据之学
清代学术的表与里
2020年6月27日下午,“云端论坛”第七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重审考据之学——清代学术的表与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17年秋季学期文研院邀访学者华喆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璧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董婧宸、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教授张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琦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陈鸿森先生的新书《清代学术史丛考》展开。陈先生在中国经学史和清代学术史领域耕耘近四十年,发表文章愈百篇,成就斐然。去年,陈先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文集《清代学术史丛考》,选入论文十二篇、演讲稿三篇,是两岸学界期待已久的大作。在文研院的组织下,八名学者共聚一堂,分享各自对该书及陈先生治学的心得体会,并重新思考、讨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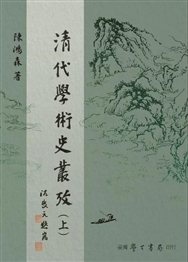 华喆教授首先宣读了陈先生为此次论坛撰写的引言。陈先生以本书向当年推荐自己入史语所的几位老先生致敬,希望无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前辈学者渐次凋零,民国学风式微沦替,陈先生坦言自己已是“史语所旧学传统最后一个残垒”。现在的学风急于求成,“研究的人变多了,但读书人变少了”,自己则不惮“逆风而行”,以“抵抗流行的学风和研究,不管是精神上或方法论上”。陈先生指出,自己倾心于“阐幽扶微”,会刻意关注一些重要而长期被忽略的学者,或重要学者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这本《论丛》,对陈先生而言,如在高山攀爬时所见的一些景观意趣,“我无意攀登峰顶,我只是随性的在清代学术这座连绵的大山里,探索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原生态景观,如是而已。”最后,陈先生还预告未来会另编《清代经学研究》一书,收录有关清代经学的部分成果,并计划撰写《皮锡瑞〈经学历史〉得失论》一文,作为研究清代经学的总结。
华喆教授首先宣读了陈先生为此次论坛撰写的引言。陈先生以本书向当年推荐自己入史语所的几位老先生致敬,希望无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前辈学者渐次凋零,民国学风式微沦替,陈先生坦言自己已是“史语所旧学传统最后一个残垒”。现在的学风急于求成,“研究的人变多了,但读书人变少了”,自己则不惮“逆风而行”,以“抵抗流行的学风和研究,不管是精神上或方法论上”。陈先生指出,自己倾心于“阐幽扶微”,会刻意关注一些重要而长期被忽略的学者,或重要学者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这本《论丛》,对陈先生而言,如在高山攀爬时所见的一些景观意趣,“我无意攀登峰顶,我只是随性的在清代学术这座连绵的大山里,探索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原生态景观,如是而已。”最后,陈先生还预告未来会另编《清代经学研究》一书,收录有关清代经学的部分成果,并计划撰写《皮锡瑞〈经学历史〉得失论》一文,作为研究清代经学的总结。
吴飞教授率先分享了自己对陈先生治学的三重印象:初读陈先生文章,会为其考据功夫之精细详密惊叹;再读后,则会叹服于他从蛛丝马迹中得到重大发现的能力;而等读了更多、了解更深后,便逐渐领略到陈先生惊人的历史洞察力。他的考证、辨伪如侦探破案,令人拍案叫绝。他仿佛就生活在清代学者当中,可以洞悉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同时又充满同情与爱护。陈先生的这本《清代学术史丛考》,着实嘉惠学林,其中对很多经学家的生卒年代、事迹作出新的考证,可以作为我们重新理解清代学术人物的新起点;对清代学术史上长期被遮蔽、但实际上很重要的人物的发掘,可以订正我们以往对清代学术整体图景的认知;对重要学者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新发现,则颠覆了我们对清代学术流派、关系的某些定论与成见;对一些学说的重新驳正,则为我们提供重新理解清代学术史的宝贵契机。
清代学术史、经学史研究,因为时代相近,保存下来的材料非常之多,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还有待考察。理解清代学术史,有多重路径:或以清代考据学为中心开展研究,或从政治文化入手理解学术,或从经义之变视角做出分析。陈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学术史研究,关注的不是书、学说或流派,而是人。他从经学家的历史入手,又兼擅上述三重路径的优长之处。通过并超越以往学术史研究重视的文献、学派、学术,看到活生生的人,这是陈先生给予我们的莫大启发。
 陈璧生教授直言,对《清代学术史丛考》的一个强烈感受,在于陈鸿森先生的研究是对以梁启超、钱穆为代表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典范的极大突破。近百年来,虽然材料层出不穷,知识日益积累,但清代学术研究的大框架依然未变,一直笼罩在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阴影”下。陈璧生教授认为,若要在梁、钱二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可以有两个方向:其一,经疏之学,即将经疏理解为经学史,而非学术史,来检讨清代经疏的得失,以及经疏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其二,人物考察,即在认定学术人物的思想派别属性之前,对清代人物生平、文献、思想进行系统细致的考察。陈鸿森先生以自己深厚的汉唐学术理论背景和考据功力,身体力行,为后学示范了如何突破旧的研究典范。他的清代学术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侧重人物,比较典型的是一系列年谱著作;其次,侧重文献,或以文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
陈璧生教授直言,对《清代学术史丛考》的一个强烈感受,在于陈鸿森先生的研究是对以梁启超、钱穆为代表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典范的极大突破。近百年来,虽然材料层出不穷,知识日益积累,但清代学术研究的大框架依然未变,一直笼罩在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阴影”下。陈璧生教授认为,若要在梁、钱二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可以有两个方向:其一,经疏之学,即将经疏理解为经学史,而非学术史,来检讨清代经疏的得失,以及经疏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其二,人物考察,即在认定学术人物的思想派别属性之前,对清代人物生平、文献、思想进行系统细致的考察。陈鸿森先生以自己深厚的汉唐学术理论背景和考据功力,身体力行,为后学示范了如何突破旧的研究典范。他的清代学术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侧重人物,比较典型的是一系列年谱著作;其次,侧重文献,或以文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
《清代学术史丛考》一书集中于对清代学术人物的考察。对清代学术研究而言,启发之处至少有两点:把清代学术人物还原成活生生的人;重新表彰清代学术史上的“失踪者”。陈先生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把人看成活人,则其说也为活事,所以可以更好的进行考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以书为中心的研究的不足。陈先生的著作,呈现了对清代学术研究如何达到细致入微。而陈先生本人,则承载着一种老派学术研究者的“樵夫”精神。而如果清代学术研究要实现对近百年前的超越,则需要涌向出更多如陈先生一般沉浸在清代学术大山中的“樵夫”。
董婧宸老师则结合自己对传统小学的研究,讨论陈先生著作带来的启发。她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从江藩、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前贤的著作进入清代学术世界,但往往得到的仅是抽象的、概括的学术史脉络,以及“录鬼簿”、“书帐录”式的人名和书名的集合,这种扁平化的学术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去准确、深入地理解清代学术史呢?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意识又在哪里?《清代学术史丛考》的“入山问樵”,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期待。
陈先生通过对清代学术著作、学者生平及相关的专题研究,为我们揭开一张立体而生动的学术网络的神秘面纱。他主要从事三项工作:编订遗文,让一些清代学者(有的声名显赫,有的身后寂寥)散落各地的遗文佚稿重见天日;新撰或订补年谱,考订史实,知人论世,在时间和空间的框架中,定格清代学者的学术探索之路;清理学术史公案,准确还原相关学术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并评价相关学者的学术特色。无论我们是否认同陈先生的学术观点,都不得不承认他的文章“干货满满”。董婧宸老师认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研究,如陈先生一般,能深入到第一手材料中,把握整体框架,同时深入细节,敏锐地捕捉学术思潮,生动地把握学术生态,并准确理解和评价每一位学人的学术性情、学术兴趣乃至学术成就。
 张涛教授从研究进路、方法和关怀三个角度谈及对陈鸿森先生新书的感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学者既可以走历史的路数,从时代氛围、个人遭遇等历史背景入手,也可以循学术的脉络,从经学、小学等具体学问入手。陈先生的论文集,则兼具学术进路的深度与历史进路的广度。有人不解,陈先生的考察对象多非公认的一流学者,对一流学者的关注又多非其主要面向,这样的研究能有多大价值呢?张涛教授提醒到,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则会通过陈先生的文章,看到清代学者一般的著书习惯,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而这却是以往只关注一流学者的主要面向的研究所难以呈现的。
张涛教授从研究进路、方法和关怀三个角度谈及对陈鸿森先生新书的感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学者既可以走历史的路数,从时代氛围、个人遭遇等历史背景入手,也可以循学术的脉络,从经学、小学等具体学问入手。陈先生的论文集,则兼具学术进路的深度与历史进路的广度。有人不解,陈先生的考察对象多非公认的一流学者,对一流学者的关注又多非其主要面向,这样的研究能有多大价值呢?张涛教授提醒到,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则会通过陈先生的文章,看到清代学者一般的著书习惯,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而这却是以往只关注一流学者的主要面向的研究所难以呈现的。
陈先生的方法是考据,但考据有不同层次。考据并非全由史料说话,如何将史料运用到研究中,则体现着研究者的知识底蕴、研究框架和学术功力,在不同史料的缝隙中作出有说服力的猜想,正是陈先生本领高超之处。陈先生对小人物的关怀,对人作为本体的关注,让他既看到光,又看到影,让冰冷的考据背后,蕴涵着深厚的温情。
陆胤教授说,在陈先生的著作中有一股“气”,有时是浩然正气,有时是内转潜气,有时则是不平之气。陈先生的清代学术史,与我们以往认为的学术史不同。清代学术史的传统路线,是由章、梁、钱等先生建立的,他们都把大量篇幅放在思想升降这样的大线条上。陆胤教授认为,理想的“学术史”,应当深入一代学术的内部而贯通之,以人物境遇为中心,且有当代学人基于前修经验的精神反思和自我表达,既要避免“没有学术的学术史”,也要警惕“没有人的学术史”。陈先生的书便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既有学术自身的深度和广度,又有体会人性普遍处境的温度。
陈先生以汉唐经学为基础,贯通音韵、文字、训诂、版本、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令他在看问题时,不限于某个学科的视域,而能综合各方面知识,站在与乾嘉学者同样的高度和广度上做出判断,得出更厚实的结论。此外,陈先生还非常善于安排文章结构,他会是先呈现论证或辨伪的过程,而将最重要的证据放在最后,图穷匕见,可见陈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在考据过程中带出学术史的丰富与歧趋,为此不惜散步“烟雾弹”,读来宛如侦探小说。
学术史的考据,从客观开始,将问题本身的是非搞清楚,最后则通向主观,即知人论世,把握人物的心态,正如陈鸿森先生所言,自己希望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生员层次)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长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现象,以及清代社会某种上下略食而又相互依存的学术生态链。”学术史是当代学人基于前辈经验所作出的、针对当下的精神反思和自我表达,而在陈鸿森先生的书中,虽然研究的是两百年前的问题,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活人的温度,这是一种“有我”的考据。
 李霖教授首先分享了十年前与陈鸿森先生的一段回忆:“十年前,有机会与陈鸿森先生一起吃饭,陈先生问我正在读什么书,我说我最近在看陈乔枞和王先谦的三家《诗》研究,陈先生忽然就说:‘王先谦的书改陈乔枞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是错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印象很深。后来我才知道陈先生早年在一篇有关臧庸《韩诗遗说》的文章中,研究过相关问题。陈先生的观点其实很特殊,今天学界也没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在做一个研究时,背后其实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李霖教授首先分享了十年前与陈鸿森先生的一段回忆:“十年前,有机会与陈鸿森先生一起吃饭,陈先生问我正在读什么书,我说我最近在看陈乔枞和王先谦的三家《诗》研究,陈先生忽然就说:‘王先谦的书改陈乔枞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是错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印象很深。后来我才知道陈先生早年在一篇有关臧庸《韩诗遗说》的文章中,研究过相关问题。陈先生的观点其实很特殊,今天学界也没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在做一个研究时,背后其实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李霖教授认为,陈先生绝对有能力做任何断代的经学史研究,但他选择清代作为默默耕耘三四十年的大山,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代留下足够多的资料供后人驰骋,对研究者来说,清代是一个可以“下定论”的断代。在研究对象上,相比那些“光芒万丈”的学者、史事,陈先生似乎更关注所谓暗部、影子。李霖教授指出,陈先生所做的绝非“填补空白”的研究,他关注的也是乾嘉时代众人服膺的一流学者,只不过他们的重要性由于某些原因被历史遮蔽罢了。在研究方法上,陈先生之所以能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做出“新”突破,并非由于用了什么新方法,相反,他本持的恰恰是旧方法——所谓“旧学之残垒”,即古之考据学,今之文献学、历史学。
梁启超的学术史框架影响深远,但他显然不是站在纯粹的学术立场上著书立说,他本人也并非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动机,深受当下时局的影响,仿佛是在向清人要东西,看乾嘉学者能否为二十世纪初的救亡图存提供答案。出于这样的动机,自然会遮蔽很多问题。相反,陈先生对于清代学术,是无所求的。正因如此,他的考察才是立得住的。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樵夫”,所描述的清代学术史是原生态的,胜过之前那些粗线条的学术史。李霖教授坦言,自己并不如其他老师一般期待陈先生再撰成一部新的清代学术史,因为从陈先生的立意来看,他似乎一直拒绝某种单调的风景,而是更喜欢从不同的路径,赏玩清代学术这座五光十色的大山。
张琦老师通过回顾陈鸿森先生有关高邮王氏四种的实际作者问题的讨论,提出陈先生治学的三个特点:注重清人著作的内证;善于还原清代学术的现场;善于书信系年和利用。正是这些特点,使陈先生的学术史研究“充实而有光辉”。
 最后,张琦老师接续陈先生的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就不分卷本《经义述闻》的作者问题展开讨论,特别聚焦于成书过程和相关时间节点。张琦老师认为,通过对《昭代经书手简》的相关书信系年,可知乾嘉诸儒多于嘉庆十年或稍晚获寄不分卷本《经义述闻》,再结合焦循得书的特殊情况,可以论定不分卷本《经义述闻》直到嘉庆十年秋才刊刻完成,自叙所署的嘉庆二年并非刊刻时间;通过对不分卷本稿本的稿纸及按语称谓进行分类和分析,可以推测,在已经完成110条稿本的基础上,王氏父子决定正式撰著《经义述闻》,由王引之撰写自叙(时为嘉庆二年),案语称谓定型为“引之谨案”和“家大人曰”,并将《大戴礼》和《国语》二种视为“经”收入。《通说》则很可能是最晚撰写的;不分卷本稿本有六例“引之案”被改为“家大人曰”的条目,却没有出现“念孙案”“家大人曰”改为“引之谨案”的情况。三十二卷本《大戴礼》“贵其能以让也”条同样存在“引之谨案”被改为“家大人曰”的情况,但其草稿却为王念孙所撰,显示出王氏父子之间互相推让的心态。而有关作者的问题,可以结合稿本展开进一步研究。
最后,张琦老师接续陈先生的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就不分卷本《经义述闻》的作者问题展开讨论,特别聚焦于成书过程和相关时间节点。张琦老师认为,通过对《昭代经书手简》的相关书信系年,可知乾嘉诸儒多于嘉庆十年或稍晚获寄不分卷本《经义述闻》,再结合焦循得书的特殊情况,可以论定不分卷本《经义述闻》直到嘉庆十年秋才刊刻完成,自叙所署的嘉庆二年并非刊刻时间;通过对不分卷本稿本的稿纸及按语称谓进行分类和分析,可以推测,在已经完成110条稿本的基础上,王氏父子决定正式撰著《经义述闻》,由王引之撰写自叙(时为嘉庆二年),案语称谓定型为“引之谨案”和“家大人曰”,并将《大戴礼》和《国语》二种视为“经”收入。《通说》则很可能是最晚撰写的;不分卷本稿本有六例“引之案”被改为“家大人曰”的条目,却没有出现“念孙案”“家大人曰”改为“引之谨案”的情况。三十二卷本《大戴礼》“贵其能以让也”条同样存在“引之谨案”被改为“家大人曰”的情况,但其草稿却为王念孙所撰,显示出王氏父子之间互相推让的心态。而有关作者的问题,可以结合稿本展开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