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1月,应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教授作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来校做四次演讲,就其反功利主义与共生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了介绍。11月15日,迦耶教授在他位于静园二院的办公室内,接受了记者的访谈。以下为访谈实录,访谈人苏婉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章文博士提供了现场翻译。

多数所谓的功利主义批判都具有两面性和妥协性
问: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其实由来已久。比如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某些新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论体系,都建立在对功利主义的反省之上。尤其罗尔斯的重要著作《正义论》正是声称是要完成这样一项批判性探索。不过,您所引领的“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MAUSS)似乎与以上的路径存在本质区别,您是否认为此前的批判并不彻底或者说存在某种妥协?而选择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思想来作为这场运动的基点并创立《莫斯评论》杂志,是否代表着对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统的传承?
答:的确,马克思主义、法国近代的福柯其实都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批判,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批判是不完整的,甚至说是滑向了一个失败的境地。
首先我想讲讲马克思主义的不足。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其实极为反对将功利性置于事物价值的首位,他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提出了非常系统的批评,在他看来,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杂货店式的功利主义,因为他把很多东西都囊括进了功利主义的范畴之中。但是悖论紧接着出现了,马克思继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现象时反而又把利益的取舍放在第一位。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极其反对功利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本质上又是功利主义的;他反对经济主义,但是他的学说中有很多经济主义的成分;他反对科学主义,但是又受到科学主义很大的影响;他反对人道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是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两面性使其学说更加具有丰富性,但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罗尔斯则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承认自己是反对功利主义的,他特别反对一种将人类的利益、功用放在第一位的所谓的“完美主义倾向”。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他表面上如此反对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但在他真正写作《正义论》的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他最终又被迫将这种最初排斥的经济人假设引入书中,为了讲述正义,他还是着重将人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写入所谓关于正义的理论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尔斯的理论至少是具有倾向性的功利主义,或者说在整体上具有滑向功利主义的趋势,他不断地计算着人类的好处和优点等等。因此,与其说罗尔斯发明的是一种正义论,不如说是一种民主的理想、政治的理想。正如此前一位以色列的哲学家所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更像是一种关于社会礼仪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关于正义的理论。
我还想谈谈福柯。我们都知道福柯的思想深受尼采影响,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希望能在福柯的理论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式的、反功利主义的痕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那本《生命政治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就会发现此书正是一个集功利主义大成的著作。福柯在其中详细阐述了关于经济政府的理想,他表面声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他所支持的经济政府恰恰是功利的政府,因为它主要只是以为公民施以最小的限制为核心。因此我认为福柯本质上也是功利主义的,他其实更像是德国自由经济主义的阵营。
毫无疑问,“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莫斯评论》的创办和我们围绕莫斯理论所做的其他事,当然都是对法国社会学传统的传承。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教条主义,也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封闭在法国社会学的传统之中,我们也要向其他国家的学术传统开放,比如在我看来,如果想要真正创立反功利主义,就要在莫斯理论的基础上吸收马克斯·韦伯的学说。
永恒的良性循环并不存在
问:莫斯的经典礼物范式包括赠礼-接受-回礼三重义务环节,加入您所提出的第四重“要求”的环节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您在讲座中指出,在这个循环中,礼物得以在人、群体、国家、神灵之间流动,从而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石。但是,礼物模式摆动在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常常瞬即转换。那么,如何能够确保礼物的良性循环趋向?
答:事实上,我们无法确保良性循环的实现。不过,礼物流动的循环是良性还是恶性,大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存在于礼物循环的内部,要求在内部的参与方——也就是给予者、获赠者——之间达成平衡,要求礼物的人不应要求过多,但其要求也应该达到一定足够的分量;而对于给予者而言,给予的东西也不该过多或过少,而要恰好体现出对另一方的尊重。只有当这两方在礼物的分量和内涵上达到平衡时,才是从内部实现礼物良性循环的最佳条件。第二个条件存在于礼物循环的外部,大致可以界定为社会关系的秩序和它之间的层级制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容量越来越大,社会成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我们就需要一些外在的层级制度来帮助我们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宗教和政治。这种制度能够逐渐形成礼物范式的固态化。满足以上两个内外条件,或许能够促进一种礼物的良性循环。
“我们恐怕进入了一个反向的极权主义时代”
问:您在《新古典主义社会学:当今社会理论的展望》(2015)和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HSviews的访谈(2007)中提到,我们身处于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破碎的知识、组织和话题——世界正在走向分崩离析。当代社会科学也被过分的专业化所分门别类,即使是一个学科内部领域之间也无法对话,而这种肢解伴随着在方法上对于经济主义的滥用。您在讲座中也谈到,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经济学模式的帝国主义”就蔓延在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生物学的研究当中。在您看来,世界和社会科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度精细化的现象?以及经济学模式的诱惑力和有限性分别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我想,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一个较为浅层的原因。我们身处的社会的数量级正在变大,全球化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变得更多,一切问题也随之复杂,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增长都是造成碎片化的原因。而在文化成员不相熟的情况下,市场和商品则成为了最便捷的沟通语言。其次则是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我们如果追溯到碎片化问题的上游就会发现,我们所经历的20世纪是一个有着太多极权主义的时代,比如纳粹,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上的极权主义。
表面上我们已经战胜了这些形式的极权主义,或者说至少是在西方、在欧洲是如此,但事实上我们恐怕进入了一个反向的极权主义时代,也即所谓的碎片化主义(parcellisme)。这个碎片化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联在于,极权主义牺牲的是所有的个人利益,而碎片化主义则是要牺牲所有与集体有关的事物。这其实也并非不合理,因为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市场的极权主义时期,从而必须把集体主义都牺牲掉才能让一切更适宜市场的需求。因此,从源流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极权主义、碎片化主义都是异根同生的。
问:您刚才谈到牺牲一切集体性不啻于是一种反向的极权主义,那么,如果我的理解无误,您的著述似乎意在提出某种集体主义的呼吁。但自启蒙运动以来,个人主义一直被作为保证权利和自由的旗帜。尤其大规模战争和经济萧条之后,相对于个人主义,人们对集体主义抱有更多的反省和不安。您如何看待这种对于集体主义的警惕和不安?
答:其实我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完全的集体主义。共生主义理论正是要说明这一点。对我来说,要创造一个宜居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在两个方面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集体的自由,我之所以反对极权主义,是因为极权主义会牺牲个人的自由;而我反对它的反面——碎片化主义,是因为它会牺牲集体的自由,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间道路,寻求一种平衡,而非从绝对的个人主义过渡到绝对的集体主义。
寻求普世价值的多元表达
问:2013年您联合六十四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联合起草了《共生主义宣言》(Manifeste convivialiste),其中提出了应对族群冲突、贫富差距、生态灾难等一系列人类危机的理论方案。那么“共生主义”与反功利主义有哪些内在关联?共生主义所提出的“多元-普世主义”极富有理想和激情,但它与多元主义和普世主义都存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是否来自于您对二者的综合和批判?它们分别具体错在哪里?您的替代方案是否能够有效地纠正这些错误?
答:从历史的源流上来看,共生主义和反功利主义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本人同时参与到这两个运动中,而且也是它们的积极倡导者。反功利主义可以追溯到马塞尔·莫斯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莫斯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思想家,他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活动家,我曾说过,他是20世纪初期法国社会党的重要领袖让·饶勒的左膀右臂,一直追随饶勒斯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但必须要指出,莫斯支持的社会主义可能跟惯常理解上的社会主义存在不同,他更强调一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我想,莫斯这样的一些观点和激进的态度对现在来说已经不太适合了,所以我才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理论,希望能将其应用到当下的现实中,才有了现在的共生主义。
而多元-普适主义则是借鉴了多元主义和普世主义的优点。其实,这两种主义都极易让我们陷入到一种相对主义的陷阱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多元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又都是普世的,但如果把它们分离开来,仅就某个主义来说又都不是正确的。尤其普世主义更多地是来自西方的思想传统,追求的是将西方的价值观传播到整个世界,在当下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的思想传统中的普适主义,寻求一些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目光移向每个文化的时候,应该允许每个文化都享有话语权,按照他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来重塑这些普世价值观,这就是多元主义的意涵所在。
事实上,多元-普世主义也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它来自于一个印度的哲学家。印度看似缺乏“人权”的概念,但其实印地语中有一个和“人权”相通的词汇——“dharma”,大义也指人生而为人的权利、人类存在的荣誉感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基本观念既是普世的,又能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其独有的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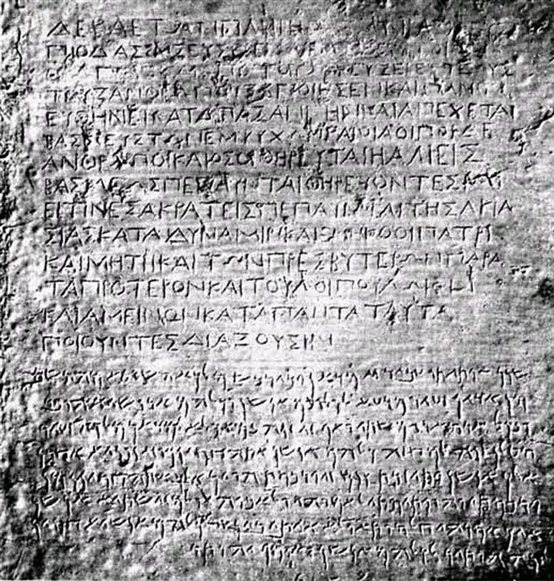
印度看似缺乏“人权”的概念,但其实印地语中有一个和“人权”相通的词汇——“dharma”,大义也指人生而为人的权利、人类存在的荣誉感等。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反功利主义因素
问:近期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功利主义提出了批判,他们中一些人为此诉诸您在讲座中反复提到的西方反功利主义思想,但也有不少人诉诸中国文明的古代思想资源。您对这些潮流怎么看?尤其是关于共生主义,我想,中国古代的儒道两家都存在相似看法的。您认为这些古老看法是否具有可以挖掘的当代价值?
答:中国的古代思想存在许多与西方反功利主义思想的共通之处。尤其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于当代来讲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挖掘的无尽财富。此前跟王铭铭教授和渠敬东教授的交谈中,他们都跟我提到礼物范式与中国思想存在诸多的共鸣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思想中找到近似于礼物范式的说法。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去回顾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回顾,一方面将其改造得更加适应当下的时代。
对立其实并不可怕
问:《礼物》是真正关于“完整的人”的研究,我记得其中有一处很精彩的表述:“对立却不互相残杀,给予却不牺牲自己”。礼物模式弥合了人性层面的利己与利他,这是否也意味着在冲突与合作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我们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体现更多的礼物精神?
答:很高兴你能注意到这句话,因为对我来说,这的确是莫斯最中心的论点之一。我认为“对立却不互相残杀”其实是一切民主制度和民主理想的基石,对立其实并不应当被视为遗憾的或者说不正当的事情,事实上对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其实是打破社会等级制度的第一步。传统的伊斯兰主义极其反对对立、冲突和争执,“fitna”这个词汇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因为难以接受对立,因此传统的伊斯兰社会是很难接受民主的价值观的。我想,等级制度一向森严的古代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过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允许一定对立的礼物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主传统是非常有必要引入到社会制度中的,尤其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中。
我曾经和法国的高层官员交谈,他们也认为其实法国的政坛正处一种矛盾之中,一面是民主的传统,另一面则要面对当下较为紧迫的经济问题,所以长期的民主理想和短期的问题常存在一定冲突。从另一角度看,法国也是一个阶层相对固化的精英式社会,我们有一些精英的专门学校,所有从这些学校中走入社会的精英似乎知道他们天生就属于这个社会的上层。但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打破这种阶级传统,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让这种对立公开化,这是目前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
作为公民的知识分子使命
问:法国一直是世界重要思潮的引领者,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诸多的杰出思想。这与法国具有的良好的知识分子传统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中国也具有相似的知识分子传统。那么,您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
答: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和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文学传统。很多法国作家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文学传统是滋养知识分子传统的源泉之一。但我不得不说,这种知识分子传统正在丢失和逐步消弭。萨特之后,其实福柯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萨特的一种复仇,他把萨特那种认为全民皆知识分子和全民参政的传统又转回了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传统。可我必须要说,自福柯之后法国没有出过特别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了,每个领域都有专家,可是没有再产生划时代的著作,对此我深表遗憾。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首先是创造一定质量的作品,不管是在文学上还是科学上,并且更重要的是承担好作为一个公民的使命,要成真正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一份子。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担任伦理和政治上的双重使命,这也是涂尔干在最开始创立社会学时提到的理想之一。如果不能肩负这种使命,那么社会学注定将是一种贫瘠的科学,一种无法产出的科学,这不仅是涂尔干的说法,也是韦伯的说法。社会学其实不应在树立某些标准方面有所迟疑,而应为人类行为塑造一些原则性的范式,这虽然具有教化性,但我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门学科才能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和谐感和统一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共生主义就是要复活一种全民皆参与的集体知识分子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