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法国著名学者、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让-吕克·马利翁教授将于近日访问北京,发表两场公开演讲。我们在此附上南开大学哲学院贾江鸿老师的文章《马里翁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的解读》,以便大家了解马里翁教授的主要思想和学术贡献。
马里翁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的解读
当代法国哲学家马里翁(Jean-LucMarion)因为其重要的宗教哲学和现象学思想而闻名于世,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马里翁的这两项工作都和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另一项工作,即笛卡尔哲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通过大致的阅读,我们就可发现,马里翁的这三个工作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形而上学,因此,梳理和反思马里翁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而是形而上学体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因为一方面,这本身可以充实我们对笛卡尔哲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去尽可能地发掘笛卡尔哲学所可能蕴含的新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去厘清马里翁自身哲学的框架和内涵提供一定的基础。

图为马里翁
一、《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解读
在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展开研究的时候,马里翁首先借用了海德格尔在《同一与差异》中对形而上学的一个定义,即一种本体-神学-论(onto-théo-logie)的思想。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本体-神学-论的构成,这种构成源自于一种在本体论上的作为地基的存在与其他被奠基的、被给予的、相互之间彼此区分又彼此关联的诸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在马里翁看来,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样的本体-神学-论思想,或者说这种形而上学基本上包含三个最基本的内涵。首先,上帝必须作为一个最根本的存在而位于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中;其次,在这样的体系中,所有其他的存在者都必须奠基于这个最根本的存在之上;第三,这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或者说最基本的存在的奠基性作用是通过自因概念而得以实现的。马里翁认为,这样的思想内涵在笛卡尔的哲学中是存在的,而且,更明确地说,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形而上学思想,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本体-神学-论框架。
在1991年出版的《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中,马里翁详尽地考察了笛卡尔在1637年完成的《谈谈方法》中的形而上学内涵。一些学者认为,《谈谈方法》,或者说由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法所构建起来的具有统一性的、全新的科学之中,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位置的(Jean-Luc Marion,1991:41)。马里翁则在吸收自己的导师阿勒格耶(F.Alquié)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很明显具有一种清晰的形而上学意图,并且也建构了一种较为完善的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本体-神学-论的思想。马里翁重点分析了《谈谈方法》的第四部分中笛卡尔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命题“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编者注)的内涵。在他看来,在《谈谈方法》中,尽管笛卡尔并没有提出一种“夸张的怀疑”的思想(这一点对后来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形而上学的建构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笛卡尔恰恰更明确地建构了一种更为完善的(相比于《第一哲学沉思集》),相关于自我的一种形而上学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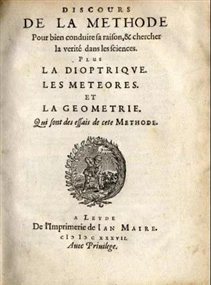
图为笛卡尔《谈谈方法》1637年版书影
马里翁引用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两段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注意到这个真理‘ego cogito, ergo sum’,它是如此的确定和可靠,以至于任何怀疑者的极度怪异的假定都不能对它有丝毫的撼动,我觉得,我能毫不迟疑地接受它,把它作为我所追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2000:26);“我们已经注意到‘ego cogito, ergo sum’之所以使我确信我所讲的是真理,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要想进行思维,就必须存在,因此我认为可以采纳一个一般的说法,即凡是我十分清楚地、极其分明地认识到的东西,就都是真的”(同上,28)。马里翁认为这两段话语和笛卡尔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相关表述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哲学沉思集》使用了一个和《谈谈方法》所不同的表述“ego sum, ego existo” (“我在,我存在”——编者注)(笛卡尔,1998:23;AT VII:25,12),在马里翁看来,这个表述不仅排除了所有这个表述中的相关术语之间的逻辑关联,而且还特别地排除了那个陈述性的思维自身,即cogito,也就是说,在1637年的《谈谈方法》中,思维是被包含在笛卡尔的著名命题之中的,而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思维则消失了。进一步来说,在1641年的表述中,自我不再通过一个客观的陈述去构想一个连接存在和思维的命题来达到他的存在,而是通过一个在完成了自己的述行行为的在思维的东西而达到其存在的。马里翁指出,1641年的这个表述,它突出的是这个述行行为的当下性,如果说在1637年,自我由于不承认任何时间性的因素,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却真正地达到了他的存在的话,那么很显然,在1641年笛卡尔的这个表述由于它突出的是这个述行行为的当下性,因而实际上达到的就是一种不太确定的存在。如果说1637年的自我由于其非时间性,而被笛卡尔马上当作一个他“所追寻的哲学的第一原理”的话,1641年的自我由于是当下的,因此也并没有被笛卡尔断言它就是一个原理。其次,马里翁还指出,在1641年,实体这个概念直到《第三沉思》的后半段才出现,即只有在加入了上帝的存在的后天证明之后,笛卡尔才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实体,自我的实体性才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马里翁认为其道理就在于,在一开始,自我并不是持续绵延的,自我并不属于原理的行列,因此他并不具有实体性,而要想达到他的实体性,就必须先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实体性,然后通过从无限向有限的反转,来推论人类精神的实体性。但是在1637年的《谈谈方法》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我思一下子就达到了他的实体性存在,笛卡尔很明确地说道,“由此,我知道我是一个实体,我的所有本质或属性只是思维”(笛卡尔,2000:28)。这意味着,《谈谈方法》特别地通过实体这个概念,马上就赋予了自我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内涵,而相反,《第一哲学沉思集》则在这里恰恰欠缺这种内涵,因而也就抹消了自我的形而上学特权。
在马里翁看来,正是由于《谈谈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确定性的,可以被称作”第一原理”的命题“ego cogito, ergo sum”,正是由于它建构了一种思维和存在的必然关联,提出了一个作为实体的自我的概念,由此它也就建构了一种“自我的创世学”(une protologie de l’égo)以及一种准-本体论(quasi-ontologie)(Marion,1991:65),而这样一种创世学和准-本体论就足以使我们去确定一门形而上学,一门本体-神学-论了。这是马里翁发掘的笛卡尔的哲学中的第一种本体-神学-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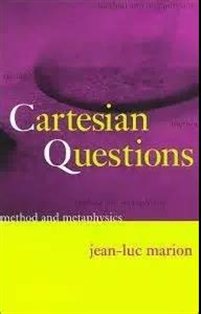
图为马里翁《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书影
马里翁认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进一步建构了第二种不同的形而上学,或者说第二种不同的本体-神学-论。相比于《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提供了一种可以被提升为“怀疑的总体”高度的“夸张的怀疑”的思想,即笛卡尔引入了一个“邪恶的精灵”,进而引入了一个最终不可怀疑的上帝,而这种夸张的怀疑在《谈谈方法》中是缺席的。其次,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改造了自己在《谈谈方法》中的命题,把《谈谈方法》中的第一命题“ego cogito, ergo sum”转换为了“ego sum, ego existo”,这种改造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它抹消了自我的那种形而上学特权(自我不再首先是一个实体,其自身并不能是持续绵延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因为上帝概念的介入,笛卡尔也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的高度。第三,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引入了一个自因的概念,一个因果性原理的概念,从而确立了上帝的实体性内涵,确立它的形而上学地位,“现在,通过自然之光,我们明显地看出,在动力的和总的原因里一定有至少和在它的结果里同样多的实在性”(笛卡尔,1998:40;AT VII:40,21-23)。正是基于这些内容,马里翁最后总结道,“在《第三沉思》中,随着因果性概念的出现,随着实体概念的显现,笛卡尔在这里最终完全放弃了他在《谈谈方法》中通过思维而建构的那种本体-神学-论思想”,同时,他也建构了一种新的“关于第一因的本体-神学-论”(Marion,1991:72)。
我们该如何来看待马里翁的这种解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展开。首先,马里翁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对笛卡尔的本体-神学-论的理解是借助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定义来展开的,由此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本体-神学-论是完全符合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定义的话(上帝的奠基性以及自因的概念),那么《谈谈方法》中的本体-神学-论,即以自我为奠基性的所谓的形而上学,看起来就是有些问题的。自我难道真的可以具有一种神学的、奠基性的内涵?自我难道真的可以用自因的概念来加以界定?要知道,自因指的是一事物是自己乃至所有其他事物的原因,它自己的本质就是存在,但是,当我们说自我是一个思维实体,是存在的时候,这仅仅是说自我是一个具有存在的思维,这并不意味着自我的本质就是存在。其次,以笛卡尔自身的哲学为标准,马里翁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解读是否完全符合笛卡尔本人,或者说笛卡尔著作的原意?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难道没有涉及上帝的讨论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尽管正如马里翁所言,笛卡尔在这里并没有涉及一种完全的上帝存在的证明思想(这一点论断是和他的导师阿勒格耶是不同的),但是笛卡尔毕竟讨论到了上帝的存在问题,因为在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命题“ego cogito, ergosum”之后,笛卡尔明确地指出存在着一个完满的上帝,他“本身具有我能想到的一切的完满,他就是上帝”(笛卡尔,2000:29)。由此,问题就是,我们能在撇开上帝的存在的情况下,而单独地构建一种自我的形而上学吗?在1630年11月15日写给麦尔塞纳神父的信中,笛卡尔曾经写道,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点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存在,因为他们是与物体相分离的,他们的不朽正在于此”(Descartes,1997:258-259),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谈谈方法》中的本体-神学-论思想主要是一种以自我(灵魂)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而《第一哲学沉思集》则是以上帝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吗?笛卡尔会同意说他自己在当时的形而上学是两种不同的本体-神学-论思想吗?
二、《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与上帝》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进一步解读
马里翁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所蕴含的困难。在《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中,他在讨论了《谈谈方法》的形而上学意义——以思维为基础的本体-神学-论——之后,就曾经指出,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言,他在《谈谈方法》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只能是一个过渡,即只能是一个有待克服,或有待超越的阶段性成果。换言之,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真正建构是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才完成的,这意味着笛卡尔的成熟的形而上学思想就应该是一种相关于上帝的本体-神学-论,而自我则正是在这种框架下的一个阶段性的,也就是说是非基础性的产物。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马里翁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在《第二沉思》中,通过夸张的怀疑,笛卡尔最终获得了一个这样的表达式“ego sum, ego existo”,马里翁指出,这时的自我的是一个非实体性的自我;而在《第三沉思》中,通过借助因果性的原理,笛卡尔确立了上帝的实体身份,并且在此基础上最终也确立的了自我的一种实体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初步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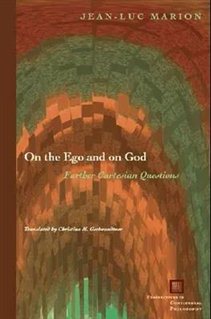
图为马里翁《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与上帝》书影
但是,在5年之后出版的《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与上帝》中,马里翁则把自己的目光完全锁定在《第二沉思》的文本上,进而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给出了一种更加大胆、新颖而且具有冲击性的解读。
马里翁大体上还是延续了他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两种不同解释路径的区分思想,即一种以《谈谈方法》中的表达式“ego cogito, ergo sum”为核心的解释路径和另一种以《第二沉思》的表达式“ego sum, ego existo”为基本依据的解释路径。并且在这一次,马里翁明确地把第一种解释路径称为是一种标准的解释路径,在他的分析中,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等人基本上都坚持的是这样一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解释思路,在马里翁看来,遵循这样的解释思路,笛卡尔的自我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唯我论以及自我分裂的窘境之中。但是,在他看来,笛卡尔实际上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思路,这种思路下的自我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原初的相异性,从而完全可以避开自我分裂与唯我论的陷阱。
马里翁紧密地围绕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的一段文本,并且把这段文本区分为四个片段来展开自己的论证:
1、可是我怎么知道除了我刚才断定为不可靠的那些东西外,还有我们不能丝毫加以怀疑的什么别的东西呢?难道就没有上帝,或者任何其他我称呼他的称谓,把这些想法放在我心里吗?这到不一定,因为也许是我自己就能够产生这些想法。那么至少我,难道我不是什么东西吗?可是我已经否认了我有感官和身体。尽管如此,我犹豫了,因为从这方面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2、难道我就是那么非依靠身体和感官不可,没有它们就不行吗?可是我曾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曾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
3、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我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吧,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能使我什么都不是。
4、所以,在对上面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同时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检验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也必须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即“我是,我存在”这个命题,每当我说出它来时,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时,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笛卡尔,1998:23;AT VII:24,20-25,13)
在第一个片段中,笛卡尔试图去对他在《第一沉思》中的结论,即所有我看到的都是虚假的,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提出一种质疑。为此,笛卡尔追问是否在这里还有没有绝对不能质疑的“某个别的什么东西”。在此,马里翁分析到,这就在根本上涉及到一个他者,一个不太好辨认的剩下来的他者,“某个上帝,或者任何其他我称呼他的称谓”。由此,马里翁认为一个比较奇特的结果出现了:作为一个假设,一个他者甚至在自我之前,在笛卡尔第一次试图超越怀疑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当然,确切地说,这个我们与之交流的对象还是不确定的,是模糊的,是匿名的。是他 “把一些想法放在了我心里”。进一步,在马里翁看来,这个上帝,这个未名的上帝是作为一个和我进行交流的对象而显现出来的。在这里,他还没有存在,没有本质,甚至没有名称,而这足以对我造成欺骗。简言之,笛卡尔在这里的怀疑是在自我和一个不确定的他者之间的对话空间中展开的,自我,在他变成在他身上出现的观念的真实起因的时候,除了他自己,他只肯定一个他者。
在第二个片段中,笛卡尔似乎只是在追问自我的同一性,在确认自我的存在,但是在马里翁看来,这样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马里翁首先注意到了笛卡尔在这里的用语:“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也曾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在他看来,笛卡尔在这里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在《第一沉思》中夸张的怀疑的那种论证,“没有天,没有地”,然而有所不同的是,笛卡尔在这里增加了对精神性东西,对自我的怀疑,而这是在之前并不曾落入夸张的怀疑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这个论证是在试图对“我总是个什么”这样的断言给予否决。如何来理解这种变化?在马里翁看来,笛卡尔在这一片段中接下来的表述给出了一种回答。“绝对不,如果我曾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很显然, 在这里,“我曾相信”,这并不是基于这种确信的内容,相反,笛卡尔考虑的仅仅是这种确信的形式,即不管我相信的内容是什么,至少我自己对它是确信的。 可是,“我曾相信”这样的话语难道不是充分地展现了那由“ego cogito, ergo sum”所蕴含的自我的同一性吗?马里翁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首先,这种由自我获得的相信,它确实并非来自于自我,而是来自于一个“在我的精神中一直存在着的想法”,一个使我们去考虑一个全能的上帝的可能性的想法。由此,自我之所以进入怀疑,这仅仅是因为,依据这种事实性的存在,他提前就被置于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事实面前了。我们可以或者把这个事实看作就是一个想法,或者把它归于一个全能的上帝,或者把它等同于一个不确定的骗子,在任何情况下,在这条所谓的应该把自我仅仅与其自身同一起来的唯我论的道路上,自我实际上都不是在先的,这个在先的位置被某个他者占据了。简言之,笛卡尔遵循的是这样的思路:那处于主体位置上的东西,它的存在在这里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一种相信,一种由某个并不确定的东西在他身上实施的相信,这个不确定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它能使我相信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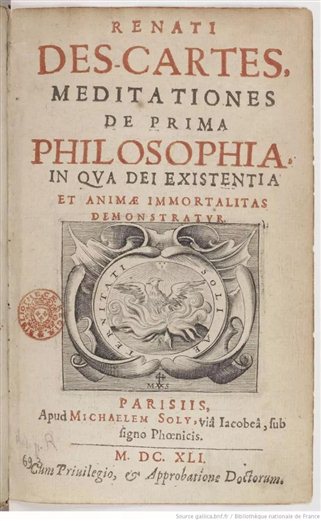
图为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版书影
在马里翁看来,笛卡尔的第三个片段马上用一个明显具有对话性内涵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欺骗我的话,我也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替代了刚才笛卡尔在第二个片段中的那个表述“如果我自己想相信某个东西,那么我一定是存在的”,从而也进一步承认了这种对话的结构。相比于“自己相信”,“如果他欺骗我”这个表述所蕴含的对话性意味就更明显了,这种对话设定了另外一个欺骗我的讲话者,正是他在自我面前招呼着我。因此事实上,当自我承认自己存在的时候,他首先承认的是他仅仅只是一个第二位的存在,他是在一个欺骗性的他者之后出现的。我的存在既不是来自于一个三段式的推论,也非出自一个直观,还不是源自于我的自主的言语行为,不是出自于一种自我感应,而是来自于由一个与我不同的他者对我造成的影响。
马里翁认为,在表面上看起来笛卡尔的第四个片段又重新构建了一个自我的短循环,而没有提到所谓的欺骗者,在这里,“我是,我存在”是通过我来实施并讲出来的。但是,在马里翁看来,那种对话性的结构实际上根本没有消失,而是出现在了一个作为被呼唤者的自我和一个在呼唤的自我(作为他者自身)之间,因为笛卡尔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典型的述行语表述(“每当我说出它的时候”),这显然涉及到一个言语的行为,而一个对话性的框架也就呼之欲出了。这意味着自我是通过他自己的呼唤而诞生的。而且,这种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是一种自我对自身的反思,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自己对自己的表象。而且在这里用该存在着一种自我对自身的称呼,一种面对自身(甚至是针对自身)的一种对话,更明确地说,自我一开始就是出神的。
三、分析和思考
那么如何来理解马里翁在这里对《第二沉思》的这四个片段的分析和解读呢?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笛卡尔这里的前三个片段都是为第四个片段的结论作铺垫和准备的。按照马里翁的分析,笛卡尔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前三个片段表明了这样一个思路,即可能有一个我们不能怀疑的其他的东西(上帝或其他的东西),他在我心里安放了一些思维,或者说他在欺骗我,可是只要如此,那么第四个片段的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即自我必然存在。当我们说有一个上帝或他者在欺骗我,在给我的心里放置了一些思维时,这意味着首先必须承认在上帝或他者和自我之间存在着一个对话的机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存在着一个上帝或者他者对自我的召唤的程序,而正是在这个召唤中,自我出场了。可以看出,相比于在《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和形而上学》,马里翁在这里对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解读显然是不同的(当然,在马里翁看来,它们与《谈谈方法》中的以自我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思想都是不同的,即它们均以上帝为基本的要素,在此,自我是第二位的):在《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和形而上学》中,马里翁更加强调的是上帝作为一种实体的首要性地位,因为自我的实体身份是来自于上帝的,换言之,马里翁是通过《第三沉思》中上帝的登场来消解《第二沉思》中自我的缺憾的;但是现在,马里翁虽然也在强调上帝的首要性地位,但是这里的上帝还是一个没有存在,没有本质的未名的上帝,是一个在召唤着自我的上帝,换言之,马里翁是通过《第二沉思》中的上帝来使得自我登场的。也许对马里翁来说,这两种解释框架可以完美地统一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未名的上帝的召唤,还不具有实体性的自我的登场,上帝的实体性的显现,自我的实体性的构建。

图为笛卡尔纪念邮票
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马里翁真的试图提供一个这样的整体性解释框架的话,这显然是成问题的。当然,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首先应该检验一下马里翁在《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和上帝》中这种解释框架到底是否是成立的。在上述文本的第一个片段里,笛卡尔继续坚持他在《第一沉思》里的结论,即我“根本没有什么感官,物体、形状、广延、运动、地点都不过是我心里虚构出来的”(笛卡尔,1998:22;AT VII:24,16-17),在此,笛卡尔设想,有一个“上帝”,是他把这些想法——显然是上述那些可以的东西,即物体、形状、广延等——放在我心里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笛卡尔接下来的另一句话,“这倒不一定,因为也许是我自己就能够产生这些想法”,因此,即使如马里翁所言,上帝或者一个未名的他者在这里出现了,但是这种出现并非是必然是的,因为我自己也能替代他的作用,遵从笛卡尔的逻辑,在这一片段里,他的目的实际上还是为了寻找那确定无疑的知识的阿基米德支点,只不过他再次强调我可能是虚构了一些自以为真实而实际上完全虚假的东西,或者有一个未名的上帝他把这些虚假的想法放在了我的心里。在第二个片段,笛卡尔继续自己的思考,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即使我自己虚构了一些虚假的东西,但是只要我自己曾相信过什么东西,我自己曾经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不管这个东西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在虚构它们的自我必然是存在的。第三个片段可以说是对第一个片段里的那个可能的上帝的假设的进一步设想,笛卡尔指出,即使我的那些虚假的想法真的是一个上帝般的骗子的杰作,但是无论他怎么骗我,但是这个在受欺骗的我总是存在的吧?在笔者看来,在这里,马里翁对所谓的作为欺骗者的他者的设想虽然是极富新意,极具冲击性的,但是仍然不能摆脱这样一个根本性事实的责难,即上帝的出现仅仅是笛卡尔为了论证自我的存在的一个手段,换言之,上帝和自我都可以充当一个欺骗者的角色,而这个欺骗者之所以被笛卡尔提及,则只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不管我怎么被欺骗(无论是自己欺骗自己,还是被上帝欺骗;无论我被欺骗了什么),但是这个被欺骗的我首先是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马里翁所坚持的那种上帝和自我的对话框架至少是可疑的,进而那种所谓的关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整体性的解释框架就是难以成立的。依据笔者的上述分析,在这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框架更应该是这样的:还并不具有实体性的自我的出场(ego sum, ego existo),上帝的实体性的显现,自我的实体性的构建。明确地说,马里翁在《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和形而上学》中的解读应该是更为合理的,而他在《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与上帝》中的解读则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参考文献:
Descartes, R. , 1964-1978, Oeuvres de Descartes, éd., par C. Adamet P. Tannery , Paris, Vrin.
Descartes, R. , 1997, Oeuvres philosophiques, éd. F.Alquié , v1, Paris, Classique Garnier.
Marion, J-L. ,1991, Questiones cartésiennes : Méthodeet métaphysique, Paris, PUF.
Marion, J-L. ,1996, Questiones cartésiennesII :Sur l’égo et sur Dieu, Paris, PUF.
笛卡尔,2000,《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笛卡尔,1998,《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笛卡尔,1959,《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