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27期、“发现文明:考古学的视野”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周原考古的进展和学术意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曹大志主讲,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兴山评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讲师马赛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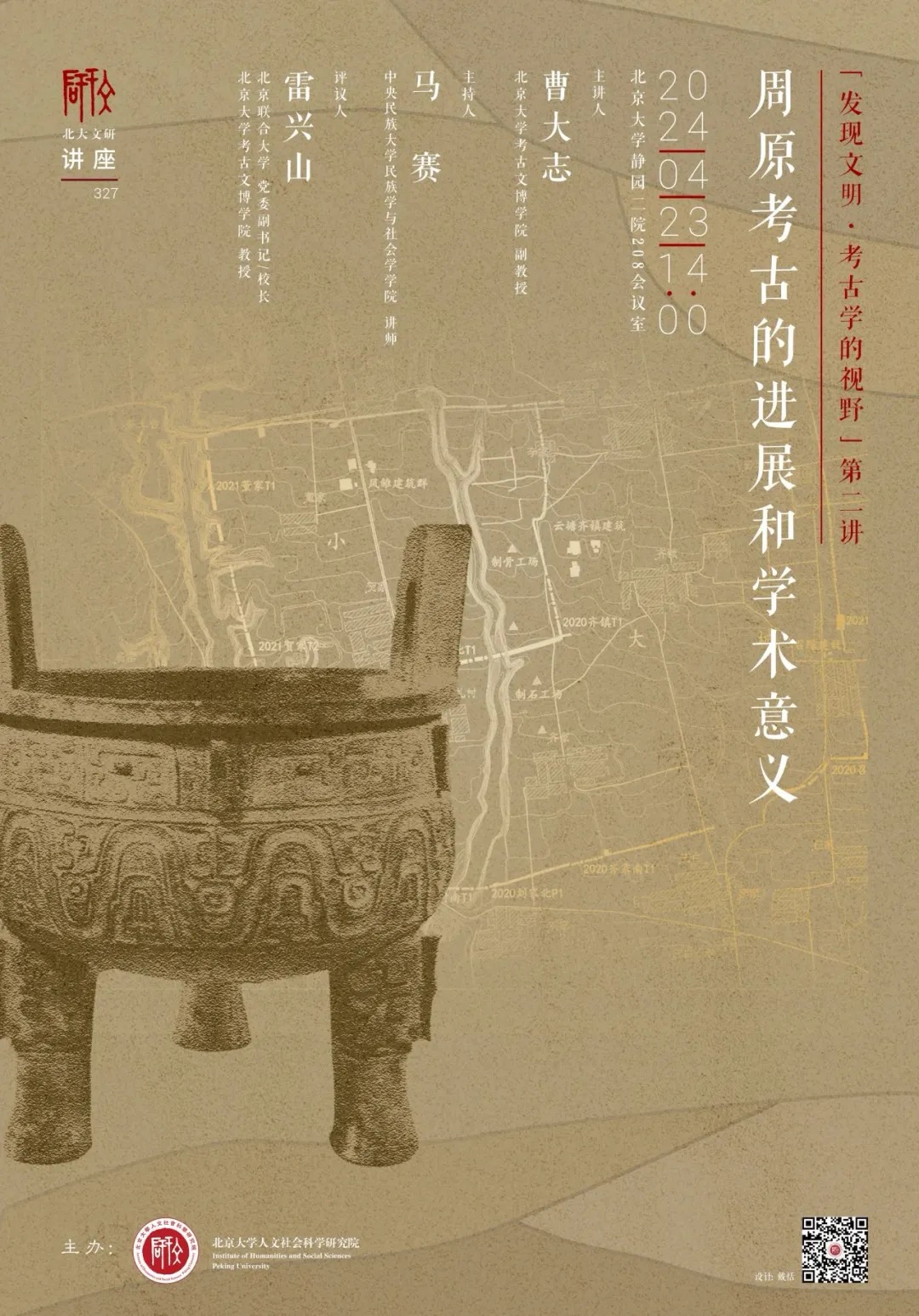
讲座开始前,马赛老师先介绍了周原遗址的学术价值和以往工作情况。周原在周人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聚落。通过长期的考古工作、多次大规模的发掘,我们对周原遗址的认识逐渐清晰。近些年,随着更多田野工作的开展,周原遗址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本次讲座旨在介绍这些新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一、以往工作
曹大志老师首先介绍了周原的地理地貌,回顾了周原考古的历程。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交界处,面积约30平方千米,是商周时期的超大型遗址。这里地处关中盆地西部的渭北黄土台原上,北面不远是北山山系,它的一部分古代叫做岐山。由于黄土沉积、河流侵蚀和渭河谷地下陷,北山山前形成了地势高平的地形——原。周原的意思是周地的原,这个地名在《诗经·大雅》里已经出现。这里南面有秦岭,北面有黄土丘陵,是黄土高原中一块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农业条件非常好。
周原相传是周人兴起之地。由于有《诗经》和汉、唐地理志书的记载,周原的大体位置一直是清楚的。晚清到民国,周原遗址范围内多次出土铜器。1942年,石璋如先生调查确认了扶风、岐山交界一带是文献记载中的周原。1949年之后,周原开始有配合农田水利工程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工作。六七十年代,当地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了贺家墓地的先周、西周墓葬,发掘了齐家遗址。这期间因为平田整地活动,也多次发现铜器窖藏。

▴
周原地貌
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和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在俞伟超、严文明、徐锡台等先生的带领下,发掘了凤雏、召陈两处大型建筑遗址。这是周原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员,影响深远。但是不久后,周原考古工作陷入停滞。80年代,宝鸡市文物工作队、周原博物馆做了很多铜器墓的记录、报道,还有黄堆墓地、刘家墓地的主动发掘工作。
曹大志老师指出,周原一直有断续的考古发现和工作,积累了很多零散的信息,显示了重要性,但作为大遗址,缺少持续性的考古工作,遗址面貌得不到整体认识。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以周原为北大商周组的本科实习地点,开始在周原长期工作,并制定了三方面学术目标:建立遗址的年代谱系;探索聚落形态和遗址性质;解决先周文化的问题。当时最主要的课题是要在考古学文化上和都邑上确定先周(周人灭商之前)的中心。
1999-2001年的两次发掘先后建立了西周和先周时期的文化谱系,但寻找先周都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此周原考古队持续进行田野调查,寻找先周时期的高等级遗存。2002-2003年发掘了李家的铸铜作坊,发现大量西周中晚期的铸铜遗物,是洛阳北窑之外最主要的一次西周铸铜作坊的发掘。2002年,周原考古队发掘了齐家制石作坊。2003年发掘了云塘-齐镇的大型夯土建筑,这是在凤雏、召陈之后揭露的最完整的西周建筑。2014年再次发掘了云塘制骨作坊。
2003年,在“大周原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徐天进老师和当年实习的同学们在距离周原遗址25公里的周公庙遗址发现刻辞甲骨,随后又发现了空心砖、铸铜遗物、夯土建筑、带墓道大墓等遗存。由于当时周原还没有发现先周时期的高等级遗存,尚未显示出在先周时期的地位,老师们也对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有所怀疑,所以之后十年的工作重点便转到了周公庙遗址。从2004年到2011年,持续的考古工作确定了周公庙遗址的性质是周公家族的寀邑,搞清了西周高级贵族寀邑的形态。这期间还在关中西部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调查,发现了水沟、蒋家庙城址,以及和周公庙同类的孔头沟、劝读等重要遗址,另一个课题——先周至西周时期王畿的空间形态——也就提上了议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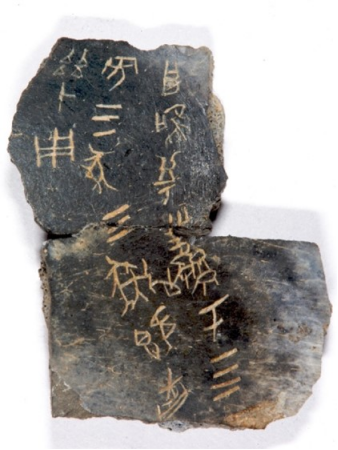
▴
2003年周公庙调查
这一阶段还发展了聚落结构研究的田野方法,简单说就是通过详细调查、广泛钻探、重点发掘来了解一个聚落的结构。关中地区的地形,由于农田整治形成大量断坎,详细的调查可以获取很多有质量的信息(比如夯土遗迹、手工业遗迹、特殊遗物)。2013年,雷兴山、种建荣老师主持进行了周原的聚落结构调查,掌握了周原大量遗存的时空分布规律,解决了遗址规模、演变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囊括以往发掘、偶然发现、调查、钻探几类资料的地理信息系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4年,为确定先周国家的中心,周原考古队发掘了凤雏三号建筑遗址。当时地表调查有先周陶片,因此考古队期待这是一处先周时期的大型建筑,但发掘证明建筑始建于西周早期,是已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庭院里还发现了特殊的立石、铺石遗迹。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次发掘大大增加了对凤雏区域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过去发掘的位于三号建筑北面的凤雏甲组建筑的年代和性质。

▴
凤雏三号基址发掘航拍图
2011-2012年,周原博物馆发掘了云塘水池。经2013-2016年的工作,发现周原遗址存在多条纵横交错的沟渠。这些水渠是框架性遗迹,对搞清遗址的布局非常重要。分布规律的沟渠,说明周原并非自然散居的聚落,而是有人为规划的人口众多的城市。工作中再次确认了凤雏南的一条夯土遗迹。这条夯土最早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未能围合。
周原遗址历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有两大问题有待解决:确定先周的中心;探明西周大遗址的布局结构。2020年之后的考古工作即以此为重点展开。
二、考古新发现
1.王家嘴一号建筑
王家嘴一带是周原遗址先周遗存最丰富的地方,以往也多次出土商时期的铜器,铜器墓是明确的贵族人物的指示。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确定先周的中心,周原考古队在王家嘴一带进行了调查、钻探,并于2020-2023年完整发掘了王家嘴一号建筑。

▴
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发掘航拍图
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位于王家嘴中北部。东西宽37米,南北长约68米,总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是已知先周时期最大的建筑。建筑由门塾、前堂、后室、东西厢房、前后庭院组成。前堂宽19米、进深12.5米,是一座面阔6间、进深3间的房屋。建筑的整体结构类似凤雏甲组建筑,柱网结构基本完整。建筑下叠压着商时期、龙山、仰韶时代丰富的堆积,夯土土质很不纯净。地基使用商周时期常见的分块夯打方法,然后开挖础坑、夯打坚实形成磉墩,部分础坑内夯打了大量红烧土块和碎陶片。基址被先周晚期单位打破,建筑前后庭院里发现七座年代明确的先周晚期小墓。打破基址的瓮棺W41碳14测年校正后是公元前1108-1010(68.3%)。基址下叠压京当型商文化晚期灰坑(H575),碳14测年校正后为公元前1201-1008年(95.4%)。这些证据都证明王家嘴一号建筑的年代为先周时期。
2. 周原城址
第二个问题——西周遗址的布局结构,需要从框架性遗迹入手。如果找到了道路、水网、城墙等遗迹,就可以较快地对遗址有一个大略认识。
2019年,曹老师观察到南北向的王家沟有东西向的方折转角,东西可以与西周沟渠相连。几处转角和西周沟渠围合成长方形,北面沟渠的内侧就是凤雏南的条状夯土遗迹,凤雏建筑群正好在这个范围的北部正中,方向北偏西10°左右,和长方形的方向完全一致,因此推测这个范围可能存在城址。
2020-2021年开展验证工作,确认了周原小城。小城东西长1480米,南北宽约1065米,整体呈规整的长方形,方向352°,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含城壕约190万平米),在同时期城址中规模最大(称之为“小城”是相对于后来发现的周原大城而言)。东城墙基槽宽约8米,夯土残深0.8米。夯土被西周中期的灰坑打破,说明年代早于西周中期。东墙以东约15米为城壕,口宽21.2米、底宽7.2米、最深3.75米,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南城墙基槽宽达25米,从揭露的平面和旁边断坎观察到的剖面来看,基槽由6块平行的夯土组成,每块宽4.2–5.7米,厚0.6-0.8米。夯土下叠压着商末周初的灰坑,又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西城墙墙基宽约13米,由三块平行的夯土组成。在其中一条解剖沟中发现城墙奠基墓葬,碳14测年属于商末周初。西墙发现多座西周末年灰坑打破夯土的现象,估计城址废弃的年代是西周末年。
在小城验证工作开展的同时,由于周原遗址的大量遗存分布在小城以东,考古队开始考虑城外东、东南是否还有郭城。根据以往记录的部分夯土地点呈直线分布,调查发现了大城南墙和东墙,通过钻探找到了大城北墙。大城位于小城东南,东西约2700米,南北约1800米,形状规整,面积520万平方米,是已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东墙长1770米,宽5米。在召陈建筑基址的东北发现一座城门。城门有南北两条门道,北门道保存较好,宽5.3米,北侧有嵌入城墙的门塾。门道曾遭火焚,被倒塌的红烧土覆盖,地面上出土西周晚期的铜器腹部残片。门道南侧的城墙内外各发现马坑一座,可能是与城门有关的祭祀遗存。城门结构复杂,内外均有瓮城结构。城门内侧钻探到的道路宽三十多米。考古工作还揭露了大城的两个拐角。东南角平面可见纵横的夯土板块。南墙宽7.5米,东墙宽7.2米。解剖显示夯土厚0.65米,夯层清晰,下压西周晚期灰沟。夯土内也出土西周晚期陶鬲。可知墙基是西周晚期建造的。西南角南城墙墙基宽10.4米,西城墙墙基宽9.5米。拐角处的西墙外连接一座夯土角台,南北长46.8米、东西宽16.1米;北端发现一排4个圆形夯土磉墩。经过5个地点的发掘,可知大城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晚期。

▴
大城东城门发掘航拍图(上为东)
西周城址确认之后,宫殿区成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根据过去的线索,小城内有一道东西向壕沟将小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正中存在大面积夯土。2023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了宫城的南墙、西墙和东墙。宫城南墙保存较好,发掘了墙体、墙外道路、壕沟、沟槽等遗迹。现存墙体相对城外地面高2.9米,相对城内地面高0.65米,宫城墙基宽16.2米,墙顶宽10.6米,收分明显。墙外有与墙体平行的道路,其上发现车辙。道路之外是宽达21米、深约6米的壕沟。壕沟最上部的废弃堆积内包含大量西周晚期的陶器碎片、动物骨骼,还有十几个个体的散乱人骨。关于宫城南墙的年代,解剖发现墙体打破商周之际的灰坑,又被西周中期和晚期的墓葬、灰坑打破;一座小墓打破了墙体内侧边缘,人骨测年为距今2825±25年,校正后在公元前1050-910年 (95.4%)。宫城范围内的钻探发现夯土分布十分广泛,应该存在密集的宫室建筑。宫城规模广大,东西宽794米,南北长609米,面积50万平方米。根据现有信息,宫城的兴建不早于商周之际、不晚于西周中期。

▴
宫城南墙外立面和墙外道路

▴
周原城址平面图
三、 学术意义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曹大志老师总结了周原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首先是发现先周大型建筑的意义。王家嘴一号建筑是迄今所见年代明确的先周时期最大规模建筑,它和凤雏甲组建筑的结构相似,但规模更大。一号建筑北面目前正在发掘三号建筑,建筑带至少长150米,这为确证先周国家中心的位置提供了证据,为深入研究先周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其次,曹大志老师将西周城址的意义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加深了对周原的城市发展过程的理解。周原遗址先周时期的核心区在西南部的王家嘴、双庵一带,这里两面临水,是一个区域中心聚落的自然选择。先周晚期,聚落向东北扩展,贺家、礼村、董家一带出现先周晚期的遗存。商周之际,在宽广的原面上规划了方正的城市。然后城市继续向东、东南扩展,西周中晚期遗存主要在东、东南部,西周晚期扩建了大城城墙。
第二,使周原城市景观、布局更清晰。城址给以往所知遗迹提供了参照背景,向着廓清城市布局结构迈出了重要一步。小城北部应是宫殿区,凤雏建筑群坐落其中,周围存在的大面积夯土,西周金文中提到的很多宫室可能就在此地。召陈建筑位于东墙内侧,位置上和城门关系更密切,可能是城市功能建筑。各级贵族的青铜器窖藏绝大多数发现于小城之外,暗示西周晚期时小城相当于王城,小城以东、以南则是郭城。
第三,为我国的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以往研究城市发展史,大量的材料来自东周时期,二里岗时期有一些材料,而晚商、西周时期的城址材料很缺乏,这使我们较难认识这个时期的城市发展状况、城市规划思想、以及整体的发展线索。而周原城址规模巨大的城门、城墙拐角的角台、面南而居中的宫城,都展现出成熟的规划思想。
第四,促使重新思考西周的都城问题。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周原的实际情况与传统说法间显现出诸多不协调之处。曹老师详细陈述了对周原遗址的性质以及西周都城问题的看法——周原是文字材料中的周和宗周,是西周王朝的首都。
四、 交流环节
雷兴山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周原之于北大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北大人魂牵梦绕的神圣殿堂。它对于北大老师来说是讲台和试验场,对学生来说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周原以往调查发现了很多夯土地点,但是以前的工作没有将它们联系起来作为城墙考虑。周原的新发现是研究理念引领的结果,是大聚落框架遗迹与聚落考古的结合。雷老师最后总结道,我们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考古学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延长了历史的轴线,周原考古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
讲座现场
现场师生就西周时期周原和镐京的考古学面貌、周原城墙的使用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