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8日,文研论坛第194期“透过青年看东亚:历史与当代的视角”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论坛由韩国延世大学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白永瑞作引言,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铃木将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飞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周晓蕾、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梁苑茵与谈,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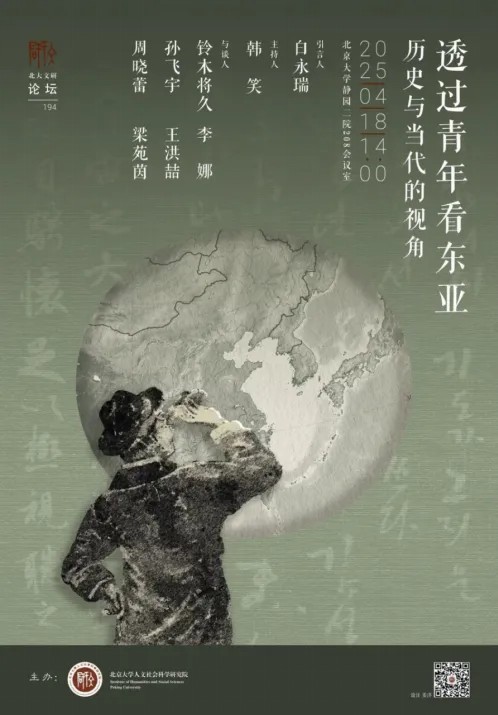
论坛伊始,白永瑞老师指出,青年问题的百年演变需要在东亚与全球联动的视角下进行审视。他特别强调,研究青年问题不仅要具备多层次视角,还应注重感受能力的培养。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作为跨国界的重要文化主体,其身份不断变迁,而本土—全球、区域—地方四个空间维度的互动,则构成了理解当代青年困境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框架。
近代初期,“青年”在东亚各个地区“诞生”,在20世纪初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青年是代表近代价值观的一代人。这个时代青年的社会形象是稳定的,他们是接受现有的价值观和理念,为成长为对未来有用的人做准备的一群人。但是,白老师指出,在传统时代的东亚文献中,“青年”(或少年)一词只是偶尔出现。积极地将“青年”评价为特定社会群体和引领国家发展的主体,是前所未有的近代现象。青年所对应的年龄群体过去肯定也存在,但没有相应概念,其独特价值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得到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支持。
在近代初期,随着东亚地区变革的需求日益加强,社会文化和国家层面需要借助“世代论”模式,有效挖掘出能够实践变革的新主体,“发现青年”的现象在东亚各地陆续出现。日本在明治20年代初期(即1880-1890年代),青年团体YMCA(基督教青年会)最早受到社会关注。中国和韩国青年受到关注的时间略晚于日本。白老师认为,青年话语出现的时间顺序和现代化进程有关,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导致其进入国民国家的路径不同,影响着青年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结合方式。比较分析青年作为主体,其形成过程有何不同,是重新解读东亚现代性的线索。

▴
白永瑞老师作引言
接着,白永瑞老师回顾了各国青年话语的内容和青年团体的出现。在日本,“青年”的发现是明治20年代初期特殊历史状况的产物。明治20年代是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开始确立的时期,从近代学校史的角度来说,因为教育带有国家主义性质,所以学生们的国粹主义倾向也比较强烈。这个时期的青年被认为是“吸收和体现欧式道德的人物”,是代表新日本的、西方的、建设性的,与东方的、破坏性的、旧日本的老人形成对比。
在中国的传统时代,青年不被承认为独立的社会群体。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少年”的概念,1910年代,在《新青年》发刊词中,陈独秀强调青年是社会的主要力量,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这一变化的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受挫后,知识阶层仿佛陷入黑暗的深渊,他们在新一代身上找到了微弱的希望,从而赞美青年,使青年话语得到扩散。对于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青年”来说,公共教育并未能提供克服疏离感的方法,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社会变革性自我开始扩散,青年们开始彼此分享经验,组建青年团体,创办各类媒体,形成独立的文化。这些青年团体的活动和青年话语在1923年前后分化为“渐进改革论”和“激进变革论”,后者中出现了职业革命家,献身于国民革命。
朝鲜的青年概念也是由日本传播而来。1905年后,随着爱国启蒙运动的开展,“青年”一词迅速扩散,青年被塑造为创造英雄的群体形象。1910年代,“青年”被重新定义为走向新世界、文明时,肩负竞争压力的进化论式主体。这一概念在1920年代初期的启蒙热潮中,成为象征新时代的关键词。这个时期青年话语的流行是“三·一”运动(1919)后迸发的群众能量转换为现实力量的需要,青年以近代化、文明化作为进步的目标,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三·一运动”后,大众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青年热情也退潮。19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加重,青年之间的差异和裂缝越来越大。综合来看,白老师认为,革命和国家建设时期,三国青年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是因为三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地位不同,由此导致三国进入国民国家的路径也不同。

▴
朝鲜三一运动
将目光转回当下,白永瑞老师将21世纪初的东亚青年文化比作“万花筒”。与20世纪革命与建设的时代相比,对于青年来说,21世纪也许是绝望和颓废的时代:青年摆脱家庭、社会、国家之间顽强的纽带和义务,工作和生活的不平衡和不确定性加深。这种全球性潮流在阶级、性别、民族、地域等多个层面上相互纠缠,青年的生活全景就体现在这种万花筒之中。当代青年作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青年个人生涯规划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联系时断时续,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青年认为明天不可能比今天好,对社会结构产生不满。
“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是青年的代表性意象之一。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一代,从小熟悉数字技术,重视自我满足和价值观,所以尊重个体的差异和喜好;会根据情况灵活地聚集在一起,然后再散开,不会形成紧密的联系,重视眼前的幸福。韩国“88万韩币”世代,Yolo世代,日本的“悟”(satori,达观)世代,中国的“躺平”“牛马”等流行语都反映了在东亚青年当中蔓延的废柴(loser)文化和“小确幸”风潮,青年一代不追求多么成功,但求生活舒适、心情平静。在对于“我的位置/角色”的探寻上,青年没有了变革志向,只有“小确幸”。
白老师指出,这是一个全球本土性(glocal)现象。很多国家青年都有对网络上的虚拟世界抱有乌托邦式期待的现象,但韩国有其特殊性。当下的韩国青年生长在自由主义普及期,没有扩大政治想象力的机会。再加上北韩问题和赤色情结(red complex),只要在自由主义中稍微偏左一点,就会被当成极端危险(亲共)的想法。韩国青年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经济稳定”和“+α”需求。“+α”需求的差异,除了后物质主义的MZ世代(韩国社会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统称,前者指1980年代初至1995年出生的一代,后者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的生活方式创新外,还有在韩国政治环境中形成的以青年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主义、以青年男性为中心的反女性主义、分配的平等主义、学历等级主义的价值差异。白老师认为,以上四种情况中,哪种价值会成为MZ世代的中心价值,将决定韩国的未来。
接着,白老师指出,东亚青年并不是单一的群体,会根据阶级、阶层、性别、地域等因素的交叉,产生差异。虽然当代青年看起来“自顾不暇”,对政治不关心,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不关心”,青年以讽刺等方式嘲讽既得利益者,拒绝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与近代青年不同,当代青年并没有选择走向政治主体化的道路,其所选择的文化实践方式是,用消极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许可以称之为“去政治的政治”。

▴
韩国青年参加反对总统尹锡悦的抗议活动
回顾20世纪和21世纪的东亚青年文化,白永瑞老师总结道,20-21世纪东亚各地的青年文化的共同点是变动时期的自我实现:同时实践适应现代和克服现代的双重课题。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影响造成的。不同点则来自于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因此需要强调“全球本土”视角。
最后,白老师强调,相比各国青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关注青年感受到的绝望和颓丧、不满和愤怒,接受青年用新的方式实现自我,并为其找到出口。这不仅是回应现实的策略,更是衡量未来社会想象的“未来史”指标。他指出,实现想象中的未来,需先接受“已经来到的未来”,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在此过程中,小规模自发组织与以情感和趣缘维系的小共同体至关重要,能为青年提供持续行动的支撑。他引用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中的观点,强调将个人经验问题化、回到实践、建立共同体的重要性,并提出,个人修养与社会变革同步并进,融合个人觉醒以创造新社会的理念与实践。
评议环节
与谈环节,铃木将久老师重点回顾了白老师讲座的两个部分:历史视角和当下青年问题。他指出,白老师以20世纪初期日本、韩国和中国青年的社会运动为切入点,特别分析了日本明治2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铃木老师强调,这一运动虽然规模小,但通过地方社会的连接形成了一定的力量,推动了日本宪法的制定,虽未达成运动目标,却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谈到当下时,铃木老师结合当前日本社会的稳定与停滞,指出日本青年普遍缺乏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接着,铃木老师介绍了东京大学王钦的《“零度”日本》一书,书中讨论了亚文化与青年困境,批评上一代人从保护视角来解读年轻人文化,缺乏对当代青年精神状态的深入理解。铃木老师认为,这种批判性思维与白老师对日本青年社会变革的反思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后,铃木老师总结,白老师的报告从历史中的社会变革中提炼出对于当代青年的现实思考,这种反思带有强烈的危机感,同时又对未来抱有希望。

▴
王钦《“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王洪喆老师围绕当代青年民族主义的演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通过分析1999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青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指出这一现象呈现出三次代际变迁:首先是1999年至2003年,以“强国论坛”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爱国者,表现出既爱国又批判社会现实的复杂心态;其次是2003年至2008年,以80后网络亚文化为特征,形成了工业党、自由派和左翼激进青年三大阵营,这一代青年通过互联网自我教育,形成“知情民族主义(Informed Nationalism)”,表现出了解外部世界越多,民族情绪反而越强的特点;第三阶段是2015年之后,民族主义在粉丝文化中扩展,粉丝文化介入爱国主义表达,更注重个体情感认同,如周子瑜事件引发的粉丝抗议,显示出以K-POP粉丝为代表,带有浓烈的情感化的民族主义。王老师指出,90后和00后青年在网络和留学经历中逐渐形成“在外越多、民族情感越强”的反向认同机制。他进一步对比中日韩青年的民族情感,提出东亚各国青年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中展现出复杂且矛盾的爱国主义形态,呼吁在未来研究中关注青年认同与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
周晓蕾老师的发言聚焦于韩国青年主体性的变化。她分析了韩国青年从20世纪初期引领现代化的主体,到90年代后逐渐丧失社会变革性的过程。周老师指出,冷战结束及民主化、市场经济转型和教育大众化使青年由革命先锋转为市场竞争主体,缺乏对社会变革的主动性。针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境,左派政治势力希望青年延续反抗性,批判其丧失变革主体性,而右派要求青年积极融入市场,指责其缺乏奋斗精神。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固守传统青年主体性观念,未能理解当代青年的身份困境。周老师指出,当代韩国青年自嘲自己生活在“地狱朝鲜”,是在表达对社会竞争压迫的不满,类似的,中国青年中也出现了“东亚小孩”的认同。这是由于压缩性现代化使得韩国和中国短期内完成现代化转型,导致传统与现代性元素混杂,青年主体性难以稳固。此外,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下,资本积累超过劳动收益,加剧青年成为市场牺牲品和消费品的困境。周老师提出进一步思考:为何东亚青年在全球资本主义冲击下,表现出回归前现代的特质?她指出,这可能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即传统价值调动和现实困境叠加所致。她呼吁进一步研究东亚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断裂,探索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互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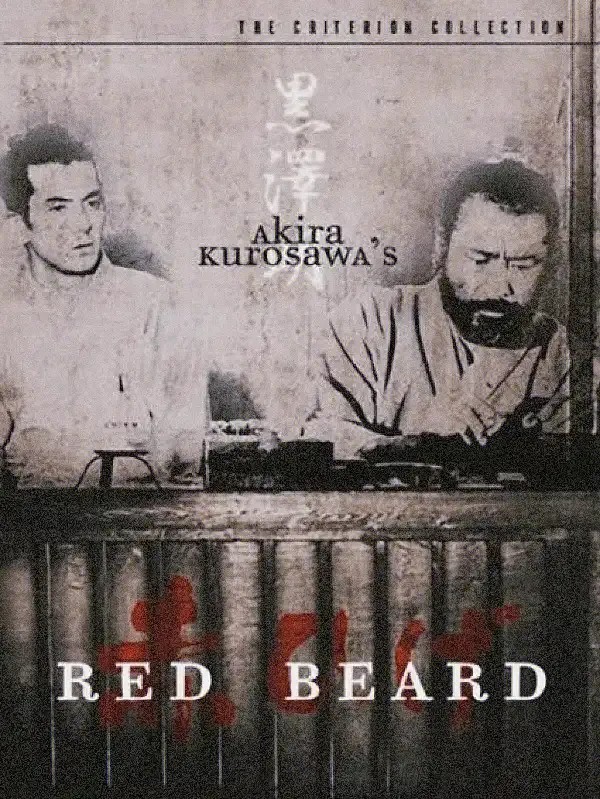
▴
电影《红胡子》海报
李娜老师在发言中围绕东亚青年问题展开讨论,重点探讨了青年作为社会变革性自我的历史与现实关联。她首先回顾了东亚思想连带工作,强调其在思想交流和历史反思中的重要性,认为这不仅促进了对东亚各国历史与民众生活的理解,也推动青年深入他者经验、反思自身处境。接着,李娜老师以豆瓣影评为例,讨论了当代青年在观看黑泽明电影《红胡子》后,对奉献和社会责任的反思。她指出,现代青年往往在现实压抑与精神困顿中,通过历史人物或经典叙事寻找精神支撑,但这种探索常流于情感化和孤立化,缺乏实践性。她认为,当代青年对东亚性的认同,往往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未能通过实践行动真正转化为社会变革力量。为打破这种困境,李娜老师提出应借鉴台湾《人间》杂志的经验,其以“人间爱”为宗旨,培养青年同理心,通过田野调查和真实故事,将社会问题转化为青年行动力,让青年在实践中形成历史认知和社会责任感。李娜老师最后总结道,青年价值的激发,不仅需要理论引导,更需要通过社会过程进行历史性的实践。
孙飞宇老师在发言中探讨了当代青年心理困境及其社会根源。近年来,孙老师通过访谈30多名抑郁症学生及精神科医生,试图理解青年抑郁的社会根源。在研究中,孙老师受到社会学者林耀华《金翼》一书的启发。他指出,以《金翼》中父亲角色为代表的闽南青年,有稳定的家庭责任感和明确的人生目标,几乎没有青年焦虑。而以费孝通的《茧》中工厂女工为代表的北京青年则因现代化冲击和社会转型产生自我认同困境。他指出,地方社会结构和家庭观念,在应对现代化冲击时,能否提供心理稳定机制,是青年心理状态迥异的重要原因。孙老师指出,抑郁症并非个体病症,而是社会问题在心理层面的集中体现,他反对将青年心理问题简单化为“空心病”或“抗压能力不足”,认为这实质上是社会问题的身体化呈现。孙老师进一步提出,青年主体性在现代性转型中,往往面临革命-守成的矛盾,但儒家文化缺乏卡里斯马精神,呈现为老年式、权威式的文化体系,缺少突破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青年无法找到社会变革的合理定位,只能在个人焦虑中徘徊。最后,孙老师总结道,青年心理困境并非单一的心理疾病,而是社会变迁与文化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主张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研究青年精神危机,还要探索新的文化和社会支持机制,以增强青年的心理韧性和社会角色认同。

▴
中国首部全方位抑郁解读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梁苑茵同学在发言中围绕青年作为社会变革性自我展开讨论,重点分析了近代青年与当代青年价值观之间的联系与断裂。她认为,虽然当代青年在网络上呈现出消极、颓丧、自嘲的状态,但实际上,这些情绪中也蕴含着变革自我和重塑主体性的潜在诉求。梁苑茵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指出当代青年在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上存在循环论证的陷阱:认为“现实如此,所以我如此”,进而固化自我认知,缺乏变革动力。当代青年在面对人际疏离、集体淡漠和自我迷茫时,往往通过网络话语和文化认同来缓解困惑,如认同“东亚小孩”这一标签。她认为,这种自我叙述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青年表达情感和寻求认同,但也存在自我封闭和认知固化的问题。梁苑茵最后强调,不应将变革性自我视为固定范式,不应以所谓的正常的青年形象作为标准来要求现在的青年,因为这可能会造成新的暴力或者是压抑,或许可以从历史当中打开更丰富的认同空间、经验和认识资源。
论坛尾声,白老师在总结中强调,共情是贯穿当代青年价值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线索,即使21世纪青年的身份和处境已有巨大变化,共情仍是理解社会困境和推动变革的核心。他指出,社会变革的动力不仅来自个人素养的提升,更依赖于小共同体的培育,如社团和自治组织,通过共同兴趣凝聚共识,从而实现个体觉醒到社会改造的转化。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智能技术促进修己及人,也是当代青年面临的重要课题。白老师呼吁通过共同体建设连接个体与社会,探索青年在现代社会中的责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