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周颖研究员
邀访学者论坛
2018年11月14日,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研究员周颖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鸦片与19世纪英国文学”。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五期邀访学者郭永秉、贺照田、刘成国、刘静贞、鲁西奇、王炳华、邢义田、薛龙春、周颖、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参与讨论。
首先,周颖介绍了自己近两年关注的题目:鸦片与19世纪英国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鸦片是一个颇为常见的意象,服用鸦片的英国文人也不在少数。鉴于近年有研究聚焦浪漫派诗人和夏洛蒂·勃朗特,讨论这些经典作家与鸦片,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乃至鸦片战争的关系。周颖在阅读相关文本、传记与批评后,分析鸦片在19世纪英国引起的争议,进而提出如下问题:鸦片在19世纪的英国究竟是商品、药品还是毒品?假如鸦片经历了从商品、药品到毒品的转换,浪漫派诗人与夏洛蒂·勃朗特分别可能处于哪个节点?如何解释瘾君子柯尔律治、德·昆西同鸦片同帝国的关系?夏洛蒂对鸦片究竟持何种态度?周颖希望结合文学文本的细读与社会历史语境的研究,对如上问题给出另一副眼光的理解。
报告第一部分以“鸦片:从商品/药品到毒品”为题,就鸦片作为药品与疼痛管理的关系、鸦片如何从药品转变为毒品、转变意义何在、鸦片疗效在英国医学界曾经引发怎样的争论等问题展开讨论。周颖指出,在19世纪英国,鸦片曾经雄踞于百药之长的宝座。因为止疼效果奇好,大量使用于伤亡枕藉的战场。消费者不限于文人墨客、社会名流,普通老百姓在自我诊治中也经常使用。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医学界还将鸦片视为最有价值的药品之一。当然,鸦片因为有娱乐的功效,且容易上瘾,也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极乐体验需要付出极痛代价:为追求欣快体验而落得形容枯槁乃至命丧黄泉者不在少数。

19世纪,含有鸦片婴儿镇定剂广告
如此一来,鸦片从药品变为毒品。虽然宗教和社会的反对呼声不绝于耳,医学界对于鸦片的利弊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赞成将鸦片运用于医疗实践的声音仍然是主流。赞成者中亦有激烈争论,又形成两派意见:一方追随古希腊名医伽林的理论,宣扬鸦片的冷效应,即催眠与麻木神经的作用;另一方则以爱尔兰名医约翰·布朗为代表,看重鸦片的热效应,即刺激神经、使之兴奋的奇效。同柯尔律治和德·昆西最相关的,正是后面这个布朗体系,也就是热效应派。两相较量之下,冷效应派逐渐占了上风。至19世纪末,正统医学界才将鸦片的兴奋与刺激作用完全排除在医学用途之外,不予考虑,只关注镇定与镇痛的疗效。限鸦片效用于镇定和麻痹,这是去魅的理性主张,使鸦片从无所不能的魔药、万灵药转变为在医生或药剂师指导下有节制、有限度使用的药品。1868年,英国议会通过《药房法案》,明文限制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规定只有注册药剂师或注册医药师才能出售鸦片。鸦片引发的问题虽未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通过政府与医药专业人士的合作,英国人成功地区分开了鸦片的合法医疗运用与危害健康的非医疗运用。
接下来,周颖分析两位瘾君子柯尔律治与德·昆西,讨论他们同鸦片同帝国的关系。两人皆因病痛始尝鸦片,屡试戒毒却至死未能戒除,又皆在鸦片的刺激下进入或瑰丽壮美或凶险可怕的想象世界,写下火候纯熟的传世名篇(《忽必烈汗》《古舟子咏》《鸦片客自白》)。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两人对于鸦片的态度,其实大有分别,不宜等而观之。柯尔律治一生与鸦片艰难搏斗,这过程其实是一个悲剧。他深陷泥潭,无法自拔,意志力彻底瘫痪,有时甚至还陷入疯狂。其间的痛苦与折磨,恐怕也只有诗人自知,里边是没有半点浪漫可言。他对鸦片的嫌恶与憎恨屡屡溢于言表,并断定德·昆西的《自白》将会“诱导人放浪形骸,沾染这让人日渐枯槁的恶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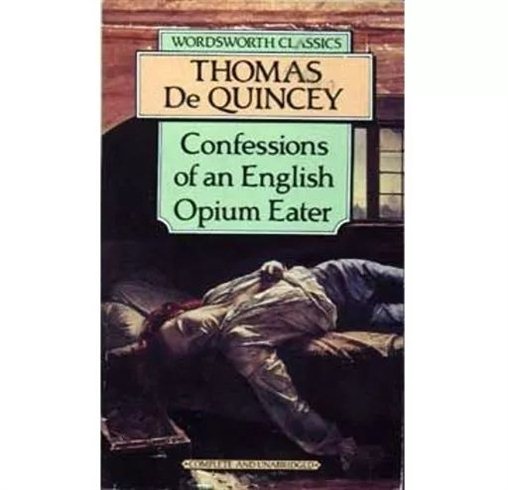
德·昆西《鸦片客自白》
相比之下,德昆西称颂鸦片的神奇与欢愉,不仅站在反医学的立场,且频繁使用富于宗教色彩的语言,将鸦片从私人癖好提升到被敬拜的神物。德·昆西将社会公认为害人不浅的毒品拔高到信仰和宗教的高度,这是他文辞富有魅力的秘密,却也是他普种苦果孽缘的根源。服食鸦片毕竟是有痛苦的,《自白》也触及这一面。但德·昆西的焦虑、忧郁、痛苦每每和各种不祥、危险、恐怖的东方意象牵扯在一起,仿佛给他负面情绪的不是鸦片,而是马来人、中国和埃及。1857年,德·昆西为詹姆斯·霍格的《泰坦》杂志撰写两篇论中国的文章,帝国心态在其中暴露无遗。不过,并非浪漫派诗人都像德·昆西那样认同政府的侵略立场。譬如在柯尔律治笔下,东方就呈现为一个绚丽、神秘、奇幻的世界。周颖认为,东方的妖魔化其实有一个过程,如果捋出一条线索来,那么柯尔律治处于这条线的开端,甚至是之前。中国在英国的形象,从18世纪的启蒙时期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好奇、钦慕、肯定到轻视、贬低、否定的变化。柯尔律治是在18世纪成长和接受教育,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于18世纪而非19世纪。这种变迁,既反映出英帝国为开疆拓宇、攫取商业利益而粉饰自我、贬低他者的动机,也对应于英国在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国力上升、野心勃勃,以及中国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日渐僵化停滞、丧失对手尊敬的客观事实。
最后,报告聚焦于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周颖从外部环境、家庭疾病、文本证据入手,层层解析夏洛蒂与鸦片的关系。细查夏洛蒂的所有小说,明确提到鸦片的地方,仅《维莱特》有一处。夏洛蒂无疑熟悉德·昆西的作品,可是,这个鸦片意象仍然不宜放大。鸦片在《维莱特》中既不是重点,也不是寓意深远的意象,只是客观地借用鸦片药效来推进剧情。夏洛蒂与浪漫派诗人的连接点,不在鸦片,而在敏感心灵、汹涌激情和神化的想象力。她对于小说的贡献,正是将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与自我引入了叙事文体。如果说鸦片是柯尔律治一度依赖的灵感源泉,是终生激发德·昆西想象的催化剂,那么对于夏洛蒂来说则只是一个戏剧化手段,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而且是她有意模糊、淡化的道具。她没有将鸦片刻意浪漫化,也没有凸显它的作用。
鸦片之于中国人,是一个牵扯了太多家仇国恨的意象,对它的仇恨可能诱使我们在解读英国文学作品时,将一个上下文情境中含义中性的药品赋予过多的道德、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内涵。柯尔律治、德·昆西、夏洛蒂·勃朗特都是19世纪的英国文人,他们对于鸦片的态度,因个人际遇和历史境遇的不同也各有分别,我们需要小心辨析,仔细分析,寻求中肯、理性的认识。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涉及文学经典的解读、鸦片意象与近代中国、鸦片文化与非理性主义的关系、如何吸收与批判地运用西学资源等话题。渠敬东教授指出,德·昆西的鸦片和东方意象究竟怎样交缠,可以有更清楚的表述;鸦片和整个19世纪西方文学之间的关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刘静贞教授和伊莎贝老师也建议周颖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研究鸦片与英国文学的关系。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为周颖研究员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