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研讲座142 2019年10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主持。
王汎森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希望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体悟,在退休前完成一本通俗小书,和大家讨论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性格与历史”将成为其中一章。因此,王汎森研究员再三声明,本次讲座不是学术探讨,而是通俗演讲,期盼能号召现代人多读历史,明白历史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不同文明历史书写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历史性的理解,即对“过去-现在-未来”关系的理解各有差异。毛利人认为,未来的基础是过去,未来是不断重复过去;埃及人在出生时就开始规划建设自己的宫殿,先假设将来如何回忆自己,再从现在开始修建宫殿——对他们而言“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对阿基里斯而言,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任何区别,过去没有意义,未来不值得想象,专注现在是最重要的。
关于传统读史的目的,王汎森研究员认为,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功利史学和进步史观较为兴盛,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19世纪后期中国流行的史书,大多以发现一种规律或一种原则为标准。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许多历史学家都遵循此标准。但是近年来,这种想法逐渐没落,大家开始怀疑是否有规律的存在。如傅斯年认为,“历史事件可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人物只能一个个地叙说,行动只能一件件地叙说,因果是谈不定的”。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历史是重演的。如学者陈登原在《历史的重演》一书中,用各种办法试图证明古往今来的各种历史事件都是重演的。德国观念史家柯塞勒克(Koselleck)认为,历史的有一半都是重复的,有着内在的结构(structure)。确实,历史有很多长时段的结构,其实是可以预测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可以把握的。但现代人重读历史时却发现,大部分故事不会重演,于是,“历史是重演”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第三,读史可以明晰历史情境的仿佛性。历史提供一些相仿的模式,使后人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可以进行参考。政治人物经常会将自己与前人相比,找到对应的模式(pattern)。美国总统华盛顿退位之后隐居庄园之举,仿效的是古罗马共和国时代君王的做法。第四,读史有助于把握未来。要注意的是,只是把握未来,而不是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功利史学、律则史学的目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用“封装(encapsulate)”一词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古代的知识被暂时地“封装”在历史之中,当遇到外界条件引导时便会涌现——文艺复兴的发生就遵循了此过程。
两个国家的外交史也是如此。当代很多外交官不能很好地处理两国关系,就是因为对历史“封装”的部分了解不够。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中,历史的训练能使我们快速认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并帮助我们准确定位。历史书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概然性,而非必然性。历史学家根据时间长短区分了三个概念,即“长时段”、“中时段”和“事件”。柯塞勒克(Koselleck)认为,长时段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把握的。
读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王汎森研究员以下棋为例开始讲起。通过熟读古人比赛时的棋谱,他顿悟到,或许可以借鉴古往今来的战局战术,帮助自己化解难题,因为高深的棋手总会用古今各种棋术来应对当时的情境。德川家康乃平庸之辈(他也有自知之明),但喜欢钻研史书,熟悉传统时代英雄们的作战策略,在对付丰臣秀吉时用的也都是这一套。
讲座最后,王汎森研究员总结道,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也增长见识之学。历史的实际功能非常强大,不在于指示具体事情,而是经由扩充历史认识,提升自我能力。朱熹认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读史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过程,不是“照着做”,而是“接着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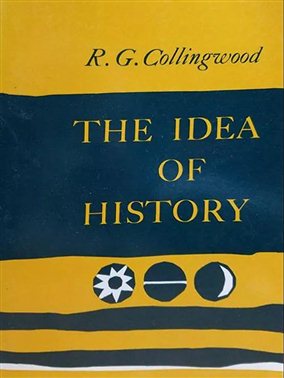
 熟读历史能够我们明白什么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关键时刻做的决定(哪怕是微小的)往往会对后世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例如,康有为
熟读历史能够我们明白什么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关键时刻做的决定(哪怕是微小的)往往会对后世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例如,康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