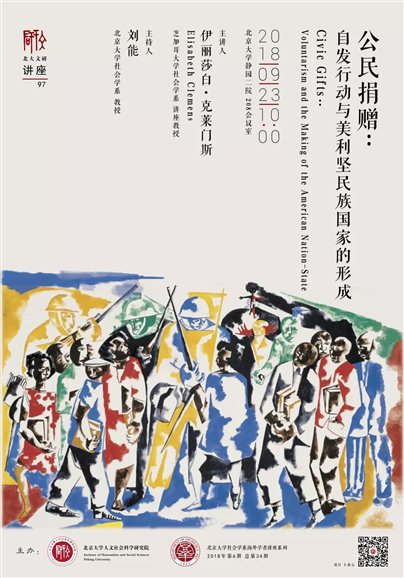
文研讲座97
2018年9月23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公民捐赠:自发行动与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形成”。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主持。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谢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助理教授田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张长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教授
首先,伊丽莎白·克莱门斯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研究背景和报告内容——同名课题的最新成果。克莱门斯教授表示,本研究始于她对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两个问题的思考:其一,反政府主义呼声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中是如何产生出全球霸权的?其二,公民的自发行动和慈善行为如何发展成为美国的政治动员和政治组织的重要形式?这两个问题,一个关涉自由公民身份,一个体现互助互惠原则,实则指向两种互不相容的行为逻辑。所谓自由公民身份,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而互惠原则意味着个体对他人的依赖性——它要求人们心存感激并给予回报。克莱门斯教授强调,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深刻的张力,美国政治文化中这两者的统一和共存格外引人深思。
讲座第一部分,克莱门斯教授介绍了本研究的理论关怀和分析框架。她表示,虽然本研究是基于史料爬梳、聚焦美国的个案研究,其后仍有深厚的理论关怀。其一,克莱门斯教授将本研究置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转型进程中。以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曾提出,历史研究应当将固化的关注点从国家权力结构转向政治秩序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和经济因素也不容忽视。其二,克莱门斯教授将经典人类学和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研究中。一方面,她强调社会关系网络背后的文化内涵。传统的研究往往忽视了社会关系其实是建立在迥异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因此未能捕捉到社会关系网络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变革的过程。另一方面,她强调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是相互建构的。传统研究将这二者割裂开来,仅强调前者有关资源分配制度和等级制度,而后者关涉人们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和团结互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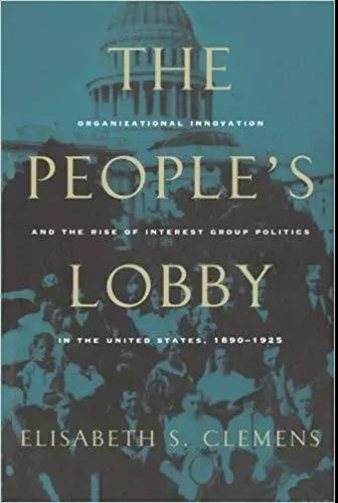
克莱门斯教授专著书影
紧接着,克莱门斯教授回顾了结社主义(associationalism)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境遇。克莱门斯教授指出,在十八世纪末期,隔洋相望的法国和美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挑战,即如何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实现平等的公民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和美国的经验有相互借鉴的意义。克莱门斯教授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俱乐部为例,讲述了社会团体在当时收到的社会评价——在革命中发挥重要影响,并在革命后成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并且压制个人自由。需要澄清的是,尽管托克维尔等重要思想家将社会团体描绘成反抗官僚政权和民主专制主义的堡垒。但这种观点并不是从建国之初就存在的。事实上,早期的评论家将社会团体视为混乱、阴谋和派系斗争的载体——威胁个人自由,提倡的善意和捐赠使公民产生依赖,并削弱他们自立自足的公民地位。
那么,作为不稳定因素的社会团体何以对美国国家建设和美国民族主义形成发挥关键作用?对此,克莱门斯教授强调,虽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但她采取的是文化和组织的分析视角。换句话说,她所关注的是强调个人自给自足的自由个人主义和强调互惠关系的结社主义这两种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模型是如何在一个治理体制中被结合起来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克莱门斯教授在她的研究中采取了以下几种分析策略:第一,证明这两种逻辑/模型/模板的独特性和不相容性;第二,寻找调和这两种模型之间的矛盾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片段;第三,总结历史遗产(也就是二者在话语层面的不相容性的体现及其变迁)以及缓解或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文化、法律和组织层面的创新策略。

讲座第二部分,克莱门斯教授选取了三个历史片段来展示上述分析策略。第一个片段发生在美国内战期间。在这一时期,公民捐赠被视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型策略。内战期间,美国面临众多挑战,如何坚守政治和道德原则便是其中十分棘手的一个。当时,人们认为参军会对公民的道德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同时,人们担心战争动员会过度加强国家能力,从而威胁公民的个人自由。对此,克莱门斯教授表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体和公民自发行为这个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当时,战备资金的筹集主要是由自发形成的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承担的。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惠关系——士兵为战争奉献自己的生命,同时依赖人民的供养;而人民将物资捐赠给军队,以表达他们对军队的感激和支持。这种普遍的互惠关系将冷冰冰的军事规训和有人情味儿的慈善捐赠结合起来,塑造了一种新型政治动员模式,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也完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内战之后,这种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仍留存在人们的文化记忆里,在城市改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个片段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自发性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群众捐助和志愿服务)逐渐成为战时资源筹集和建立民族凝聚力的关键因素。在一战后期,美国超过60%的战争资源来自民众的捐赠而非强制征税。此外,截止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的参会人数占国民人数的22%之多。这种爱国主义捐赠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它完成了战争物资的筹集工作;其二,它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内战之后,美国的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的关系仍处紧张状态。而公民捐赠为弥合这种张力提供了有效途径:边缘群体通过捐赠可以获得社会声誉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而捐赠的互惠性将原本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迥异的人有机地连接起来。

第三个片段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公民捐赠被广泛应用于1927年密西西比粮食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等全国范围的危机之中。然而,即使在胡佛总统的有力领导下,这种自发捐赠的模式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根源在于,人们认为依赖救助是对公民尊严的威胁。到了罗斯福政府时期,公民捐赠再次成为应对国内危机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更加积极地在话语层面构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互惠关系,从而减少领取救济的人们的社会污名。
讲座最后,克莱门斯教授总结了这种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留下的制度遗产的主要特点。其一,它将公民身份同捐赠紧密联系联系起来。其二,它是个控制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和混合性的制度领域。其三,组织和文化层面都具有复杂内涵的边界客体(boundary object)大量出现。其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是公共或者私人行动者,可以是营利或非营利的行动者。总的来说,从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公民捐赠模式融合了自发行为和民族团结,它为美国国家能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

提问环节,谢宇教授首先就美国在社会团体现象上的“例外性”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形成了大量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团体,他们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不屈服于教廷或世俗政权的权威。受文艺复兴传统影响,美国也存在大量类似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从这个层面上讲,美国的社会团体并未体现其例外性。克莱门斯教授回应道,欧洲和美国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在欧洲,社会团体需要有正式的章程才能得到认可,并且受到严格管制。而在美国,社会团体具有较大的政治自由,受到的司法和行政管制较少。这种自由使得社会团体得以在美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熊跃根教授注意到,主讲人使用了民众捐赠(civic giving)和爱国捐赠(patriotic giving)这两个术语来指称捐赠行为。他追问,这两种不同的捐赠行为对国家-社会关系有何不同的影响?克莱门斯教授回应道,在十九世纪,传统的捐赠行为和精英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提供大额捐赠是彰显和巩固精英政治地位的重要方式。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更加倾向于民众捐赠这一捐赠模式,根据自身能力自由选择捐赠的数量。虽然仍受精英政治的影响,民众捐赠表达的是一种更加包容和平等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