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6日晚,“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政作引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副教授王楠出席并参与讨论。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政
首先,渠敬东教授归纳了叶启政教授最近出版的《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本书反映了叶启政教授对于社会学及相近学科当今形态及未来发展的责任感。渠敬东教授提到,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着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的体制,且这一体制已经彻底进入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领域。这意味着,我们的思维、研究与方法同时代整体的体制密切相关,学术发展的完全技术化会对国家和文明自身的延续与未来产生重要的作用。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
渠敬东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者的话题可以从单纯的研究思维、方法与策略向着它形成和发育的历史回归,并由此关照整个世界的生产体系。在重新回到西方锻造现代世界图景的同时,探究当时对社会构成的理解及其内在思维和图景结构与今天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次论坛所探讨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议题,还包括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景及其与学者之间的知识的关系。
随后,叶启政教授分享了自己有关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观点。他强调量化的意义,并认为关键点在于“诠释”意义的方式。同时,叶启政教授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态度,而非衍生出来的一种特定的技术。假如我们接受“知识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前提,那么,既然是社会的产物,知识就都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特质,并享有社会连接起来的对世界或对人的一种感知的特殊模式。换言之,任何的知识(包含科学知识)背后都有一定的所谓哲学、人类学的预设,也都会有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这些东西不是不可批驳的。我们可以对知识建构背后的基本预设进行追问,若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反思的能力。
以《实证的迷思》一书为例,叶启政教授表示,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回头检验美国社会学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成为今天这般模样的。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之为定量的研究。当理性化逐渐压缩纤细型思维的空间,几何型思维成为唯一的教条。自然科学同数学结合,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典范,并将计量应用到了对人的研究当中。叶启政教授也在书中阐释了十九世纪以后的统计学发展、“均值人”(average man)出现的历史背景。
在介绍书中有关统计学发展历程的内容时,叶启政教授再次强调,统计学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以参数统计中平均值的使用为例,这一概念在各时期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每个测量的单位也在人类世界中各自表示着特殊的意义与性质。他援引统计学家的观点,表示“统计是处理误差的艺术”。在对智力等与人相关的因素进行测量时,重点不在于人种的优越与否,而在于概念与测量的比例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连接。研究者应当关注并思考基础测量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理解定量背后西方哲学人性与历史提供的预设。
叶启政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定量研究过程中的思考极为重要,也是构成所谓学术良知的最核心部分。人们应当理解其中的局限性,并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表达真理的唯一方法。学界应当警惕西方逻辑对现代知识的决定作用,在做学问时保持谦虚的态度,明确自己的极限,否则将产生“暴君型的作为”。而在定性研究的领域,理论的思考同样有其局限性。叶启政教授表示,世界是多元的,社会也存在不同角度的多种面向,没有一个侧面能代表“最后的真理”。他强调自己对定量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反对把特定的科学观当成准宗教的无上律令,替代上帝宣言真理。
接下来,周飞舟教授也从统计学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他引述了叶启政教授在书中表述的观点,认为统计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哲学,是在对人的假定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周飞舟教授以“法身”、“法相”举例,表示好的量化研究不是纯粹靠量化技术做出来的——量化研究不是一个自洽或自足的研究。如要很好地完成样本选取这一关键步骤,其先决条件就在于对样本总体有非常充分的了解。此外,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总体的方差也是决定抽样的关键因素,但做社会研究的主体还是人。好的量化研究首先需要作者洞察两个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再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证明,而非通过数据发现关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
周飞舟教授进一步解释了量化研究与田野的关联。他认为,应当把量化研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技术;另一部分虽未在文章中呈现,却是关键且无法为人工智能所代替的。量化研究无法自足的原因就在于洞察力无法通过统计技术得到——洞察主要依靠理论和田野。周飞舟教授表示,尽管统计和数据收集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学很多的洞察力还是来自田野,而离开田野则会“自己断了自己的路”。如叶启政教授所说,田野中面对的不是“一些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活生生具体的人”。数据或田野研究的目的都是增加自己对社会的洞察能力。社会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省的过程,一个反思的过程。
应星教授则从另一侧面回应了讨论的主旨。他首先分享了对《实证的迷思》一书的感受,归纳了叶启政教授所表述的关于知识社会学分析的观点。应星教授指出,现在的社会学教育缺少对理论训练与方法论的学习,对这些学术工具所具有的力量和局限性也缺乏充分的理解。叶启政教授的著作从技术视角追溯到哲学层面,讨论了统计学中的“偶然”放置在现代科学或现代社会位置中的方式问题。学者不应做西方的追随者,但也不能简单地抛开,而应更深地进入西方、挖掘其根本,才有能力回头面对本土文化与田野。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
侯旭东教授从历史学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理解。联系自身教学指导经历并与叶启政教授的著作对照之后,侯旭东教授表示,在历史中运用统计学的研究具有一定困难性,一些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把握。叶启政教授曾在书中对“均值人”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侯旭东教授认为,以统计学的方式研究并理解古今中国,需要思考“均值人”假设是否适用,且应思考不同时期、体制与位置上的“人”应被如何度量。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
李猛教授同样援引书中的论述,分析了不同倾向的统计方式背后的社会概念。他表示,叶启政教授二十多年前的授课改变了他对社会理论工作方式的理解。整个大数法则和常态分布曲线以及对均值和方差的理解,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大众社会的特点,而这样一个社会应该具有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部分人相当重视体现在离散度上的、个人偏离或者并不完全等同于常态的形式。这要求构成社会的基本不应是等级制,不应存在人和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与古代人伦社会的强烈差异性、偏私性,也不应被明确具体的社会集团所阻断。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
李猛教授指出,现代社会存在大量的新生特征,而非长期的稳定状态——这将给长期统计分析带来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叶启政教授的分析很好地揭示了由“均值人”个体构成的社会,具体内容包括怎样理解现代社会中建立的个人以及社会形态背后的政治构成过程,而这些正是社会在社会学形态上体现出来的面貌。李猛教授强调,叶启政教授不仅警示我们提防统计背后过于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的理解,更通过对统计进行反省,让我们认识到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何种样态。统计概念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理解的方式,统计学本身也是这个社会最应探究的真相。
刘云杉教授则从教育的角度进行探究。她认为,实证主义不仅是方法论,也是社会对知识范式的塑造和选择,同时对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均值人”、常态分布等要素既左右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又设计着我们的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在中国教育政策的情境中,除了培育功能,还有筛选功能。现代社会的教育已不再高居象牙塔,还担任着人才分类、教育筛选的作用,同时是欲望再生产的核心机制。刘云杉教授引用了一些学者的观点:二十世纪的社会驯服的是生产者,二十一世纪培养的是消费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
刘云杉教授对当代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她认为,“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而是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一方面追逐着稀缺昂贵的教育符号,另一方面又在舆论上排斥着教育。教育公平由此成为非常复杂的内涵的诉求:行政权力在回应复杂诉求的过程中,以减负回避筛选,又以均衡来延缓筛选。但她仍旧相信现代教育“师道传承”的因素,并表示人们依旧能在其中挖掘人性和理性的光芒。
接下来,王楠副教授围绕社会科学的传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美国社会科学呈现科学主义的趋势,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变化也和我们今天的处境有类似之处。社会学在美国社会科学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美国兴起时恰处在社会大规模扩张和动态变迁的过程之中。社会学家尝试着突破传统的宗教、政治以及经济学的框架,去寻找一个理解社会发展和再组织化的方式,以期对大规模社会的组织秩序、个人道德和自律意识的实现提供说明。王楠副教授表示,一个文明或社会急于走向世界、进行扩张的行为可能源于自我的迷失与遗忘。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
论坛最后,叶启政教授再次归纳了《实证的迷思》一书中的部分理论要点,阐述了统计学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中的定位,并重新审视“机遇能不能驯化”的统计学问题。叶启政教授认为,当代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应当承担起文明古国应有的使命与责任,在学术乃至文化领域面向世界,并对西方提出带有批判性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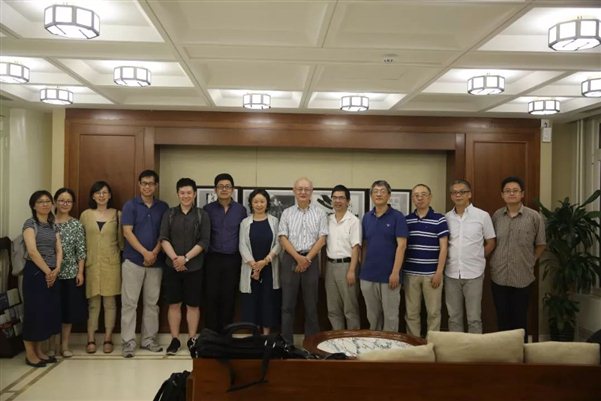
会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