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从社会史角度看陕甘宁边区的起源”,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讲座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杨奎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主任章百家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牛大勇、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黄道炫,及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出席并参与讨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也莅临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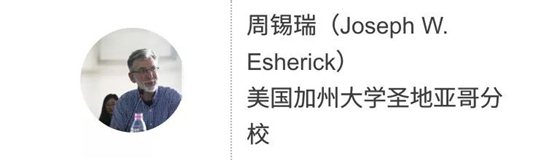
周锡瑞教授在引言中指出,他在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起源”时使用了研究义和团等问题时的方法,即把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口头历史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陕北地区进行了多方面考察。一直以来,中国总是从党史的角度去谈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但对于学界来说,社会史的视角是必需的。那么,党史和社会史研究有什么区别呢?党史研究有其特定的方法和目的,它关注历史人物的评价,关心领导人的岗位变迁和政策得失;相较之下,社会史研究则关注领导人的社会背景、教育经历以及在革命前后和周围人群的关系。他举了一个例子,党史资料提到陕北革命重要人物刘志丹时,只表明二十六军是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组建的,至于“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也只笼统谈到其与当地民团有一定的关系。显然,这样简单地分析阶级成分并不能展现历史的原貌。而在社会史的范畴,我们则需要探究刘志丹究竟是如何动员、拉拢民团的?这些被他动员起来的所谓“土匪”、“流氓”又在当地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社会史关心的问题。
接着,周锡瑞教授简单概括了他自己的课题。在探究陕甘宁边区起源的问题上,他把自己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共产党革命早期,第三阶段是“土匪与布尔什维克”,即刘志丹和陕西省委之间矛盾冲突的时期。本次报告中,周锡瑞教授着重谈第三阶段,即主要谈论1934和1935两年的历史,并探究陕甘宁地区是怎样在短短两年之间实现革命力量从无到有的过程的。周锡瑞教授谈到了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时代背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时的中共还没有把“抗日”当作自己的主要口号,而是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显然,这个口号并不能在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深入人心。1934年,中共的宣传重心始转移到“抗日”上。在“抗日义勇军”的旗帜下,很多百姓响应号召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
其次,地区气候也影响了革命局势。1926—1931年间,关中和陕北地区发生了大面积干旱,中共很难动员饥民发动革命。直到1934年大丰收,部队有了足够的粮食,征兵工作才得以较好地展开。另一方面,大丰收之后,地方政府增加农民的税收,许多不堪忍受沉重赋税的百姓选择参与革命。
此外,地理因素也构成了陕北革命的社会背景。刘志丹是陕甘地区的革命领导人,他的家乡是延安西边的保安县(现为志丹县)。保安县受“回乱”影响严重,人口稀少。之后,随外来人口迁入,土著和非土著之间产生矛盾,并在长时间的争斗中形成多方民团势力。刘志丹的父亲出身民团,刘志丹在发动革命时,便是通过此方面的关系动员民团加入到革命队伍中。而另一位,陕北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谢子长,则主要活动在榆林地区。这一地区相较陕甘地区耕地要多,文化水平要高。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两所学校也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很多农民学生后来成为了党组织在地方上的重要干部来源。陕甘和陕北两地不同的社会地理,造就了两个地方不同的革命发展路线。
在革命过程中,谢子长带领的陕北派和刘志丹带领的陕甘派虽然一直矛盾不断,但在战斗中则多有合作。可以说,整个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是在谢、刘二人“一文一武”的合作中完成的。谢子长有较为完备的党组织,刘志丹则带领着集结了各方力量的革命军。陕北革命中,刘志丹率领军队南下,与谢子长领导的党组织结合,通过学校的人际网将当地的乡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动员了起来。在两人的带领下,到1935年下半年时,延安周边已经有多个县革命成功并脱离国民党的管辖。
但是,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之前,陕北和陕甘两派正处于矛盾之中。陕北派为了压制陕甘派,通过“肃反”抓捕了二十多名陕甘派的干部,刘志丹也因此以“叛变革命”的罪名被捕。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纠正了“肃反”错误之后,刘志丹才获释回到军中。但在之后不到一年,刘志丹就在晋西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刘志丹究竟是如何牺牲的?是因为战争还是内斗的因素?周锡瑞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牵扯出另一段历史。对于革命史中的诸多细节,他能做到的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很多时候“石头还没有摸到”。

赵世瑜教授指出,周锡瑞教授在研究陕甘宁边区起源的问题上,采取了和研究义和团运动同样的方法,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和义和团确实有类似的地方。起初,它们都只是一个脱离了国家政权管辖的特殊行政区,只不过,陕北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共后来成为了合法的政权。所以,陕甘宁边区才有了和义和团截然不同的命运。若我们暂时抛开党史的视角,单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看革命地区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更多的矛盾和问题。试举一例,在“回乱”平息之后,清政府组织了大批移民,到十九世纪末期时,陕北地区就已经有了很多甘肃、宁夏迁移来的移民。此外,历史上,延安本身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性非常大的地方。它毗邻长城,常年有军队驻扎,连带着也有很多为军队服务的百姓在此定居。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人口构成复杂且流动性大的地方,却一直至明末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反而是到了后来,生活稳定,定居人口增加,大规模的内乱才逐步开始出现(比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现在讨论的陕北革命)。随着生活逐步安定,政府开始对这些一直以来自由散漫的偏远地区“编户齐民”。于是,赋税问题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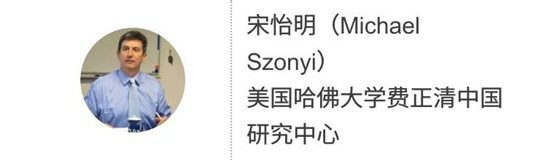
宋怡明教授谈到,早期美国在研究中国革命史时非常重视阶级,认为阶级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重要的历史分析工具。但现在大家则逐渐认识到,阶级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一种政治语言,因此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此外,“革命潜力”也是美国学界常常谈到的概念——或是从抗日史的角度谈革命潜力,或是从党史的角度谈革命潜力;而周锡瑞教授并没有受到这种研究传统的限制,他直接从物质条件和社会构成的角度去探究三十年代的中国,这是非常难得且可贵的。当然,这可能和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在某种程度,当前学界对待革命史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接近研究政治动乱或起义运动的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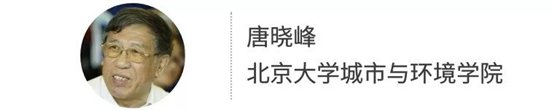
唐晓峰教授发言,他指出地理分析在周锡瑞教授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周锡瑞教授区分了陕北革命的两个不同地区:一是人口较少、矛盾冲突较多的陕甘地区;另一个是人口较多、较为安定且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的陕北地区。通过这种区分可以看出,共产党革命和其他“氓流起义”的不同点正在于革命者身份的不同——共产党的领导者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若非如此,陕甘宁边区和义和团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说,谢子长与刘志丹的合作正体现了共产党革命的典型特征。此外,唐晓峰教授也谈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革命潜力,即中国农村中的“造反机制”。当农村社会遭遇重大危机(例如灾荒)而官府又不出面解决时,矛头就会转向官府,就会有一批聪明的“捣蛋分子”开始出头,带领大家起来反抗。共产党在革命时也在农村中利用了这种造反机制,并做了进一步引导。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革命以中国广大的传统农村为基础,而非新兴的工商业和口岸经济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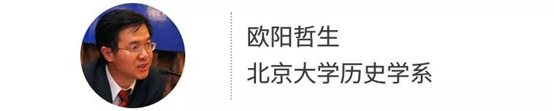
欧阳哲生教授对周锡瑞教授从社会史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表示赞赏。他指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相比,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确实在其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建立也主要归功于刘志丹和谢子长。这些领导者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构建带到了军队和农村中,使得共产党革命呈现出与义和团不一样的面貌。其次,无论是井冈山还是陕甘宁,领导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根据地的选址定在了十分偏僻的地方。在这种偏居一隅、没有革命倾向的地方,只有领导人积极动员,革命才有可能产生。因此,欧阳哲生教授向周锡瑞教授建议,在采用研究农民起义的方法考察陕北革命的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和传统农民起义不同的地方,而这些不同的地方恰恰是这场革命成功的关键。

作为一名榆林人,高波老师谈到了陕北特别是榆林地区在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保守。但是,保守的陕北为什么能够诞生出如此巨大的革命力量?对此,高波老师指出,陕西人在提到陕西时一般是从南北纵向来谈的(如“陕北”、“渭南”)。而周锡瑞教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东西跨向的视野:陕西的西边山地多、人口少、“土匪”多,而东边相对来说耕地多、人口多、文化程度高。那么不妨推测,对于内陆的革命来说,外部因素的介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陕西是一个地处西部的内陆省份,在这里“建国”的汉、唐其实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外来政治精英集团革命的成果,而非陕西人自己的功劳。因此,似乎必须要有一个或多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外因介入,内陆的革命才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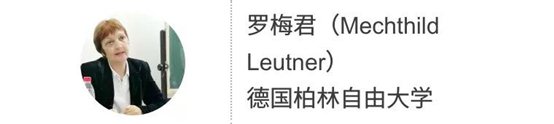
罗梅君教授也十分赞赏周锡瑞教授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她指出,在社会史中我们会考虑到不同阶层、不同种类的人群甚至是不同性别之间的问题,只有把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阶级问题考虑在内,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革命,因此当下在研究革命史时我们应当把党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此外,作为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罗梅君教授也提到了马克思一些基本原则对她的影响,比如在对待历史原因的分析上,她会更加看重经济因素和社会分层(social division),并且,罗梅君教授认为,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共产党才能在历史中取得诸多成功,比如本次论坛谈及的陕北革命,农民们更多地支持共产党而不是支持国民党,正是因为共产党了解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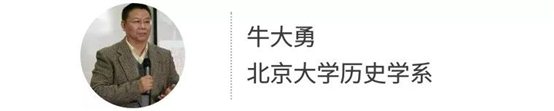
牛大勇教授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陕甘地区的党组织虽比陕北弱一些,但还是一直存在的;第二,陕北地区虽然人口较少,地理相对封闭,但在村社内部仍然有着严密的宗族组织,这些宗族组织有时会同游离在宗族之外的流民发生矛盾,而这些小的矛盾在遇到外部力量冲击时(比如土地改革)就有可能转化为革命;第三,黄土高原的独特地形为革命军采取游击战术提供了条件,也让国民党后来的“围剿”变得较为困难;第四,如果有人通过宗教或党派把饥民组织起来,饥民就有可能造反;第五,作为一个曾经被判“反革命”的人,刘志丹很可能希望通过战死沙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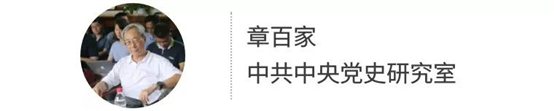
章百家教授也对周锡瑞教授的研究表示赞赏。他提到,国内的党史研究一般呈现为两种倾向:“八股式”研究与“八卦式”研究。而周锡瑞教授的研究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社会史的视角,而这个视角对于党史研究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章百家教授也提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传统的农民革命往往是农民起义成功后,知识分子再被招揽加入;而中共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由新式知识分子发起的。作为社会精英,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又学到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人际关系网,而最初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只是在这样一个精英的小圈子中诞生。此外,章百家教授也强调,革命和造反是两个概念,革命是要“改朝换代”,虽然国国民党也讲革命,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真正扭转乾坤的社会革命——这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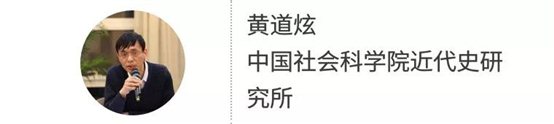
黄道炫教授表示,我们在讨论历史原因时,总不免会陷入一些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只是一个伪议题的原因之中。所以,议题本身首先就要切中要害,只有这样,我们在探讨原因时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目前,国内的革命史研究也逐渐开始强调社会史的角度,这种新视角的引入确实大大丰富了革命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素材。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共革命具有连续性和独特性,我们在谈论它时必须将政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若完全抛开政治因素,单纯考察社会关系、地理结构等次要条件,很多问题就会难以说明。虽说共产党的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但它将政治因素注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用政治的手段改变、控制社会。因此,政治因素在革命史中永远占有一个实质性的地位,这是我们无论从事革命史哪方面的研究都要保有的清醒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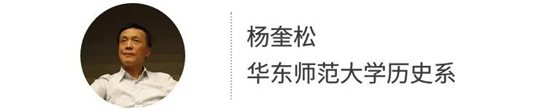
杨奎松教授压轴发言,他指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起源,就必须要谈到宁夏和回民的问题。作为一个行政区划,“陕甘宁边区”其实和地理、经济,甚至同红军长征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至于哪些县属于边区,而哪些县不属于,这一划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共两党持续斗争的结果。共产党实际控制的“边区”范围一直在变动,从最初的15个增长到18个,1942年时又增长到23个。在这期间,若中共很好地控制了宁夏的两个县,那么中共后来的干部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从宁夏回族中培养出来的,但事实并未如此。因此,杨奎松教授也希望周锡瑞教授可进行一些跨省研究,更多地探讨陕甘宁三个地区共性的问题。此外,杨奎松教授也谈到了陕北的党员成分。自苏维埃革命后直到中央红军到来前,陕甘宁地区的富农和富裕中农一直都是党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人正是前面几位老师谈到的新兴知识分子,他们作为革命的领导集团带动了当地其他农民参与革命。
最后,周锡瑞教授就与谈嘉宾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建议做了回应,并与莅场同学进行热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