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方法的文献学”
2021年5月21日下午,“文研论坛”第14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作引言,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程芸,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龙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系“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第六场,由北大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平台共同主办。
 论坛伊始,潘建国老师首先抛出两个问题:为何要提出所谓的俗文学文献学?如何来构建俗文学文献学?并以此引入本次论坛的主题。在他看来,传统古典文献学建立在印本书籍与经史著作两大学术基础之上,因而以一个初始定本的存在与流播过程中文本的基本稳定为默认的学术前提。这就造成它在处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周秦汉唐时期的写本、抄本等一些不稳定或具有一定流动性的文本时,会出现一些学术上的不适应。随着近一二十年来各学科文献学研究的推进,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写本的文献学或抄本的文献学。潘建国老师指出,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用意大抵与之类似,俗文学的社会地位与自身的体制决定其文本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但其特别之处在于,俗文学基本发生于印本时代,故而这种流动性整体上是属于印本时代的流动性。以小说为例,北师大郭英德老师曾提出小说领域存在“一书各本”的现象,如《水浒传》就既有容与堂本为代表的“文繁事简本”,又有插增水浒本为代表的“文简事繁本”,还有明代袁无涯刊本为代表的“文繁事繁本”、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本等等。面对同一小说而各本之间情节、文字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传统古典文献学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论坛伊始,潘建国老师首先抛出两个问题:为何要提出所谓的俗文学文献学?如何来构建俗文学文献学?并以此引入本次论坛的主题。在他看来,传统古典文献学建立在印本书籍与经史著作两大学术基础之上,因而以一个初始定本的存在与流播过程中文本的基本稳定为默认的学术前提。这就造成它在处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周秦汉唐时期的写本、抄本等一些不稳定或具有一定流动性的文本时,会出现一些学术上的不适应。随着近一二十年来各学科文献学研究的推进,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写本的文献学或抄本的文献学。潘建国老师指出,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用意大抵与之类似,俗文学的社会地位与自身的体制决定其文本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但其特别之处在于,俗文学基本发生于印本时代,故而这种流动性整体上是属于印本时代的流动性。以小说为例,北师大郭英德老师曾提出小说领域存在“一书各本”的现象,如《水浒传》就既有容与堂本为代表的“文繁事简本”,又有插增水浒本为代表的“文简事繁本”,还有明代袁无涯刊本为代表的“文繁事繁本”、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本等等。面对同一小说而各本之间情节、文字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传统古典文献学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潘建国老师进一步指出,《水浒传》的情况在古典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戏曲、说唱文学的流动性相比小说则更甚。戏曲是一种场上的艺术,演员与戏班主随时可能为了适应场上观众或是表演的需要,而对戏曲的文本、宾白、角色进行临时变动——这就导致在同一作品的不同梨园传抄本之间,几乎没有办法用传统意义上的校勘学来进行版本的校勘。说唱文学的流动性则更显著,甚至已经越出刻本、抄本的范围,成为一种案头与口头,或纸上与田野之间的流动。基于传统古典文献学在俗文学文献研究中的种种不适应,俗文学领域有必要根据实际的学术情况,参照古典文献学的部分概念体系、方法理论,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有一定独立性的俗文学文献学。
那么,如何构建俗文学文献学?潘建国老师提出,或许可以参照程千帆先生《校雠广义》包含的四大板块——目录、版本、校勘和典藏,来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体系。接下来,他对这一路径作逐一的简略展开。第一是俗文学的目录学。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古代各种官私目录对其著录很少或几乎空白,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发生转折。在建设俗文学目录学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几个关键问题:一是需要确立俗文学在综合目录中的著录位置;二是在编制各类专科目录时,俗文学各分支的分类、应被著录的要素、各要素所使用的术语等等,也需要达成一致。第二是俗文学的版本学。在这一面向上,俗文学与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差异较大。一方面,古典文学最看重的宋元本、名家批校本、明初大黑口本、白棉纸本等在俗文学领域几乎没有,或存量极少;另一方面,俗文学又具有绣像本、评点本、梨园传抄本、晚清报刊连载本、明末清初析出单行本、节本与洁本、繁本与简本等独特的版本形态。因此,需要根据俗文学的特点,重新厘定版本的名目、类别,组建一套俗文学的版本术语。另外,俗文学版本的研究方法、理论,也还需要从学理上进行归纳、总结与提升。譬如运用“窜句脱文”、建立版本标记物等,就是梳理小说版本系统时较为简单有效的方法。
第三是俗文学的校勘学。潘建国老师认为,陈垣基于《元典章》所提出的校勘四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俗文学校勘。小说文本的有些“错误”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特别用意,如果根据“他校法”加以校改,不仅埋没或含混了俗文学的本来面目,而且会使其丧失服务于主题或思想表达的功能。由此,他提出现在的俗文学研究不妨学习当年陈垣的做法,在整理、校勘的同时,从大量校勘记中提炼出专门面向俗文学文本的校勘法与校勘通例。第四是俗文学的典藏学。他谈到,俗文学的典藏史较短,不足百年,但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私人收藏所占的比例,及其功能、作用较大,早期的俗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收藏家,一部俗文学的典藏史与其学术史几乎是同步同构的;二是海外典藏在俗文学领域意义重大,这种意义有时是整体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最后,潘老师总结道,出于学术的必要性,需要提出探索和建立俗文学文献学;且在他看来,可以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典藏学这四条路径、四个面向上去展开俗文学文献学的建构。
接下来,三位与谈老师围绕俗文学的“流动性”,分别立足戏曲、说唱文学、小说领域,做了或整体或个案式的阐发。
程芸老师首先从古代戏曲文献研究的角度做出补充和回应。他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流动性视野下戏曲文献学的对象和框架。他认为,孙崇涛先生《戏曲文献学》中的相关论述已经蕴含着文本流动性的核心认识,而如果作进一步的延伸,戏曲文学的流动性还包括变异性、层次性的问题,其本身还具有表演性与仪式性。因此,戏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戏曲的文学文本,即所谓的剧本,还包括大量与演出、改编、传播等各种“再生产”环节相关的文本。这些围绕在戏曲文学文本之外的“周边”文献往往更不稳定,它们频繁经历着增益、删削与改订,反映出戏曲的舞台风尚、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从而,程芸老师提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戏曲文本的流动性。一是时间维度的流动性,戏曲史上“曲无定本”的现象十分常见,几乎所有成功的戏曲文学作品都有一个被不断选择、改编、演绎的过程。二是空间维度的流动性,同一戏曲文本在不同地区,往往会被不同的声腔剧种演绎。三是戏曲形态本身的流动性,文本会在不同的表演形态中发生变异。
 接着,程芸老师聚焦于元杂剧文本的流动性来做更具体的阐述。面对臧懋循的《元曲选》与元刊本、其他明刊本、钞本之间的差异,程芸老师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存真”的角度对臧懋循擅改文本的做法提出批评;但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不能机械化与走上形而上学,不能将所有文本差异都一概归咎于臧懋循,并以此来评价与贬低《元曲选》。在他看来,元杂剧的版本问题关系到对元杂剧的基本文献、演剧形态、思想倾向、风格特征、艺术成就等等方面的认识;既是一个保存元杂剧真貌,即所谓“存真”的问题,也包括对其背后意义的阐释与发掘。元杂剧属于俗文学的范畴,作者往往门第不显、地位卑微,有些就是下层艺人,即便是一些文人创作,恐怕也不会如刊行诗文集那样,能由作者自己来把关他的“原作”,故而所谓的“原本”并不会被刻意保存下来。直到明代中叶,元明杂剧的文体体制才逐渐整饬化、规范化。此外,元杂剧首先是一种表演文学,很多文本就是以诉诸表演为直接目的,表演本身的流动性、变异性使得元杂剧在流播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同于“原本”的差异。
接着,程芸老师聚焦于元杂剧文本的流动性来做更具体的阐述。面对臧懋循的《元曲选》与元刊本、其他明刊本、钞本之间的差异,程芸老师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存真”的角度对臧懋循擅改文本的做法提出批评;但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不能机械化与走上形而上学,不能将所有文本差异都一概归咎于臧懋循,并以此来评价与贬低《元曲选》。在他看来,元杂剧的版本问题关系到对元杂剧的基本文献、演剧形态、思想倾向、风格特征、艺术成就等等方面的认识;既是一个保存元杂剧真貌,即所谓“存真”的问题,也包括对其背后意义的阐释与发掘。元杂剧属于俗文学的范畴,作者往往门第不显、地位卑微,有些就是下层艺人,即便是一些文人创作,恐怕也不会如刊行诗文集那样,能由作者自己来把关他的“原作”,故而所谓的“原本”并不会被刻意保存下来。直到明代中叶,元明杂剧的文体体制才逐渐整饬化、规范化。此外,元杂剧首先是一种表演文学,很多文本就是以诉诸表演为直接目的,表演本身的流动性、变异性使得元杂剧在流播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同于“原本”的差异。
这种流动性也引发了程芸老师对戏曲文献研究的新思路做出一些理论化的思考。第一,在流动性观念的指引下,我们可能会更重视文本中流动、变异的细节。通过对文本采取历史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立场,强调回到文本产生、形成与变化的历史语境,关注文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变化性、层次性,以及这些流动、变异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或可以重新检视某些戏曲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流动性的观念也能为戏曲文本的整理与校勘带来新思路。程芸老师发现,目前学者在校勘时对各版本有不同的取舍,造成校勘结果各有异同,如果能建设一种结构化、智能化的数据库,这一问题或能得到较为理想的解决。第三,流动性的观念也有助于我们从学术方法、视野等方面,与写本学、早期中国文本的生成、域外的俗文学文本等等相关研究进行对话。总而言之,通过将流动性的观念、意识上升为一种理论方法的自觉,来建构流动性视野下俗文献研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对于推进俗文学研究是大有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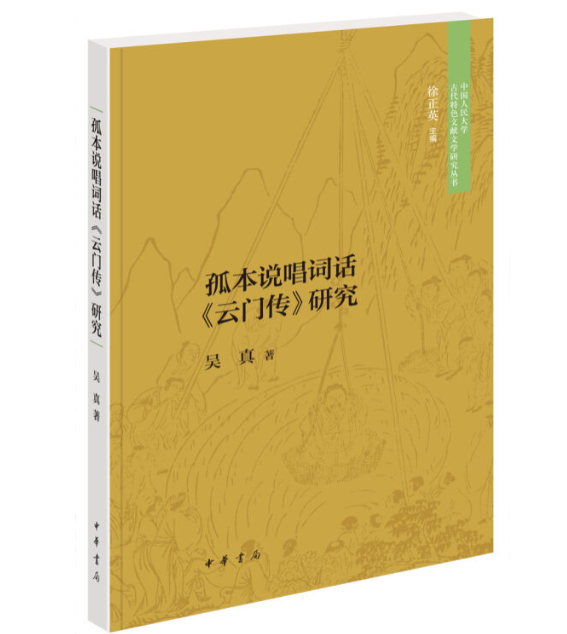
《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 吴真著
中华书局 2020年6月版
接下来,吴真老师以说唱文学《云门传》的个案研究为例,分享她对俗文学流动性的看法。首先,吴真老师将俗文学文献的流动性归纳为三种“无定性”,分别是作品无定类,作者无定名,文本无定本——这特别在说唱文学中得到了清楚的展现。明刻本《云门传》作为一个说唱文本,从1930年代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以来,首先面临无从归类的问题。它既不见于明清公私书目的记载,亦未见被民国以来的说唱文学编目叙录提及。它先后被不同编目者归入道家类、集部曲类传奇、小说演义等类别,但无一定位是正确的;直到马彦祥先生在自己的私人藏书目录中将其归入弹词鼓词,《云门传》才算遇到了知音。从《云门传》的归类困境引申开去,古代说唱文学研究在整体上也面临三大困境。第一,在说唱文学的体裁命名中,一部分是地域性称呼,一部分又是体裁性的全国称呼,这使得对说唱文学某一类目的编纂与体裁研究常要面临哲学上的能指与所指困境;第二,说唱文学存在记载的断裂,文本内部记载与社会史外部记载有时并不一致;第三,存世的元明说唱文学文本十分稀少,要研究清楚它的源流发展就更加困难。此外,说唱文学的独特性还表现为文本形态的现场性和口头性,如《云门传》全书注出了300多个难读字、正读字、多音字的读音,可能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或演出者在现场进行诵读。
吴真老师接着谈到,《云门传》研究的另一困难在于其作者无法定名。从中唐文人薛用弱的小说《集异记》、《太平广记》到《云门传》,再到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八《李道人独步云门》,《云门传》的李清故事经历了文言小说——说唱文学——白话小说的演进。其中,《云门传》对于李清故事的白话说唱体改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从文本中完全找不到这位作者的踪迹。为了推测作者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创作语境,吴真老师多次去到故事的发生地山东青州,从《云门传》产生的地方语境中理解文本。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她发现书中描述的许多地方社会场景都能在现实中得到还原;再结合嘉靖、万历年间云门山的全真道教复兴背景,推知《云门传》就是仙人李清的信徒为了宣扬李清信仰而创作的道情说唱。一些云门山的历史遗迹可能现在已经湮没,但借助于过去的影像与地方志记载,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云门传》的地方信仰语境。她进而提到,《云门传》的产生也与明清之际山东的说唱文学环境隐隐相关——曲阜、临淄、淄川、青州一带恰为此期说唱文学最为蓬勃发展的区域。
第三重困境是说唱文学文献的“文本无定本”。俗文学的异文本恰恰说明了俗文学文献的特定流动性,每一种写本或刊本都是对传播过程中口头演述的记录,每一种异文都是反映传播过程中地域性、社群性甚至信仰性的独特表述。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对传世经典文献“元本”、“古本”的追求,同时也不应将异文之间的差异作为“勘误”的标准,反而应该更加重视仪式场、市场演述语境、地方社会的差异给同一题材说唱文本带来的文本变异。同时,无定性的俗文学文本也可能在历史上经历一次经典化或者凝定固化的过程。如冯梦龙《醒世恒言》对《云门传》说唱文本的整理与改编,就是一种经典化过程,通过对文本流动性的控制,最终产生了比较固定的强势文本,甚至覆盖了原来的说唱。这一固化过程如何进行,则带来了俗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如冯梦龙大量删改《云门传》中的演出套语“留文”就是一种典型的处理方式。最后,吴真老师附带提到,冯梦龙唯一新添的东岳庙前老盲人演唱《庄子叹骷髅》情节,实为晚明时期流行于江南宝卷、小调、道情、徽州滚调、杂剧传奇等各种体裁的热点题材。这反映作家文学并不只对俗文学进行直接固化,也可能视俗文学为一个资源库、体裁库,在截取、叠加的基础上加以固化。
如果说说唱文学的文本是水的流动,那么小说文本的流动性可能就是沥青的流动。以此为引,李小龙老师开始讨论小说领域中校勘法则的应用问题。首先,他充分肯定了陈垣校勘四法的意义与价值。在他看来,陈垣先生从大量校勘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个校例具有极强的逻辑自洽能力与包容性,不仅是文献学、校勘学的指导性纲领,而且在小说校勘中的适用程度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仍有一小部分不合适的情况,它们虽然占比不大,却非常重要,且极易被忽略。接下来,李小龙老师依次给出小说文本中的校勘实例,来说明校勘四法的应用局限。
首先是对校法。古典小说存在“一书多本”的问题,两种本子之间如果差异非常大,我们可能只能尊重每一版本的内在逻辑,而不能简单套用对校的方式来对某一本子进行复原。本校法关注文本前后的逻辑自足,这在小说里有时也不合适。如《红楼梦》第三回提到贾母给黛玉一个名唤鹦哥的丫鬟,但此后鹦哥去向成谜,成为红学界的一桩公案。而在第二十九回黛玉身边所领的丫鬟中,除了紫鹃、雪雁,还有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春纤,程乙本便采用本校的方式,将此处的春纤替换为鹦哥。李小龙老师指出,这一校法从本校上来讲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春纤在此后章节中仍有出现,并不是作者无形之中随意添加的人物,不可与鹦哥的身份问题混为一谈。根据贾母同时送珍珠给宝玉,并改名为袭人的情节,以及脂砚斋在紫鹃第一次出现时所作的批语“此乃鹦哥化名”,可知紫鹃很可能就是改名后的鹦哥,只是曹雪芹分别作了一明一暗的处理。如果用本校法改正,文本逻辑就会发生错乱。
又如《霍小玉传》引用的李益诗句“开帘风动竹”,在李益原诗中作“开门复动竹”;《红楼梦》提到妙玉最喜范成大之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因而自称“槛外人”,而原句实际作“铁门限”——我们同样不能用他校法来加以订正,否则就可能打乱文本逻辑,抹杀作者的本意。最后是理校法,如《南柯太守传》描述淳于棼婚礼时有群女来贺,谈恺本《太平广记》作“皆侍从数千”,沈与文钞本作“数十”,《唐五代传奇集》便据以校改,但我们不能完全从现实情理进行推断,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蚂蚁所变,达到数千也是合理的。
在实例的基础上,李小龙老师对这种局限性予以总结说明。第一,对校法的最大逻辑是一个理想的元本的存在,校勘的最终目标或理想状态也是还原作者的元本。但小说作者未必是常态,文本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我们无法评判我们的校勘最终要求哪一作者之真,这就给对校法的使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第二,本校法的逻辑前提是前后叙事的一贯性,但小说会根据人物性格或作者的虚构原则进行细小的修正。一致有一致的用意,不一致也有不一致的叙事逻辑。第三,他校法之所以不适用,是因为小说引用他书的某些资料,主要服务于作品逻辑而不完全是现实逻辑。第四,由于小说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不完全是自然逻辑的迁移,依据自然之理进行理校有时也会出问题。李小龙老师进一步指出,小说校勘存在两大类问题:一是作者问题和虚构问题,小说作者不固定,且具有虚构的逻辑;二是被动错误与主动错误问题,小说的很多错误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建构的,改正了反而会抹杀作者的本意。
但另一方面,我们仍可以谨慎地使用校勘四法。他特别表示,在小说的同一版本系统中可以使用对校法;前后一贯的文本,尤其是文言小说文本的校勘可以使用本校法,但需注意前后语境的问题,分清作者逻辑和人物逻辑;在使用他校时,要注意作者意图和人物意图的冲突,关注作者引用他书资料时是否经过了个人改造;使用理校则要以人物形象的逻辑为本,而不能全凭自然逻辑。因此,校勘四法在小说中既适用又有限度,只要对其局限性加以注意,它在俗文学校勘中依然可以发挥理论指导性的意义。
最后,潘建国老师为本次论坛作结。首先,他再次重申了建立俗文学文献学的学术必要性。俗文学内部的差异虽然也很大,但相比俗文学与经史、雅文学之间的差异还是要小得多。因此,归纳出一些俗文学内部彼此都适用的通例或方法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行的。此外,俗文学文献性质上属于文学文献,不能只考虑纯文献学的概念、术语,方法、理论,也要注意到俗文学本身的文学性、艺术性或场上性也会对相对恒定、标准化的文献学构成冲击,需要兼顾文献、文学、文体、搬演体制等几个层面的因素。最后,潘建国老师希望借本次活动,呼吁更多学界同好在俗文学文本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理的归结与提升,从而将俗文学文献学真正地建构起来。
“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
(2021年)
第五讲:集部文献与文学史研究
主讲人: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第六讲: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
引言人: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与谈人:程芸(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七讲: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
主讲人:常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孟庆楠(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第八讲:文献学新视野与宋代文学研究
主讲人: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与谈人:吴国武(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第九讲:诗文校勘与文艺的关系
主讲人:钱志熙(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