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聂溦萌老师
2021年5月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溦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尚书省与汉魏南北朝文书行政体制的演进”。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翾、杜永彬、黄晓春、马忠文、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聂溦萌老师在论坛伊始即指出,杜佑《通典》批评隋唐官制六尚书与寺监并立,“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其说影响很大。近代学者严耕望,始以《唐六典》对官制的记载为主要依据,辨析唐前期尚书与寺监的不同职能、地位,指出“尚书六部为上级机关,主政务;寺监为下级机关,掌事务”。这篇文章对于后来唐代三省六部制研究的基础性意义自不待言,但它在辨明唐代尚书与寺监关系的同时,对于魏晋南北朝制度的印象依然沿袭《通典》,如文中评论唐代行政制度是将南北朝之旧贯“釐革变通,加以系统化,于是旧官不废,而体系精神焕然一新,‘化臭腐为神奇’,此之谓矣。”这种负面评价也对魏晋南北朝制度研究影响很大。
夹在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图景首先是政治、制度的衰乱,而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南方地区的开发等则更多获得史家的积极评价。这种局面是魏晋南北朝制度史研究缺乏原生性观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出土资料,尤其是出土文书是拉动制度史研究进展的重要动力,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书相比汉唐数量较少、发现较晚。这样,汉代或唐代的制度史研究已经提出了关键议题,形成了研究范式,后起的魏晋南北朝制度研究容易受到影响。


魏晋时期文书载体从简牍向纸张过渡
但严耕望描述的唐初制度之精致整齐,显然不会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我们再反思汉魏以来所谓“叠床架屋”或“重复混淆”的制度,倘若果真如此,为何会历经数百年至唐代方得厘正呢?即便这种混乱确实存在,也应该是某种发展的副作用,此期制度史研究更应当回答这个发展的正面缘由是什么。“重复”主要指尚书机构在三公与九卿之间的兴起。尚书是由皇帝侧近逐渐走向外廷的,但尚书在汉唐间的发展不仅仅是君臣权力争夺,或各机构之间权力侵夺的问题。“尚”是主掌,“书”即文书,尚书是最早出现的专门处置文书的部门,其职能发展也一直紧密围绕文书。文书行政是一个庞大精细的文字处理体系,需要各种技术性保障:如文书处理的环节、层次的增加,文书档案收藏、整理、调阅水平的提高,故事典章编纂的发展等,而汉唐间尚书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文书行政体系发展的一个重点。
在上述问题意识下,对汉唐间与尚书相关的文书与政务还可作深入考察。《唐六典》注引《汉官仪》云“尚书令主赞奏事”,祝总斌解释“赞”即“唱读”,《汉书·霍光传》记载废昌邑王的场景,也是尚书令在殿上读群臣请求废黜皇帝的奏。这个过程落实在文书程式上,是汉代批复型诏书在奏文之后的“制曰”和“某年月日尚书令某奏某宫”。曹魏以后,现场进读奏章改由中书负责,这或许是由于东汉中后期长期由太后主政,士人不能入内奏事。不过曹魏以后的文书程式并没有随中书、尚书职能的替换而改书“中书令奏某宫”,“奏”依然是尚书使用的字眼,它指向的实际工作则是在尚书机构内单独展开的一套复杂的政务处理流程。尚书官员会对上奏内容进行审核、讨论,提供处理意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事务性质的不同引导后续政务处理分层。整体观察汉代与魏晋以后文书体系的关系,尽管《独断》所载的汉代王言分类体系到魏晋以后发生明显改变,但《独断》诏书三品分类的政务分层逻辑在南朝元嘉太子监国有司仪注所见的文书体系中变得更加明显,说明了汉魏以来行政体制演进的总体方向。另外,从纵向上把握汉唐间与尚书相关的文书变迁,也为进一步解读南朝元嘉太子监国有司仪注提供了基础。

居延汉简元康五年诏书颁下文书及附件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谈论了典章制度与实际运作的错位,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理论认识,尤其是中国相对于西方官僚制的差异,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发展的关系等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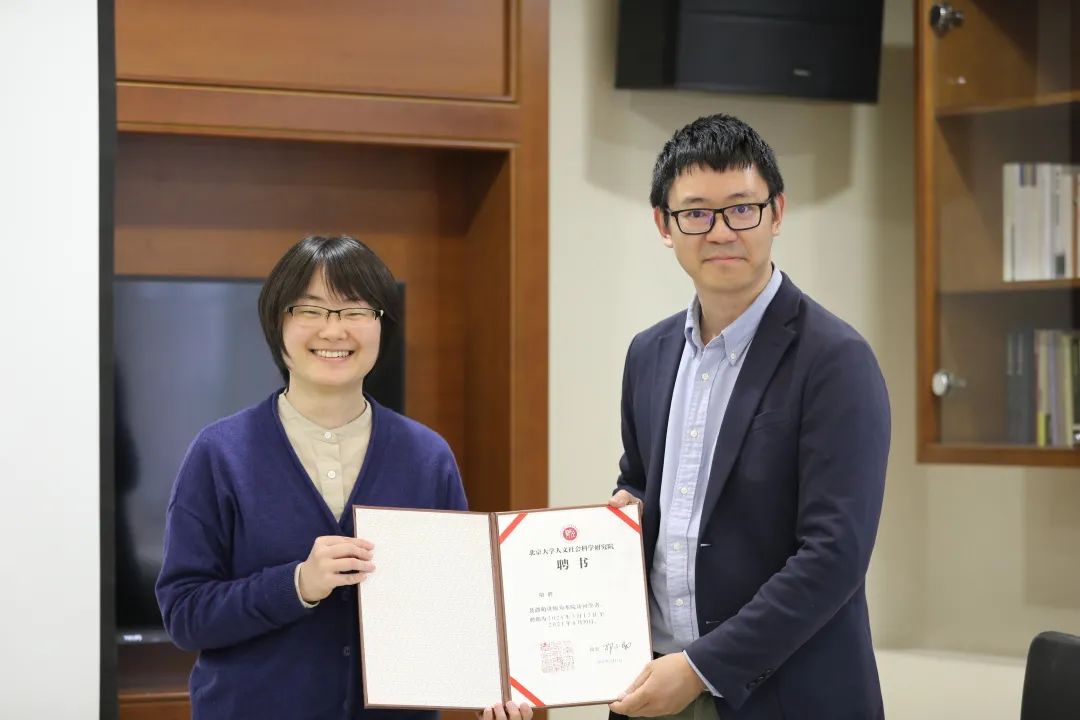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为聂溦萌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