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於梅舫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铸经与破经: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路径分歧及旨趣离合”。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於梅舫教授表示,康有为、梁启超既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又是中国文化近代变迁的关键要角,深入了解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的异同离合,可以对晚清今古文之争的本来事实与后来描述和近代创新文化的不同取径提供新的认识。

康梁师徒合影
大体来说,清代的今古文分争,如亲预其事的学人所说,“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到乾嘉以后,学人虽然分别今、古文,却旨在“欲明汉人专家之学”(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以征明古书、古学(章太炎《与支伟成》),并非具有入主出奴、此是彼非的门户派分的见解。晚到清末,“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其中,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树立“今文”经排斥“古文”经,大张“今文”经学门户,引起较长时段内士林官场的连续反响,是今古文学术史论述中的枢纽要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康有为,今古文分争在晚清学术史上是否存在,也并非不是问题,更何况成为清代学术史上与程朱陆王、汉宋议题鼎足而三的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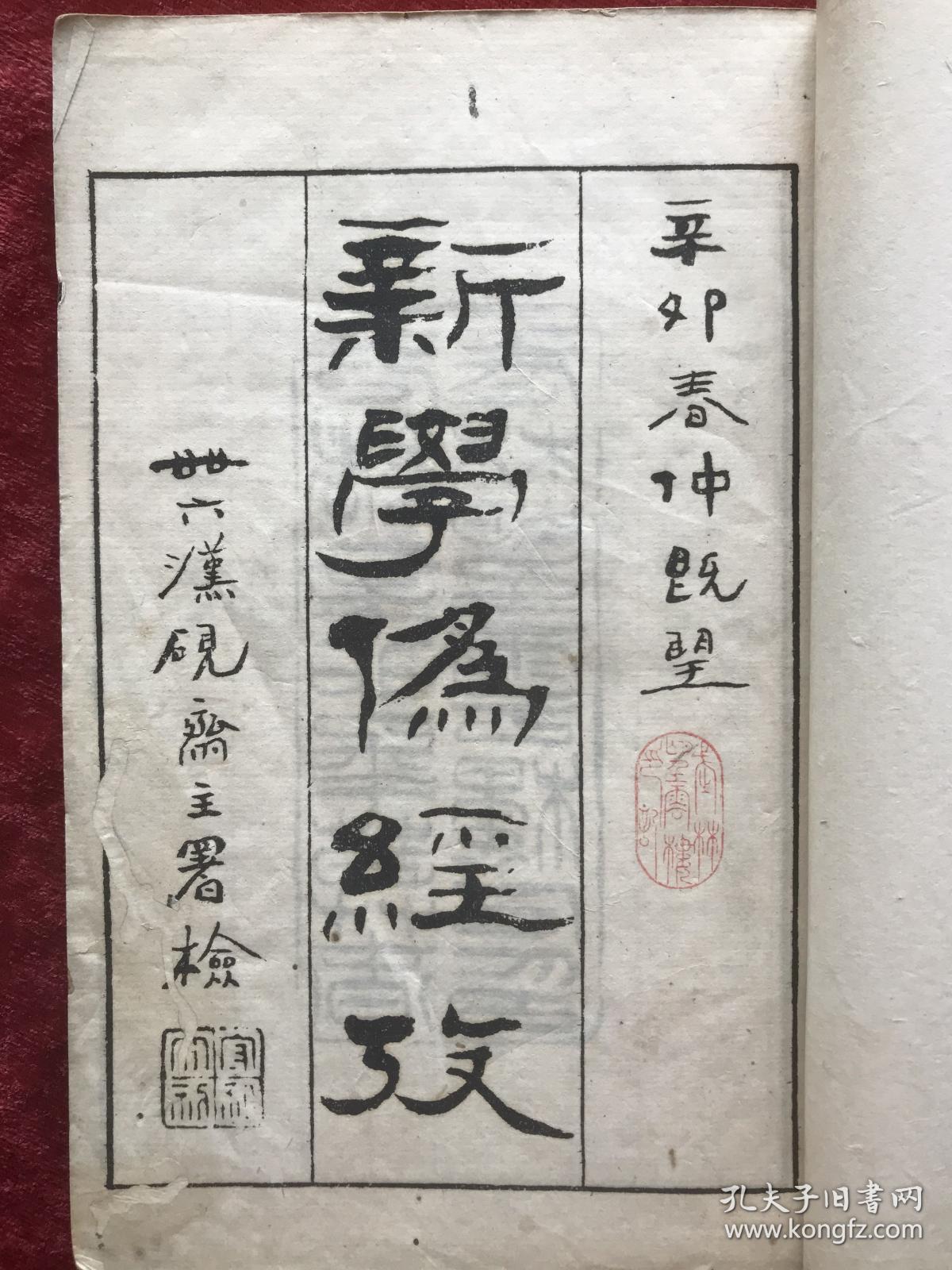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
以《新学伪经考》为例,此书在康氏本人整体学术体系中具有极为扼要的起始一环,所谓撰“《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全书烙有鲜明的康氏印记,“最富于自信力”地表达:刘歆遍伪群经,故需截然破除古文“伪经”,恢复今文“真经”,进而申说孔子“真经”所匹配的托古改制的义理(康有为将托古改制定为义理)。此类表述,容易让研究者的视角,更关注于康有为确立公羊学的“今文经”立场,又因为康氏今文经学立场中鲜明的孔子托古改制的意味,亦牵及康氏的变法(改制)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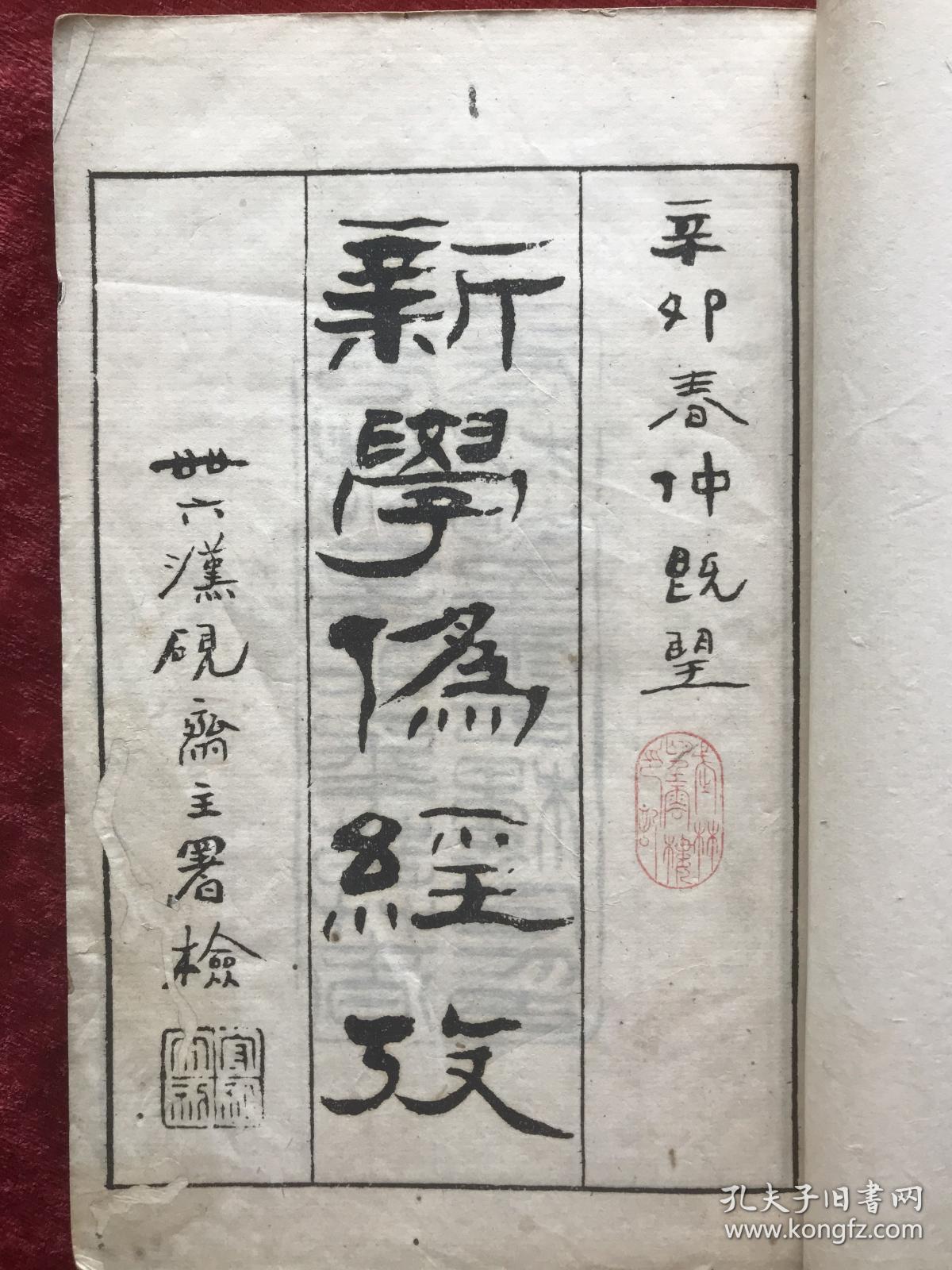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
于是,今人在研究晚清今古文之争的历史时,比较自然地出现了以下两种互为影响的倾向。因康氏学说中具有浓厚的公羊学色彩,易于将公羊学与清代今文经学划上等号,故一面以公羊学在清代的发生、兴盛来条理清代的今文经学历史,一面则又以清代中前期流行的公羊学说来解释康有为的学说。事实上形成一个自成首尾的逻辑圈。这很有可能导致一个结果:既不能正确说明康有为学说形成的历程,同时也消解了清代公羊学自身发展中的丰富意味与现实关系,也难以恰当的把两者的真实关系链接起来。
因此,至少需要将清代公羊学演进的本事本意作为一层。康有为学说的形成史及其因时不同的政学抱负为一层,时人对于康氏学说的接受反响及其政学意涵为一层。
扼要来说,在康氏政学理念演进过程中,受到朱子学说及人格的深刻影响。康氏对于朱子学说的运用或是塑造,因事因时而更易,此种变化,体现康氏抱负与措施之因时递进。《教学通义》在其中地位关键。康氏由中法马江之役的时局所刺激,受师友学说之影响,更受到龚自珍国家衰乱由于人才不兴,人才不兴缘于学术不能复古,学术复古在于回复“六经皆史”一代有一代之治(学、礼、法、道)之“学”的影响,并以编礼书的朱子为典型,撰成《教学通义》,呼应龚自珍的“自改革”理念,有意编礼书铸经典。至上书受挫则大感世道淡薄,感觉世道大异,教也须大变异,于是发愿如刚果近禅的朱子,“托于教”,诗集与致友人函内大张其旨,遂在回粤乡居的时候,撰《伪经考》。《伪经考》重订“真经”及其传承系统,并发挥原(新)教义,是其立(变)教的重要一环。这一学术操作,与朱熹集注《四书》别出于《五经》、序列“道”的传承、确定新义理的精神极为近似。康氏既以朱熹为偶像,更愿以朱熹之道而为新时代的朱熹。通过运用刘歆伪造经典之说,在立“真经古本”的基础上,“恢复”孔子改制之的“微言”而别于《四书》的“大义”,树立以公羊学“孔子改制”义传承为核心的道统。确立真经的本子(铸经),传承的新道统,而对于“改制”之义的诠释则很具有一些“民权”说的时代特色,显示康有为“世变异则教异”的特质。这一颇具“开放性”的阐释,对于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的认识与接受,产生极大影响。
《伪经考》具备双层特质:既有“熔铸事物”,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历史的“考据”过程。更有在“考据”揭明“真经”、重订“道统”后,打开的发明“素王改制”义理的窗口。康氏发明“素王改制”的义理,又多“因承”于“公、穀、董、何之口说”,本身也带有很强的“康子口说”(包括文字)色彩,因此也包涵了康氏因时而进的政学理念与抱负,其中不时显露出突破中国固有纲常,以师统驾于治统之上的“非常异义”。《伪经考》本身的这一“双面”特质,深刻地影响、约束了当时士林与官场中人物对于《伪经考》的认识,故出现多歧的政学反应。
当时的士人、官员,因对于《伪经考》特质的了解深浅,出现迥异的认识与反应。大体上说,单纯读《伪经考》文本者,多从学问的角度视之,或称其可成一家言,或惜其考据粗疏,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也便是从“考据”角度,判其“考据”的得失,纯粹出于论学的一面,此一层恰恰不见所谓今古文之争的意味。与康氏有较深往来者,则从其口说、书信中,了解《伪经考》更深一层意思。
於梅舫老师指出,其中人士,大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正面视之,如江浙的宋恕、孙宝瑄、夏曾佑等,论学虽未必与康氏完全合辙,却颇认可《伪经考》显现出来的“君民共主”的民主色彩。尤其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中坚,不仅赞同“素王改制”说,且在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湘学报》、《湘报》多有推扩,也因此引起张之洞及湖南当地士绅的强力反弹。一类对此有所保留、忌讳,如朱一新,由《伪经考》所显露的素王改制义,怀疑康“日新义理”,“独言圣人罕言之理”,颇有“逾义理之学”,便是指其有突破君臣之分。
更进者,如张之洞早先对康氏虽颇表赞同,多加赞助,而在知悉其“素王改制”说后,对其政治抱负顿起忌心。《孔子改制考》不仅因“素王改制”说已经口说大为传播,而且很容易将此与“素王改制”说联结为一体,更是引起极大争议。从张氏一系列行动及幕僚的观察,甚至有将康氏视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之意,可见对于康氏《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反对,主要围绕“素王改制”说的“非常异义”、近乎于“教匪”的“异心”,绝非所谓《公羊》《左传》的今古文学问之争,也不能以改革与守旧限之。事实上,最早将张之洞排斥“素王改制”说,与今古文“学术”之争联系起来,并在后续的追忆、书序内不断加强这一说法者,就是康有为本人。而被张之洞引为批驳康学同道的章太炎,也承认“古文”不成专业。然而,在学术史的叙述中,康、章早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壁垒坚实的今古文之争中的典型代表。
康梁师徒往往合称,却多有不同。吴樵致函汪康年称:“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而在熔铸中西古今学说中,康有为有铸经(旧瓶)成新学(新酒)之取径,梁启超一开始则以破除孔教经典为开始,以国家学说为圭臬,扛起了道德与学术的革命旗帜。
二十世纪初,受国家思想影响甚深的梁启超,一心想建立“新中国”(取其《新中国未来记》之语),为达此目的,具体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因应时势而变动,与此政治主张密切配合、联贯呼应的是其“新学”之道。创办取之程朱所释《大学》“新民”之义的《新民丛报》为其重要举措。《新民丛报》以及《新民丛报》的核心文章《新民说》反映此期梁氏的新民理论。“新民”理论架构的根本逻辑非常清晰有力,适于报章鼓动宣传。核心在于“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如何讲新民之道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中称学术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如旭日升天”,可以左右国家、世界之前途。“新之有道,必自学始。”“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 故梁氏“新民”理论脉络可谓由新学——新民——新国家,层层递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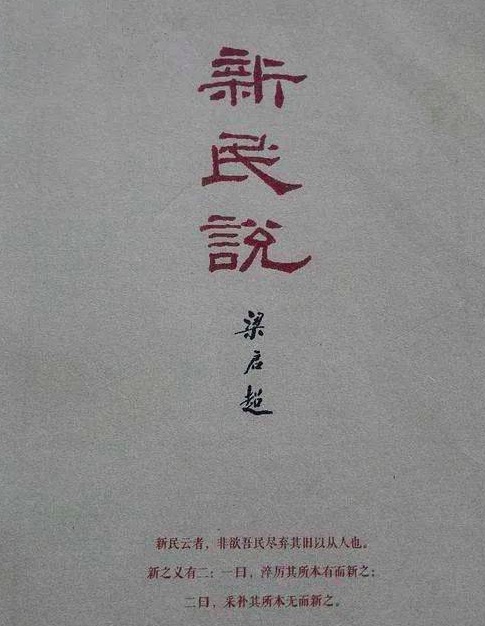
梁启超《新民说》书影
相比于学术,“宗教今已属末法之期”,显然要超脱康有为的笼罩,确立自己的新学之道。不过这里需要辨析的是,这一理论架构中从“新学术”到“新道德”的描述,看似“新学”居于根本底蕴的位置,实际上这一路径面对的是受众,即梁氏在“新学术”中传递“新道德”。而在梁氏本人理念中,“新道德”已是确定的清晰目标,一定程度上“新学术”转而落于推阐“新道德”手段的地位,而非由“新学术”确定“新道德”。
在《新民说》中,梁氏以“公德托始”,在他的描述中,“人群之所以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而中国素来缺乏“国家”观念,缺乏对应“国家”的“公德”,则国家之新精神亟待发扬,因此梁氏在此期有一决断——“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而新道德与新伦理相应,“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有意突破维系王朝道德的纲纪,反映此期的“革命”性。
新学反而是为这一新道德服务。 1902年秋,梁约黄遵宪一道编辑《国学报》,便称:“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恃此足以立国矣。”作为早期推动国学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的国学,实际上是要与公德(新道德)相配合。而“泰西”的国家学说下的国民道德居于核心地位,成为“进化”的方向,“革命”性植根于此。故梁氏号召“我国学者”,要善运学术之力,重心其实并不在如“倍根、笛卡尔、达尔文”的创造,而在于“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点出“磨洗”的味道。与此相应的是,梁启超又《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以为文明进步,思想自由为其总因。欧洲有今日,皆由“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孔子之所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故反对“以保教为尊孔子”。意图打破一尊,主张学术与道德的进化与革命。
然而如果去除相对恒定的价值、意义、信仰的来源与根基,主张一切以进化与新为准,实际上即是标准可以随时更改,道德的维系力实际永远出于变动中。1903年拒俄运动带来的革命风潮,使得梁启超可以目睹革命的真正狂潮,意识到“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则无需道德……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印于脑,则道德之制裁,已无可复施,而社会必至于灭亡。”因此反思道德革命之说。好友黄遵宪观察梁“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返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
1904年,梁启超开始调整新学之道。最能说明这一变化后的理论架构,是《节本明儒学案》(1905)《例言》所说道学与科学的分别与联系:“道学与科学,界限最当分明。道学者受用之学也,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科学者,应用之学也,藉辨论积累而始成者也。随社会文明程度而进化者也。故科学尚新,道学则千百年以上之陈言,当世哲人无以过之。科学尚博,道学则一言半句可以毕生受用不尽。”即以道学为锚定,而科学则仍取进化观念。可谓破经后的折衷。
因此,《近世之学术》(1904年)可以一面赞赏清代汉学考证的科学精神,一面可以批评乾嘉时代学人整体上的道德失序。《欧游心影录》反对科学万能提倡精神之学而《清代学术概论》则欣赏清代汉学的科学方法。1920年代大力提倡“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可见其成为梁氏后半生的重要理论架构。
梁启超之前沟通中西有两大架构,一为中体西用,一为体用合一。梁启超则在二者之后,对二者皆有重要修正。梁启超在戊戌之后尤其是1902年左右“猖狂言革”期间,大反张之洞中体西用说,主张“道德革命”,打破纲常,确立国家伦理,欲将自由、破坏、权利、民权等国家思想输入国内,改造国民,主要持“以西释中”的理念,几乎与主张体用合一的严复一致,事实上寻求的是从学到政的“西体西用”。
至美洲之行后,梁氏对于破坏之说大起反思,反对“瞎闹派”的革命, 对于固有道德的追逐成为沟通中西思想的修正之道,因此提出近似于中体西用说的“中体”(根本)以为定锚。然而,他的学、道两分的理论架构,并非要回到中体西用说。对于中体,或者说固本之根本,梁氏绝不同于冯桂芬以至张之洞所要维持的“纲常名教”。相反,虽然此期的梁启超已领会到暴力手段下革命的破坏性,因此强调道德的恒常不变性,不随时势的演变而发展,然其道德说的维持目标,恰恰在于皇朝“纲常”对立面的国家与社会,其建立立宪政治国家以取代专制政府的理想,并未改变。
同时梁氏对于严复体用合一之说,也有修正。最巧妙的地方,在于梁氏所谓“道”,有体之实,甚且有中国固有学说精神之实际,却并不居于或者说强调“中体”的地位。虽然梁氏以阳明学尤其是以黄宗羲为后续发展为核心的良知学说,作为“道”的提倡方向,但在整体理念下,道实际上出于“良心之自由”,故“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虽然,行道德,仍受社会性的约束,“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 因此,“道”(体、文化)既无中西之别,为普适的理念,只是因社会性质而表现有异,内在则同,既然如此,注重进化性的科学自然可以在此根基上生长,回应了严复的中西体用合一说。
在於梅舫老师看来,梁氏之说,既能因应立宪政治与建立国家的时代要求,使专制政府无借口可言,又避免吸收西学而失去中国固有之精神,以至于最终走向全盘西化尽“化为西人”。康梁师徒沟通中西文明的不同取径,显现近代创新文化的多样性,而因应时势的变化与保有价值、意义的根本之间的紧张,长期考验着哲人的智慧与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