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闵雪飞作题为“弑神诗人佩索阿——读组诗《守羊人》第八首”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闵雪飞副教授提出了理解佩索阿的基本前提:佩索阿的诗强调感觉主义,读者必须直面文本,全身心地进入作者的历史时空去体会诗人的作品。因此,要进入佩索阿的世界,我们有必要化身为佩索阿同时代的普通人去了解他的一生。

费尔南多·安东尼奥·诺隔伊拉·佩索阿
佩索阿全名为费尔南多·安东尼奥·诺隔伊拉·佩索阿(Fernando António Nogueira Pessoa),生于1888年6月13日,卒于1935年11月30日。他在里斯本市中心圣卡洛斯广场(Largo de São Carlos)旁的公寓中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童年痕迹:在《黄昏印象》中飘荡在黄昏村落上空的钟声来自于家旁的殉教者圣母大教堂(Basílica de Nossa Senhora dos Mártires)的塔楼;《斜雨》第六首中的剧院和后院之间交织,起源于正对着居所的圣卡洛斯剧院(Teatro de São Carlos)。佩索阿的父亲是业余音乐评论家,常去剧院听音乐。然而,在他还小的时候,生父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带着幼子随丈夫移居南非德班。
在这里,佩索阿接受了标准的维多利亚式英语教育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岁时,佩索阿回到葡萄牙定居。后来,诗人用异名写下《再访里斯本》(LisbonRevisited)一诗,并在其中再次提到童年:“以更遥远的心,以更非我的灵魂”。从此,诗人定居于里斯本,直到最后因胰腺炎而死。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同样是英文:“我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I know not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佩索阿曾表示:“我的父国是葡萄牙语。”那么相对的,英语则是他的母国——佩索阿在英语上寄托了特殊的情感。在他死后,葡萄牙政府决定将其葬在代表着大航海时代荣光的热罗尼姆修道院(Mosteiro de Jerónimo)。佩索阿的墓碑为一桩三棱柱,三面分别刻有三个主要异名的诗一首。

佩索阿的墓碑
闵雪飞副教授认为,佩索阿的普通生活与其文学生活呈现出惊人的矛盾。总体来说,作为普通人的佩索阿,一生平淡无奇,充斥着虚无之感:他不曾拥有过成功的职业生涯,两次创业均以失败告终,基本上仅靠翻译英文商业信件为生;亦未受到过爱神的亲睐,终生未婚。
相比之下,其文学生涯却是波澜壮阔的。在佩索阿的文学背景之中,主要由英伦传统和古典传统构成,并未包含葡萄牙文学。他将自己的文学生活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青春期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接受教育;第二青春期居住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国度中,并受到了雪莱的影响;第三青春期则栖于希腊与德国的哲学家、法国的颓废诗人和瑞士作家诺尔道的思想之中。他曾经创造过一个前异名亚历山大·瑟迟(Alexandre Search),与另一异名阿尔瓦罗·德·冈波斯(Álvaro de Campos)一起寄托了英伦自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闵雪飞副教授
佩索阿在葡萄牙文坛内以叛逆的形象出现。根据其发表的《从社会学层面思考的葡萄牙新诗》,佩索阿对于葡萄牙文学有自己的创见,文学中蕴含的便是改造葡萄牙社会的热望。佩索阿认为:正如莎士比亚先于护国公克伦威尔出现一样,在每一个政治的高峰出现之前,必然要有文学的高峰作为前奏铺垫。而无论法国还是英国,但凡在文学上贫乏、不能体现民族精神时,政治上也相应地缺乏建树。而葡萄牙作为民族的存在,是与其“诗化存在”相生相伴的。目前,其诗化已经完全停滞。葡萄牙若要重获昔日的荣光,必须在诗学上寻找新的超越,要“扩大”、“荣耀”葡萄牙的诗化存在,实现“超卡蒙斯”(Super-Camões)。这一壮举依赖于一个“强大的人”(homem de força)——只有他才能实现“超越”。而佩索阿所做的种种文学上的努力,都是在为这个“强大的人”出现做出应有的准备。
闵雪飞副教授认为,“超卡蒙斯”意味着将已经被葡萄牙人奉为神祇的卡蒙斯赶下神坛。佩索阿将要重写卡蒙斯已经书写过的葡萄牙大航海,并予之以新的意涵,“使其能与我之所是相结合”。在此之上,佩索阿要通过神秘主义等方式创造出精神上的乌托邦——“第五帝国”,重新在思想上赋予葡萄牙民族以生命。这种精神构建的努力浓缩在其生前发表的唯一一本诗集《音讯》(Mensagem)中。诗人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待并重新审视了葡萄牙的历史,解构了昔日的神话,又再度构造了属于葡萄牙民族的新神话。
佩索阿对旧神的解构始于渎神。为此,他创造出了“出离的自我”——异名,赋予了他们各异的人格,并让这些异名组成一个不存在的异教徒团体。据佩索阿自述,在某一天突然感受到了神启,并写下了《守羊人》和《斜雨》。团体领袖阿尔伯特·卡埃罗(Alberto Caeiro)就此从佩索阿的身体之中诞生。闵雪飞副教授通过给出异名的代表作品,具体解释了每个异名的典型特征。在署名为阿尔瓦罗•德•冈波斯的《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中,卡埃罗就是异教本身。阿尔瓦罗·德·冈波斯是脾气上的异教徒,反叛社会对他的所有要求;安东尼奥·莫拉(António Mora)是异教徒的哲学家,提供哲学意义上的讨论;里卡多·雷耶斯(Ricardo Reis)是性格上的异教徒,一个有着拉丁“范儿”的老学究,追求古典文学的形式,对文明持有极端保守的看法;佩索阿本人则是“一团乱麻”,追求神秘主义。至此,佩索阿构建出了两组二元对立:佩索阿和卡埃罗代表了神秘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对立;冈波斯和雷耶斯代表了对文明反叛和保守的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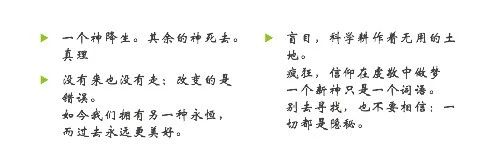
佩索阿《圣诞》节选
在介绍完佩索阿的生平以及基本的文学架构后,闵雪飞副教授解读了署名为阿尔伯特·卡埃罗的组诗《守羊人》第八首,进一步分析了佩索阿“渎神”以及重新建构新神的方式。
卡埃罗的诗大都运用感觉主义,通过简单的词语带给读者明晰的感受。感觉主义认为所有的客体都是我们的感觉,而艺术就是在把感觉转换为客体。因此所有的艺术就是试图一种感觉转换为另一种感觉。卡埃罗的诗即是在传达感觉,《守羊人》第八首伊始,读者就能看到“春末的中午”“梦”“照片”这样的话语,皆是在传达一种直观的感觉。诗人希望读能者拥抱感觉,敞开内心以体会诗。

Santo António e o Menino Jesus(圣安东尼奥和耶稣)
《守羊人》一诗打破了一般人对于基督教的认知。通过亵渎神灵,圣父、圣母、圣灵被降至极低的位置。诗中的圣子离开了虚伪的天堂,抛弃了束缚于十字架上永远赴死的角色,重新变成婴孩回到人间。在孩童耶稣口中,圣父、圣母变成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形象:圣父是一个满嘴脏话的老头,常常随地吐痰;圣母则不知爱为何物,永远都在以织毛活消磨永恒。圣灵则完全变成了动物——一只鸽子。它总是用喙又啄又挠,栖息在摇椅上把线团弄脏。佩索阿解构了旧三位一体,祛除了基督教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性。
作为替代,圣婴和诗人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圣婴向诗人传授世间的真理,教他如何观察花朵,观察石头。石子就是进入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于是,他们就在房子前的台阶上用五颗石子做游戏。圣婴、诗人和全部的存在手拉着手一同走在路上,三者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玩累了之后,圣婴在诗人的臂弯中安睡,诗人遵循着一种充满洁净与母性的仪式慢慢脱掉圣婴的衣服。在这里,诗人实质上自比圣安东尼奥。他进入到圣安东尼奥的梦中,获得了圣婴耶稣的神祇,为重构圣三位提供了正当性。当诗人面对赤身裸体的圣婴时,人与圣婴、自然在象征意义上达成了新的盟约。至此,佩索阿建构出新的神话。

渠敬东副院长为闵雪飞副教授颁发文研院未名学者聘书
评议环节,周伟驰研究员发言。他表示,佩索阿的神秘主义具有神智学的痕迹,和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有几分相近。而阿尔伯特·卡埃罗(佩索阿异名)的诗中也有一些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相似的思想,即明显的反象征主义。反象征主义强调直观经验、直观感受,反对宗教的象征主义和哲学上的种种术语,意图去除所有形而上的部分。周伟驰研究员认为,卡埃罗的思想可能受到了其他东方教派(例如庄子)的影响。在卡埃罗的眼中,生活就应该像行云流水一样,思想反而是一种“疾病”。冈波斯虚无主义的想法应该产生于尼采所形容的“上帝已死”之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人失去了上帝便不得不独自面对死亡,因而感到空虚、不安。冈波斯的《烟草店》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他所描述的状态。雷耶斯则以《棋者》为代表体现了其对完美形式的追求与审美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