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六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面具魅影——对非洲现代文艺实践中传统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程莹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
 讲座伊始,程莹老师分享了自己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博时期的一些经历,回顾了自己如何在非洲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内部产生了与欧美同门相龃龉的“第三世界”关怀与问题意识。在拉各斯的一次学术活动中,她发现当她提及“第三世界”时,同行的欧美学者对“第三世界”这一术语表现出几乎是本能的拒斥,他们认为这是饱含意识形态色彩的、“略显过时的”的外交辞令,不值得再被重提。这一经验引发了程莹老师的思考:“第三世界”作为历史内涵极为丰富的术语,将在何种程度上为来自中国的、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者提供思想资源?来自中国的外部研究者在进入非洲时,应该如何就自身所处的语境展开反思,这种立场和位置性如何影响了中国学者在面对非洲文本时的问题意识?程莹老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她之所以关心非洲现代文艺实践中如何处理传统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和经验体系中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讲座伊始,程莹老师分享了自己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博时期的一些经历,回顾了自己如何在非洲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内部产生了与欧美同门相龃龉的“第三世界”关怀与问题意识。在拉各斯的一次学术活动中,她发现当她提及“第三世界”时,同行的欧美学者对“第三世界”这一术语表现出几乎是本能的拒斥,他们认为这是饱含意识形态色彩的、“略显过时的”的外交辞令,不值得再被重提。这一经验引发了程莹老师的思考:“第三世界”作为历史内涵极为丰富的术语,将在何种程度上为来自中国的、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者提供思想资源?来自中国的外部研究者在进入非洲时,应该如何就自身所处的语境展开反思,这种立场和位置性如何影响了中国学者在面对非洲文本时的问题意识?程莹老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她之所以关心非洲现代文艺实践中如何处理传统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和经验体系中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在这场讲座中,程莹老师结合自己对非洲文学和文化文本的理解以及在非洲的田野调查经验,以面具这一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符号为线索,追溯并讨论了面具仪式传统是如何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非洲电影、文学、戏剧和艺术实践中被不断再现的。她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归到非洲文本自身及其社会语境梳理非洲文艺实践中的“传统化”倾向,而不是给非洲作家作品简单地贴上“现实主义”“神秘主义”或“民族主义”等标签。这一工作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性与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当代非洲社会怎样通过不断地动援传统来回应现实社会的张力、特别是后殖民时代剧烈的社会变迁。
 程莹老师选取的第一个关于面具的文本是“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的《黑人女孩》(La noire de…)。《黑人女孩》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由非洲导演制作完成的长片,在非洲电影史上极为重要。这部电影围绕来自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黑人女孩Diouana展开,Diouana受雇跟随白人夫妇远赴法国。影片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她最初接下这份工作时曾赠送白人夫妇一个非洲面具作为礼物。而对白人夫妇而言,这一礼物只是作为室内装饰品增添了他们家庭内部的异国情调,他们也从未将来自西非的礼物赠予者Diouana看作是平等的交流对象。在法国所经历的奴役和监禁般的生活最终导致Diouana在白人雇主的浴室中自杀。
程莹老师选取的第一个关于面具的文本是“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的《黑人女孩》(La noire de…)。《黑人女孩》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由非洲导演制作完成的长片,在非洲电影史上极为重要。这部电影围绕来自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黑人女孩Diouana展开,Diouana受雇跟随白人夫妇远赴法国。影片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她最初接下这份工作时曾赠送白人夫妇一个非洲面具作为礼物。而对白人夫妇而言,这一礼物只是作为室内装饰品增添了他们家庭内部的异国情调,他们也从未将来自西非的礼物赠予者Diouana看作是平等的交流对象。在法国所经历的奴役和监禁般的生活最终导致Diouana在白人雇主的浴室中自杀。
《黑人女孩》取材于导演塞姆班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真实故事,而影片对面具的使用颇有深意。回看面具的赠予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我们会发现,白人夫妇对面具的关注点在于其“本真性”——他们之所以认为这个面具是“真正的”非洲面具,是因为它与那些卖给白人的纪念品不同,这一面具来自达喀尔的本土社群、是真正在“原始”仪式语境中使用过的面具。这一对面具“本真性”的要求实际上隐喻了(西方)非洲艺术史的几次重要的辩论。因此,要全面理解非洲面具在《黑人女孩》中深刻的象征意义,首先需要梳理非洲面具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西方殖民者掠夺和观看的历史。程莹老师指出,对非洲艺术品的“本真性”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殖民语境下的伪命题。就像在谈到非洲艺术时,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及非洲面具曾作为某种“原始艺术”的代表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比如谈及毕加索以非洲面具为灵感),在这场遭遇中,非洲面具所代表的非洲文明被视作是“部族的、本真的、拜物教的”。这种惯性认知下,非洲艺术似乎要通过西方艺术批评体系才能真正获得价值。实际上,西方收藏家对“本真性”的定义意在凸显“先进理性的”欧洲文明与“原始传统的”非洲文明之间的区别。
 也是从这个层面上,程莹老师认为,塞姆班在电影中借助面具等传统文化符号实则触及了现代非洲文化和艺术所面临的一种普遍境遇。结合《黑人女孩》的拍摄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围绕面具的对话实则隐喻了非洲本土电影生产的困境与“再现”的悖论。《黑人女孩》等一系列早期非洲电影的拍摄最初都受法国文化部的资助,从电影语言的选择到受众的考虑再到内容的呈现方式上都受到掣肘。法国出资方希望在塞姆班的电影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非洲,也就是丛林遍布、充满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的非洲,而塞姆班则拒绝在影片中将非洲人进行“他者化”的处理。影片的主人公——黑人女孩被呈现为一个典雅美丽的现代女性、和好莱坞电影当中呈现的黑人女性形象截然不同。Diouana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拥有姓名的角色,全片以她的内心独白为线索展开叙事。面具每一次出现,都与Diouana的身份认同紧密关联。在《黑人女孩》结尾,Diouana自杀以后,白人雇主把Diouana的遗物连同面具打包送回了达喀尔Diouana母亲的家中。影片在村落里的黑人小男孩戴上面具,一路追随仓促逃离的白人男性的场景中结束。在此,面具似乎构成了某种警告和惩戒的功能。程莹老师指出,在后来的《哈喇魔咒》(Xala)等电影中,塞姆班也通过类似于面具这样的传统文化符号不断重新叙述传统。如杰姆逊所言,塞姆班并没有怀古主义的倾向,那么他反复叙述传统的原因就值得深入探究。而他如何再现传统,或者说探索出一种“本土化的”、“非洲的”电影语言来阐释传统,则代表了非洲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也是从这个层面上,程莹老师认为,塞姆班在电影中借助面具等传统文化符号实则触及了现代非洲文化和艺术所面临的一种普遍境遇。结合《黑人女孩》的拍摄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围绕面具的对话实则隐喻了非洲本土电影生产的困境与“再现”的悖论。《黑人女孩》等一系列早期非洲电影的拍摄最初都受法国文化部的资助,从电影语言的选择到受众的考虑再到内容的呈现方式上都受到掣肘。法国出资方希望在塞姆班的电影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非洲,也就是丛林遍布、充满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的非洲,而塞姆班则拒绝在影片中将非洲人进行“他者化”的处理。影片的主人公——黑人女孩被呈现为一个典雅美丽的现代女性、和好莱坞电影当中呈现的黑人女性形象截然不同。Diouana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拥有姓名的角色,全片以她的内心独白为线索展开叙事。面具每一次出现,都与Diouana的身份认同紧密关联。在《黑人女孩》结尾,Diouana自杀以后,白人雇主把Diouana的遗物连同面具打包送回了达喀尔Diouana母亲的家中。影片在村落里的黑人小男孩戴上面具,一路追随仓促逃离的白人男性的场景中结束。在此,面具似乎构成了某种警告和惩戒的功能。程莹老师指出,在后来的《哈喇魔咒》(Xala)等电影中,塞姆班也通过类似于面具这样的传统文化符号不断重新叙述传统。如杰姆逊所言,塞姆班并没有怀古主义的倾向,那么他反复叙述传统的原因就值得深入探究。而他如何再现传统,或者说探索出一种“本土化的”、“非洲的”电影语言来阐释传统,则代表了非洲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程莹老师指出,传统习俗和象征超自然力量的符号在非洲文学、电影、艺术文本被频繁地使用,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母题。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在当代非洲的日常社会实践中传统文化元素或者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被非洲本土的知识分子(Harry Garuba、Tejumola Olaniyan等)总结为一种“复魅”(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现象。“复魅”与韦伯所说的伴随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到来所发生的“祛魅”形成对照,也就是说,在现代非洲语境下,那些思想中的魔幻成分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持续不断地将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机制放到传统的、神话的世界观下进行观照。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人将之称为非洲的“重新传统化”。理解这种“复魅”现象及其复杂性,是解读非洲现当代社会文化实践以及人伦日用的关键。
接着,程莹老师以多个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为例具体阐释了后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重新传统化”问题及其与社会文化肌理间的关系。在关于文学文本的讨论中,程莹老师讨论了钦努阿·阿契贝的小说《瓦解》和沃莱·索因卡的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的面具场景。学界认为《瓦解》对伊博文化传统的重新书写,在当时的非洲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建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程莹老师的讨论没有停留在这一结论上,她选取了重新回顾《瓦解》等小说中关于伊博族面具仪式舞的细节,借此来讨论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对传统及其“本真性”的理解和再现方式。阿契贝在似乎不经意间描述的多个伊博族面具场景生动地体现了面具仪式在伊博族社会中的具体运作机制,他实际上细致地再现了伊博民族传统信仰的权威、以及当地社群如何参与和维护这种权威,建构一种与超自然力量相关的“社会真实”。
这种超自然力量主导的世界观今天依然是当代非洲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同样围绕面具符号与面具场景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则采用了“死亡仪式戏剧”的框架,体现了经典的非洲现代戏剧家如何在本土神话体系中基础上建构悲剧体验和美学理论。在这部作品中,索因卡将传统的死亡仪式和现代表演、现代戏剧并置(后者相对较少涉及到灵魂附体trance、spiritual possession等过程),在悲剧与挽歌意义的本质上重新拷问死亡仪式和死亡传统的今日意涵。这些文学和艺术实践丰富了对“传统”的界定,从不同视角挑战了开头提到的那种西方艺术史和艺术批评领域对于本真与虚假、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认知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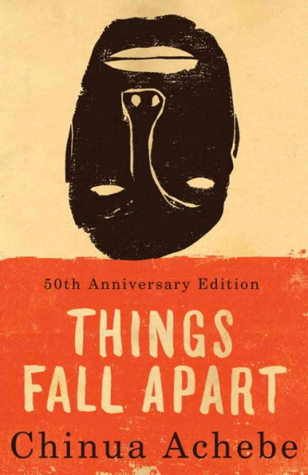 程莹老师总结道,的确如尼日利亚学者阿戴莱克·阿戴埃科奥(Adélékè Adéèkó)所言,非洲人文学发展的对抗(去殖民)语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流思想的激进倾向以及本土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阿契贝、索因卡等人的创作以及文论呈现出非洲本土主义论争的许多不同面相。索因卡可以被理解为“形式本土主义者”,他强调非洲戏剧创作应该从传统仪式的结构和框架中被理解,而阿契贝则更偏向“实用本土主义者”,他认为非洲作家可以采用所谓西方的现代艺术形式和语言来展开创作。除此以外,重要的非洲文学代表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则可以被归为“语言本土主义者”,因为他在创作的后半阶段主张非洲的文学作品坚持认为非洲作家应使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非洲知识分子围绕本土主义的论争展现出诸多面向,体现出传统与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
程莹老师总结道,的确如尼日利亚学者阿戴莱克·阿戴埃科奥(Adélékè Adéèkó)所言,非洲人文学发展的对抗(去殖民)语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流思想的激进倾向以及本土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阿契贝、索因卡等人的创作以及文论呈现出非洲本土主义论争的许多不同面相。索因卡可以被理解为“形式本土主义者”,他强调非洲戏剧创作应该从传统仪式的结构和框架中被理解,而阿契贝则更偏向“实用本土主义者”,他认为非洲作家可以采用所谓西方的现代艺术形式和语言来展开创作。除此以外,重要的非洲文学代表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则可以被归为“语言本土主义者”,因为他在创作的后半阶段主张非洲的文学作品坚持认为非洲作家应使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非洲知识分子围绕本土主义的论争展现出诸多面向,体现出传统与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
接下来,程莹老师强调不应将非洲现代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的本土主义倾向与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黑人性运动”混为一谈,或者简单将其划归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脉络之中。本土主义论争事实上批判早期“黑人性运动”所携带的本质主义倾向,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度。他们对于什么是所谓独立之后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物质性语言的象征意义,以及独立国家如何面对殖民遗产等方面,都存在共同的疑问。许多文学和艺术实践者其实一直激烈地反对将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阵地。20世纪60年代,在塞内加尔、几内亚、刚果(布)等非洲国家出现了国家力量主导的“本真性作为国家意识形态”(“Authenticité ” as national ideology )的政治运动。具体策略包括设立相应的国家文化机构,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艺术节等,倡导社会文化礼仪中回归传统等。然而,许多同时期的非洲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对此保持了批判性的距离甚至对抗的姿态。例如,尼日利亚在举办第二届世界黑人与非洲艺术大会(FESTAC’77)时,选取了贝宁象牙面具作为这一文化盛事的标识。而索因卡和非洲著名音乐人费拉·库蒂(Fela Kuti)则以不同的方式批判了FESTAC’77对传统文化及历史的肤浅挪用。如果我们考察索因卡和费拉·库蒂等人的文学和艺术实践,不难发现,对后殖民国家政权及其权力的滥用进行激进的反叛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面向,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审美特征。在后殖民非洲,“安静的”写作或者艺术实践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书写、音乐等艺术形式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需要不断挖掘与再现神话经验中的审美、结构和政治意涵,处理和回应错综变幻的现实世界与政治秩序。尼日利亚评论家Tejumola Olaniyan曾提出 “the postcolonial incredible”这一概念阐释后殖民非洲“危机与悖论作为常态”的社会状况,并认为这种语境是理解非洲艺术及其审美特质的关键(详情可参见Tejumola Olaniyan的Arrest the Music一书;此外,著名的理论家Achille Mbembe也在On the Postcolony一书中对后殖民非洲社会权力关系与审美属性间的关系有类似阐释)。这也再次表明,文艺作品中传统的认知与再现问题的复杂性,是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多重张力作用的结果。


左图为FESTAC’77海报上的面具,右图为费拉·库蒂在他的专辑封面上以讽喻的方式进行挪用
最后,程莹老师分享了一些当代青年表演文化和社会运动中面具符号的再现。她通过自己在博士期间对非洲青年文化所做的调查试图说明当代非洲社会文化并没有像一些批评家所言日渐偏离“仪式中心”,相反,以超自然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符号依然在公私领域不断浮现。尼日利亚走上街头抗议的年轻人通过在脸上画上同已逝的反叛音乐人物费拉·库蒂一样的白色面具,重新召唤和“复活”费拉的反抗精神。


左图为表演中的费拉·库蒂; 右图为青年人在社会抗议中通过涂抹面具来复活费拉·库蒂
在社会抗议中,年轻人通过“复活”和引用传统的面具仪式,以实现一种与权力阶层的对话方式。复活传统的过程,不仅仅是策略意义上的,更像是一种对传统背后的社会秩序及其所代表的未知的、僭越性力量的体认。在这一意义上,传统的生活哲学和所谓的复归传统的倾向,也持续地影响着当代尼日利亚人对于公民社会和自身角色的理解。这种和戏剧与表演相关的文化政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后殖民的非洲国家,看似现代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机制实则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共政治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也许正如传统仪式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归结的那样:“非洲的仪式传统,比现代主义更加现代。”
戴锦华老师在评议阶段指出,程莹的研究是在非洲本土、通过对非洲当代社会的介入和体验当中来展开的,她所做的是一个非常内在的研究。程莹从传统等核心概念出发试图去捕捉非洲现当代文本表达的丰富性,并在其中发掘那些并非二元对立的、纠缠着的情境与经验。戴老师指出,这些经验在第三世界语境中具有普遍性,每一个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与霸权结构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都面临类似的情境——一方面,统治者会利用所谓的传统或者本土性作为一种合法化的表述;另外一方面,传统又始终是一个反叛者,或者说是一个自觉的文化生产者,是作为创作者必须去直面和尝试去重新赋予力量的一种基本资源。这个因素使我们处在一种紧张的拉扯之间,而实际上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可能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与此同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资源脉络和这样一种现实的实践方式在各个具体语境中间的呈现是有所不同的。比如,程莹就非洲的研究和观察就指出,传统不仅作为符号学的展演,本身也是一个现实文化建构的方式。这些共通性以及不同的具体面向值得我们的研究和关注。

戴锦华老师为程莹老师颁发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