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就地造景与资本平台——农村高端民宿的兴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杜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杜月老师首先从一个真实的经验问题讲起。杜月老师指出,近年来中国农村高端民宿逐渐兴起,之所以会关注农村高端民宿的发展,与十年前的成都调研有关。在调研中看到,农民大规模上楼后,资本进入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然而当时却不清楚它的收益点在何处,农业本身周期长、回流慢,还有各种人工费、流转费和其他成本,这使得当时的调研者都困惑于资本为何投资农地?
通过此后十年对于成都的调研获知了在投资高端民宿之前,资本与农地结合的一些方式。第一种盈利方式是打政策的“擦边球”。例如,当地一公司流转了620亩农地,购买了60亩挂钩指标,在购买指标后,利用国家农业补贴违规建设住宅并出售,售价为每平米2000元。因为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修建住宅,所以该项目被判定为违建,老板也因非法集资罪被逮捕。投资农地的资本另一种盈利方式是搞政策投机,即等待流转的农地被开发征用。当地一家大公司流转了大面积的农地,利用国家补贴进行农地改良并建设地上附着物。一旦被国家征地拆迁后,土地补偿费用归土地所有者,地上附着物补偿归流转土地者。总之,上述两个投机的现实案例都说明了,下乡的资本并没有找到与农地结合的点。换言之,资本投资到农地,并没有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关于资本为何没有找到与农地的结合点,杜月老师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框架去思考这个问题。资本投资农地,其实关乎到“土地商品化”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土地商品化的讨论,最早是从马克思开始研究的。马克思认为,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过程,必须“将土壤(soil)变为资本(capital)”,即将具象的土地变为抽象的地租;同时,具体的人抽象为挣工资的劳动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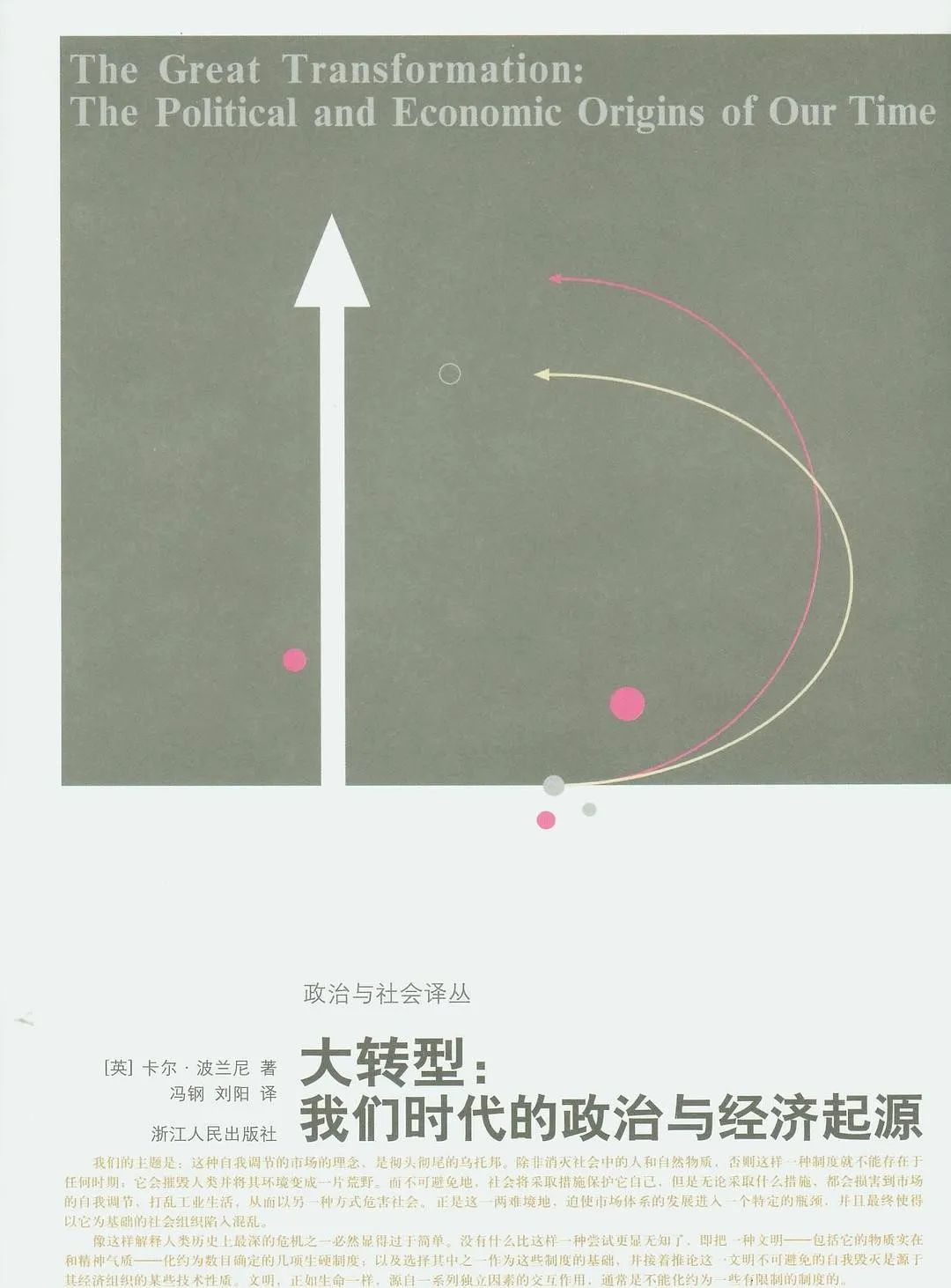 接着马克思的思路,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将土地作为虚拟商品 (fictitious commodity )进行思考。在波兰尼看来,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本身并不是商品,并非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只有将其虚拟化,才能抽象为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并且依靠这种虚拟,市场才能组织起来。沿着这一脉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会出现“过度积累” (over-accumulation)和“剥夺性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必然过程。过度积累是指剩余资本无法找到可谋利的出口,因此只能被闲置;而剥夺性积累则是指一系列资产以非常低的价格释放出来,过度积累的资本就可以进入这些资产,将它们做更有利的用途。前些年,资本疯狂涌入楼市,导致楼市竞争愈发激烈,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而资本的收益率随之不断降低。大量过剩的资本找不到可投资的出口,继而转向征用农地,以一种非常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资源释放,将其修建成楼,通过房子的买卖,赚取一级土地市场的价格(买地)和二级土地市场的价格(卖房)之价差,满足投资的需求。这解释了在全球各地出现抢夺土地(land-grabs)的现象。所以,土地的商品化往往伴随着两种结果,一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征地),二是土地用途的变化(工业、地产)。
接着马克思的思路,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将土地作为虚拟商品 (fictitious commodity )进行思考。在波兰尼看来,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本身并不是商品,并非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只有将其虚拟化,才能抽象为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并且依靠这种虚拟,市场才能组织起来。沿着这一脉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会出现“过度积累” (over-accumulation)和“剥夺性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必然过程。过度积累是指剩余资本无法找到可谋利的出口,因此只能被闲置;而剥夺性积累则是指一系列资产以非常低的价格释放出来,过度积累的资本就可以进入这些资产,将它们做更有利的用途。前些年,资本疯狂涌入楼市,导致楼市竞争愈发激烈,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而资本的收益率随之不断降低。大量过剩的资本找不到可投资的出口,继而转向征用农地,以一种非常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资源释放,将其修建成楼,通过房子的买卖,赚取一级土地市场的价格(买地)和二级土地市场的价格(卖房)之价差,满足投资的需求。这解释了在全球各地出现抢夺土地(land-grabs)的现象。所以,土地的商品化往往伴随着两种结果,一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征地),二是土地用途的变化(工业、地产)。
但是无论是农地所有权的变化,还是用途的变化,近年来在中国都变得越来越难。这和我国近十年实行的特别严格的耕地保护法规和实践有关。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永久基本农田”概念,指出任何情况下禁止改变基本农田用途,不得以任何方式挪作他用;2009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保增长、保红线”行动;2017年,国家完成了全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意见。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技术治国”的治理理念下,国家通过“制图”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把新增耕地落实到图上,并通过卫星遥感的手段,实现了对基本农田的精准执法和有效监控。这解释了为何资本难与农地进行结合,因为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不能轻易使农地发生任何所有权和用途的变化。
随之,杜月老师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在国家严密控制之下,所有权和用途都无法发生变化的农地如何商品化?沿着提出的问题,杜月老师引出她最新的研究发现,资本找到了与农田结合的新方式,那就是投资高端民宿。杜月老师的田野地点是在成都R区,从自然环境和自然禀赋来看,有着工业污染历史的R区并不是发展高端民宿的最佳选择。但恰恰是在R区,于2016年引进了多个高端民宿的项目,并且该区的旅游收入在2016年之后有了快速增长。
杜月老师结合在田野地点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资本用来流转的农地,很多都被用来“造景”了,大面积的农地被用来种植草坪、花卉、果树等。被制造为“景观”的农田,本质上是为了衬托和点缀资本修建的高端民宿。这种“农田造景”的理论意义与英国和北美经验的“农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理论完全不同。农村绅士化的理论是指,大量中产阶级从城市涌向农村,是受自然环境(河、湖、森林、山)或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吸引。而R区“农田造景”的最大作用是将民宿与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分隔开来。首先是将高端民宿与污染的农村空间相隔离,其次是将民宿与自然风景区相隔离。脱离自然的民宿,看似是反逻辑的行为,但高端民宿做的是小众市场,注重挖掘乡村的价值,具体挖掘的就是用来造景的农田价值。

农地被改造为草坪用于造景,
远处这棵孤树被用于“营造孤独感”
“农田造景”也使得民宿脱离于农村社区,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与村庄完全隔离开来。物理隔离较为容易做到,但要做到与村里人完全不接触的社会隔离却很难。在民宿中运行着一套成熟的体系,它能保证住客与村民的接触呈现出高度选择性的特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民宿老板于当地挑选的民宿管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如清洁、做饭等。15个院子配置18至20个管家, 分为A、B角,职位与人员配比为1:1.3。此外,公司还会对管家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如怎样处理客人与村民发生的矛盾。
脱离了村庄和自然环境,民宿的空间被彻底独立出来,看似是一个完全真空的环境,既接触不到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接触不到外来的社会生活。这个真空的空间为资本提供了极佳的平台。首先,这个独立的空间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客户体验店,客人可以深度体验民宿提供的一系列产品,如高级家庭影院、最新的智能家电和高端护肤产品。在这种意义上讲,民宿成为了资本平台,各种品牌对客户展示和开放。资本不但占满了空间,也充斥了时间。这体现为民宿为客人安排的行程满满的日程表。例如,观看展览、组织团建和会议、体验传统手工艺、开展亲子活动和儿童教育等,所有行程均由专业的内容商提供。总之,客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资本细致规划。
这种民宿的发展和运营模式可复制性很强,在本村运行的高端民宿,可以完全复刻在另一个村庄。最初的民宿培训是用来培训当地的农民。但到后来就变成了标准化的培训模式,培训对象也由农民变成了当地的领导干部和充当未来项目经理的当地年轻人(多有政府关系)。这种培训模式是高度上的抽象化,它能将本村具体的经验抽离,然后复刻到任何地方,无关乎于复刻地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研究发现,民宿产业吸引了一部分楼市的资本投资农地。资本之所以能够农田造景,与国家大面积的土地增减挂钩和农民上楼有密切关联。土地增减挂钩实施后,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大片的土地被复垦和连片化,其次是农民耕作半径增加,使得耕种土地越来越困难。结果就是,村集体面临巨大的农田流转压力,大片的农地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流转。在这种背景之下,地产公司、地产联合基金和政府资金(一部分扶贫款)等纷纷投资于高端民宿,被抽离出来的民宿空间变成了一个资本的平台,各种家电、家具、家居和化妆品等品牌,以及多种多样的内容商都涌入其中。


不同的造景模式:人工造景与原生态农田
接下来,杜月老师讨论了大规模的农田造景对村庄造成的影响。首先,从农业方面来看,林木从经济作物变为景观作物,民宿公司对种植的林木没有产量要求,只求林木保持景观的功能。从当地的统计数据来看,R区的年均播种面积和年均粮食产量均在2016年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下降的时间点恰好与引进这些大型造景的民宿项目的时间点相吻合。其次,从村庄方面来看,由于村庄的土地基本流转在一家公司手中,容易出现价格垄断和流转费拖欠。例如,调研中的一个村落,公司老板拖欠村民的土地流转费,导致村民到镇政府上访,最后镇政府通过规自局申请了区政府的维稳经费来解决公司的拖欠问题。
杜月老师最后总结道,在国家严格的农地保护法规和实践下,农地的所有权和用途都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其难以成为虚拟商品进入资本链条。资本通过“农田造景”的方式解决过度积累问题,转向发展高端民宿,使土地从自然与村庄中脱离,实现完全的虚拟化,完全抽离于它的自然和社会空间。虚拟化的空间成为了资本平台,吸纳多方资本填入。可以说,高级民宿本身成为了吸纳城市楼市资本溢出的一个出口。现在看来,这种经营模式可能会导致农业的减产和农地的垄断。

主讲人杜月老师
评议环节
在随后的评议阶段中,周飞舟老师将“土地商品化”的问题放在国家宏观政策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分析。周飞舟老师指出,杜月老师的理论研究框架是土地的商品化。中国第一轮的土地商品化,指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和征地制度改革之后,全国住房商品化热潮兴起,资本在各地圈地,地方政府“大兴土木”,引发的后果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问题。第二轮土地商品化则是指资本到农村圈地,即资本下乡。资本下乡后,大规模征用农村的流转土地,利用政府农业补贴,在农村社会开展农业规模经营。但资本在下乡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和难题,一是由于国家对于基本农业保护的严格规定,致使资本无法在圈来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无法修建商品房;二是下乡的资本投向农业领域后,往往与当地社会“水土不服”,投资的农业无法达到预期的收益。这是近些年农村社会学、农业社会学领域讨论较多的主题。面临两大困境之下的资本,近年又转向了投资农村地区的高端民宿,其实资本在农村不仅仅是“原地造景”,更重要的是建造了一个个庞大的“庄园”。
周飞舟老师认为,运用“政府——资本——农民”三方关系来理解土地政策问题会更加清晰。地方政府往往与资本纠缠不清,但是中央政府对于资本非常警惕,在第一轮土地商品化过程中表现为对土地指标和土地规划的利用保护,在第二轮土地商品化过程中则是强调基本农田保护,强调耕地“非粮化”问题。当资本的洪水越涨越高时,国家则是要把大堤修筑更高,以此来保护基本农田和农民的权益。中央政府的意图就是要防止耕地“非粮化”一般,防止农民无产化,筑起围墙抵御资本的侵蚀。这三者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土地政策的核心要害。
在提问环节,围绕不同地区民宿发展的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保护、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资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等问题,杜月老师逐一进行了解答。杜月老师补充道,真正理解资本在农村社会的做法,需要从土地制度入手,来理解国家、资本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目前,高端民宿就地造景的发展模式是它在数轮经验做法中总结出来的道路,这个做法非常有理论讨论的价值,因为它使农地高度虚拟化——也正因为高度的抽象性,使得这种模式可以在诸多地点,甚至是没有自然禀赋的地区进行复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