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1830年的世道与人心——《红与黑》与‘贝尔德案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王斯秧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映虹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田庆生评议。

 首先,王斯秧老师从讲座标题入手,解释司汤达为何以“贝尔德案件”为蓝本创作《红与黑》,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关于人性新发现的宝藏,当激情将人推到无路可走时,人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司汤达认为理想的作家是“诗人哲学家”,既深刻地认识人性,又能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触动人心。《红与黑》的手稿页边注释中多次写到的“木桩”一词,又叫“真正的原因”,思考人物性格如何导向行为,证明作家把小说当作认识人性的工具。
首先,王斯秧老师从讲座标题入手,解释司汤达为何以“贝尔德案件”为蓝本创作《红与黑》,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关于人性新发现的宝藏,当激情将人推到无路可走时,人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司汤达认为理想的作家是“诗人哲学家”,既深刻地认识人性,又能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触动人心。《红与黑》的手稿页边注释中多次写到的“木桩”一词,又叫“真正的原因”,思考人物性格如何导向行为,证明作家把小说当作认识人性的工具。
在司汤达之前,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人物观,认为人性普遍而永恒。司汤达却强调思想与情感的历史性与相对性。《红与黑》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超时空的人物类型,而是由大革命之后法国新的风俗所塑造的典型的历史人物,归属于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阶层、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德·莱纳先生和瓦勒诺是1825年左右法国一半有钱人的画像”,德•莱纳夫人是外省烦闷、拘谨的新风俗所塑造的单纯自然的迷人女性,德•拉莫尔侯爵是旧体制的大贵族,等等。小说副标题定为“1830年纪事”,因为作者借助司各特开创的历史小说类型来记录当下,以司各特描写中世纪的手法来描写当代,把历史小说转变成了现实小说。
王斯秧老师指出,呈现混乱且难以捕捉的当下,这与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的“浪漫主义”的定义是一脉相承的:“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因此感动同时代的人”。这样的写作观念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于连正是新时代所造就的、身份与性格都处在变动之中的人的真实写照。
接着,王斯秧老师梳理了评论家对小说标题《红与黑》的解读。读者普遍接受的政治象征层面的解释,是红代表士兵的服装,黑代表教士的道袍。像于连这样出身卑微的穷青年,如果早生20年,就可以追随拿破仑,在军队建功立业;可惜他晚生了20年,在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代,他只能披上教士的黑色道袍才能有出头之日。这种解释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当时的军装并不是红色的,黑色也不仅仅是教士的服装。在整部小说里,于连当家庭教师、教士、秘书,自始至终穿着黑衣服,这实际上代表着那一代年轻人的卑微地位。而于连摆脱自身身份的几个时刻,穿着由贵族馈赠的蓝衣服。如果仅从现实的角度解读颜色,这部小说应该是“蓝与黑”的对立,而不是红与黑。

(1700-1845年间巴黎城骑兵着装演变)
有批评家认为红代表革命、鲜血、青春、热情,黑则代表森严、肃穆、压抑和死亡,还有人认为红代表爱情,黑代表野心,等等。不过,各种猜测并无定论,只是感觉到红色似乎更倾向于诗学层面,黑色则更倾向于现实层面。它们的组合也许表达一种对立或共存、甚至互相转化的关系,也许暗示着于连这个人物的矛盾属性。
于连身上所集合的多重矛盾既源于他本身的性格,又与他的时代和社会处境息息相关。他的斗争始终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出身低微而才华横溢的穷人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外部斗争,一个是自卑又自尊的年轻人克服敏感的天性、给自己强加责任的内心斗争,两者相伴相生,但后者更为激烈,构成小说暗潮奔涌的深层脉络。小说这样形容于连:“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几乎天天都是风暴”。评论家普雷沃也说:“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首先在与世界作战;司汤达的主人公尤其在与自身的敏感作战,不断地跟自己为难。”
不过,从整体来看,变动不居的人物其实仍然具有内在逻辑。司汤达笔下最为关键的概念——力(énergie),有助于理解于连的种种行为。这种“力”指的是生命活力与动力,小说中德·拉莫尔侯爵无法定义的于连性格深处“可怕的东西”,包括意志坚定、愿望强烈,也包括情感强烈、感受深刻,使得人物能够更深地体会生活,介入生活。而于连枪击德·莱纳夫人的行为,最终显露了他被野心所掩盖的敏感与高傲,使他转向激情。这个行为让他在现实利益的层面失败,却让他在小说层面得到拯救。
王斯秧老师援引卢卡契的观点加以解释:“于连和司汤达的其他人物一样,不会向现实妥协,因此选择了死亡,以对抗现实的腐蚀。因此,不是贝尔德让于连举起枪,而是司汤达身上不可救药的浪漫精神。”小说家只讲述人物突如其来的行为,对其动机与信念故意保持沉默,让人物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让读者感觉到事件强烈的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反而是真实的标志。
由此,王斯秧老师点明,在于连这个脱胎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浪漫精神并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实合一。现实唯一的法则是无序、易变,人心的现实更是如此,小说也应通过多变的人物、无常的事件,呈现现实的丰富与厚度,这才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司汤达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家,又是现实主义的代表。
接下来,王斯秧老师借助评论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提出的“平行故事”概念,从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和语式三个层面,分析了小说家是如何在贝尔德案件的基础上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同他穿越的外部世界联结起来,在文本内部营造巨大的叙事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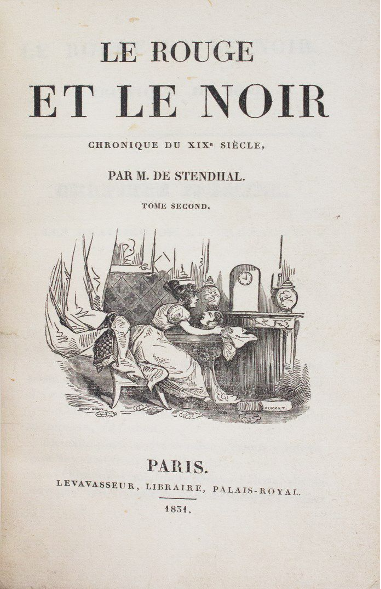 第一,小说结构建立在大革命之后、因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巴黎/外省”对立之上,以于连的上升为线索,呈现了复辟时期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把个体融入更为宏大的时代历史进程当中。司汤达由此展开早年在哲学论著《论爱情》中所划分的两种爱情,即激情之爱和虚荣之爱。维利埃和巴黎是催生这两种爱情的土壤,德·莱纳夫人在外省隔绝、谨慎的氛围里成长起来,得以产生激情之爱。而文明过度的巴黎,只能催生出虚荣之爱。
第一,小说结构建立在大革命之后、因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巴黎/外省”对立之上,以于连的上升为线索,呈现了复辟时期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把个体融入更为宏大的时代历史进程当中。司汤达由此展开早年在哲学论著《论爱情》中所划分的两种爱情,即激情之爱和虚荣之爱。维利埃和巴黎是催生这两种爱情的土壤,德·莱纳夫人在外省隔绝、谨慎的氛围里成长起来,得以产生激情之爱。而文明过度的巴黎,只能催生出虚荣之爱。
第二,王斯秧老师指出,小说在于连这条主线之外,还并行进展着两个平行故事——拿破仑与瓦勒诺。拿破仑是于连的偶像,在这个困顿于现实之中的人身上注入浪漫主义的激情和英雄主义。而读者关注不多的瓦勒诺,则像是于连的分身。小说刻意让他和于连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一种现实的态度:于连这样的穷青年在教会势力猖獗的时代本该像瓦勒诺一样,低三下四、不择手段,他因为不肯遵循社会法则而失败。小说最后由瓦勒诺宣告于连的死刑判决,是现实的于连宣告了理想主义的于连的死亡。这三个故事的交错展现人物承受的外在与内在的力量。世道塑造人心,但不足以严格地解释人心:个人的才能、意愿与想象,与时代的难题、社会的变动时有冲突,心理现实和社会现实并不重合。

(拿破仑1812年远征俄国:博罗季诺战役,油画作者为俄国画家瓦西里·维希查甘(Vassili Verechtchaguine))
第三,王斯秧老师认为,小说通过语式与时态的运用,呈现出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复杂的关系。《红与黑》中运用了大量条件式过去时和虚拟式过去时,形成嫁接在小说主干之上的、指示故事发展诸多可能性的“平行故事”(para-stories)。小说由此突破了严格的线性叙事框架,“在虚构的内部创造出了虚构”,在文本内部拓展了更大的叙事空间,更是洞察人性、表达价值判断的工具。
王斯秧老师以司汤达为《红与黑》写的介绍文章的最后三段作结,指明司汤达在小说再现现实与认识现实方面所作出的创新。
“有件事会让读者吃惊。这部小说并不是小说。它所讲述的一切都于1826年真实发生在雷恩附近。主人公正是在这里去世,他朝前一个情人开了两枪,他曾是这家孩子的家庭教师,而这个情人写了一封信,妨碍了他和第二个情人、一个富家女成婚;德·司汤达先生什么都没有编造。
这本书敏锐,生动,充满趣味和感情。作者做到了以简单的笔法描绘温柔、单纯的爱情。
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也没有人细心描绘过19世纪前30年各种各样的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风俗。有一天,这部小说会像瓦尔特·司各特那样描绘古老的时代。”

讲座现场
田庆生老师随即对讲座进行了评议,主要就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追求现实的特点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一方面,这体现在书中对于社会风俗的精准刻画,从底层农民到大资产阶级均有所涉及,并对王斯秧老师强调副标题“1830年纪事”的观点表示赞成,指出这直接点明故事是讲述当代,要知道《红与黑》本身就是于1830年11月发表,这也就意味着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叙事时间几乎重合,可以说是一种可信度和真实性的极致,因此国内现行的张冠尧和郭宏安两个译本中省去了副标题的情况实际上是对重要细节的忽略;而另一方面,在本书上卷开头写到的“事实,无情的事实”这一题记也是对于客观记录现实的强调,但值得注意的是,维里埃这座城却又是司汤达虚构的,从虚构的背景中反映真实的故事,正如书中叙述者所提到的“小说是行走在大路上的一面镜子。它映入您眼帘的,时而是湛蓝的天空,时而却是路上的泥泞”,仿佛只有在小说中才可以达到真实,历史反而做不到。
田庆生老师还指出,《红与黑》现实主题下蕴含着作者对教会、上帝、贵族、金钱等强烈的批判意识,比如运用反衬的手法描写维利埃这座小城,自然景色优美,但却散发着锱铢必较的铜臭味。他还将《红与黑》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进行对比,指出现实主义作品中英雄主义的消解,人物形象的溃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