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十里八村——近代乡村社会与村民认知空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副教授冯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珊出席并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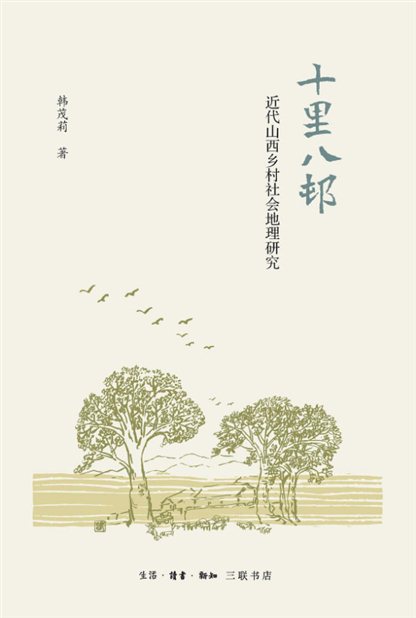
本次研读会围绕《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一书展开。韩茂莉教授首先说明了《十里八村》一书的研究视角。本书研究的是山西“乡村社会地理”,但从学术角度来看,其实更侧重于历史地理和地方历史研究,即用地方的历史依据和历史材料来研究地方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讨论的“社会地理”并非仅针对地理与空间问题,而是囊括了村民生产生活的所有空间,即从“田头”到“炕头”。其中心是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它把农民的一切活动都牢牢束缚于此。在中心之外,还有婚姻、祭祀、交易、行政等重要环节。这些活动都可被容纳在以自己所在村落为中心的空间范围中,这个范围即俗语中常说的“十里八村”。接下来,韩茂莉教授从乡村集市与水权两方面论述了“十里八村”这一空间范畴的形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教授
一、乡村集市与村民认知空间
农村生产生活中最基本的制约因素便是土地。因此,为了照顾农业生产,农民的所有活动都要在一日之内往返。对于山西农民来说,“一日之内往返”的距离正是“十里八村”,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很好地概括了村民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范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际间的商业活动,村民参与交易的距离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空间,也构成了村际间的婚姻圈与祭祀圈。在本次研读会中,韩茂莉教授从乡村集市来说明“十里八村”的形成与作用机制。
地形上来看,山西以高原为主,“定期市”一直是村民们主要的交易形式。定期市也称作“赶集”,是商业活动的较低阶段。但对于村民来说,它不仅是交换剩余产品的场所,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与娱乐场所。村民们的交易需求支撑起定期市的形成,而村民需求力度的大小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决定了定期市的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集市门槛值(即维持集市所需要的人口与购买力)低、集市密度大、间距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集市门槛值高、集市密度小、间距远。在四川,定期市的覆盖范围大约在一里半到四五里之间。而在山西,这一覆盖范围扩大至“十里八村”。
即便在同一地区,各个村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定期市的集期与客源区范围也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单日集与双日集在交易服务中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单双日集覆盖范围的交叉,两个集市构成同一个客源区,而这一组单双日集的交叉地区与另外一组单双日集的交叉地区则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客源区。于是,不同的村落就在客源区的大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共享空间。这个空间为村民们提供交易场所,也为将来的婚姻、结社提供了交往圈子。因此,定期市也往往成为村际间的社交中心。
以晋城县为例,无论是单日集还是双日集,县城所在的城关镇的商家数量都远超其他村镇,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级别较高的交易点。但即便如此,也只有距离城关镇较近的村民才会去这里交易,如果往返超出一日距离,村民们还是会选择去自己村落“十里八村”以内的集市。所以对于村民来说,集市没有“较高等级”与“较低等级”之分,仅以“十里八村”为限。像城关镇这样的大集市只对职业商人有意义,这些商人游走于各个集市之间,平衡不同地区的商品需求,他们的交易轨迹和活动范围与农民是完全不同的。总之,虽然村民进行的是较低层次的商业行为,他们的交易活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这样一个涵盖了“十里八村”的交易空间已可以囊括村民的全部基本生活。
二、水权与乡村社会
接下来,韩茂莉教授谈到了乡村社会的另一层面——“乡村精英”。历史上的大部分王朝都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官员”皆非国家任命,而从本地农民中挑选,且享有很大的话语权。但这些精英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韩茂莉教授从乡村水权找到了解决思路。
山西是一个半干旱地区,水权便是生存权,它的重要性甚至在政权之上。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山西百姓们修建了很多用来引水灌溉的渠道。这些渠道由村民集资修建,管理者自然也从村民中产生。从渠道的管理制度可以看到,山西农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了两套以水为本的空间管理体系——以水渠为中心的“地缘水权圈”和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
“地缘水权圈”以渠系为中心,涉及到上中下游利益分配的问题。试举一例,山西著名的民营渠道“通利渠”全长100多公里,流经三个区县。“自在使水,永不兴工”,其中上游地区灌溉不受亩数和时间限制,也无需负责渠道的日常养护。这是因为渠道的修建其实是将上游村落独有的水源由三个区县共享,中下游地区的村落若要换取上游水权自然要多付出成本。此外,通利渠还规定,作为渠道的最高管理者,渠长必须从下游村落选出。在整个灌溉过程中,下游处于利益最难保证的地方。从下游选出渠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一渠段的利益。并且,为了保护这一利益最薄弱地区,每年来水时都要先由下游灌溉。当然,在具体的灌溉过程中,整个秩序的维持还需渠长同村民间不断协调。在大旱年水源不够的情况下,已经定下来的秩序有可能被打破,这时,就会产生械斗。
械斗关联着第二个体系,也就是“血缘水权圈”。依附血缘关系的家族水权,来自渠长的权力。渠长承担了整个水渠的管理工作,也会获得一定的额外利益。比如,一个月固定的灌溉日一般为28天,若某个月超过28天,多出来的灌溉权则归渠长所有。渠长可多浇灌自己的田地,也可卖给其他农户。那么,作为享有特殊利益的“乡村精英”,渠长是如何选出的呢?一般来说,渠长由下游家道殷实、家风良好的大户人家轮流担任。这就涉及到了这一职位背后的预付资本,这个预付资本既包括祖先的传承积累,也包括修筑水渠时的投入,甚至还包括械斗中的人员牺牲。这些资本共同构成了乡村中的精英阶层。
总之,历史上的朝廷官员虽然只任命到县级,但乡间也一直保有自己的秩序。村民在保障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依靠利益形成了统一的保障圈。这个圈子在山西农村以水权为中心,它维系着十里八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最后,韩茂莉教授谈到,因缺乏实际经验,只能依据样本提供的历史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随后,唐晓峰教授发言。他认为,由于时代不同,自己经历的农村生活同本书中描写的农村生活有很大差别,但这一差别也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对照性视角。唐晓峰教授亲历的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自由交易和祭祀已基本消失。公社化时期,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生产单位也从一家一户变成了的生产队,劳动报酬以工分计算。韩茂莉教授提到的“剩余粮食”在合作化时期也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农民上交的粮食不是按“剩余”,而是按指标——这也是后来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唐晓峰教授还提到,当时他们去农村插队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是针对全国解放以后的新形势而言,要农民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另有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做了较大的牺牲。
公社化时代农村限制私人商品交换,自然也看不到“集市”,农民不能自己生产的用品大都可以在村里的合作社买到。关于商业问题,茂莉教授在书中提出传统社会的商业“二元”论,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与城镇工商业者的商业活动是不交融的,这个观点很重要。过去,我们在书本上读到,小生产者会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于是简单地以为农民也是小生产者,也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像山西这样的传统农民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
唐晓峰看到过的公社大队的灌溉管理,同韩茂莉所讲的情况有些相似,不过负责灌溉的人(相当于渠长)是从生产大队这个层面上选出来的,他们对水系渠道最为熟悉。灌溉的时候,“渠长”守在渠口,每个生产小队按顺序轮流计时灌溉,灌溉时间事先分配好。在一个灌溉地区,每个村子分多少水,指标也要统一规划。
公社时期,虽然是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在同一个生产队里也存在殷实户和艰苦户之分,这是各个家庭劳动力强弱不同造成的,也与个人头脑和勤奋程度的差异有关。但即使是殷实之家也达不到可以“预付资本”的程度,制度也不支持。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农村社会里一直都有一些所谓的“能人”。这些能人大致可分为两类:有头脑者和“灰旗杆子”。前者眼光长远,讲道理,在村中享有威望;后者聪明,但不讲常理,敢打敢闹,这类人在特殊时期会起作用。
关于“十里八村”这一核心论述,唐晓峰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过去,农民的活动范围的确非常小,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呆在“十里八村”的范围内,即使是公社化时期也差不多。因此,作为一个相当有限且封闭的空间,村子便成为了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名字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大家从小就熟悉,有个小名,可以用一辈子。只有准备走出农村的人(上学、当兵),才认真起个好听的名字。
唐晓峰教授最后说,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已完全不具备书中所描绘的那种乡村面貌了。而至于未来的农村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不过,韩茂莉教授研究的是中国传统农村最为基础的体制构建,是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维持发展和稳定的自主机制。要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必须懂这个机制。农村的现代变革,也是从这个机制出发的,成就也好,问题也好,都在参照它。正因为此,韩茂莉教授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冯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接下来,冯健副教授发言。他非常认同韩教授提出的“十里八村”,这一空间尺度在当今依然发挥着作用,并构成了我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半径”。冯健副教授例举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这一项目需要将宁夏某个农村的居民全部搬迁到城镇上。因耕作工作变得十分不便,很多农民并不乐意搬迁。可以看出,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无法摆脱“一日往返”的生活半径。此外,本书也让我们意识到,不应仅仅为了节约土地就“一刀切”地全部拆迁入楼,而应更多考虑农村一直以来的发展规律和空间布局。冯健副教授还提到加速乡村文明衰落的“空心化”问题和“剩男”问题,而韩教授所做的研究正是当前农村建设所欠缺的。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杭侃教授指出,考古学也是一门乡土学科。作为一个地理层面相对独立的单位,山西保存有很多古建筑。2001年,杭侃教授在去山西考古途中也注意到,村民们只熟悉本村的古庙。庙直接关系着村民的祭祀活动,建筑排布格局与上香群众出处均是考古工作者在研究中要考虑的问题。杭侃教授还就自己家乡(江苏南通农村)的情形与韩茂莉教授进行交流,希望她可进一步研究山西农村“十里八村”的空间规律能否运用于更广的江南农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
陈晓珊副研究员表示,从古代行政区划的改革中也可以看到出人的生活半径在发挥作用。古代划分区界一般遵循“百里为县”。“百里”是平原地区一天之能走完的路程,这个距离保证了人们若在早上从一个县出发,晚上可在另一个县下榻休息。但是,在非平原地区,“百里为县”不再适用。以书中的山西高原地区为例,可在一日之内往返的距离只有“十里八村”,因此,各朝各代的行政区划也要按照不同地区的“一日之程”不断调整。且人们的生活半径和工作半径虽有着固定的规律,但在具体条件下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蔬菜瓜果一般会种植在距城镇较近的地方,五谷杂粮则会种植在较远的地方,这是由农产品保鲜期不同决定的。即便在交通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时下流行的“江浙沪包邮”便是一例。
最后,韩茂莉教授和与谈老师就相关问题同听众作了进一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