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7日下午,文研院邀访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2022年春季学期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包伟民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要研究宋代的乡村社会》,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化系的陈文龙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研究唐宋官制史》。王明珂、杜华、欧树军、谷继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陆一、刘文飞、刘清华、罗鸿、赵丙祥、邓小南、杨弘博、韩笑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包伟民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自己选择专业方向“被选择”的经历,但他在“被选择”的过程中又保有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形成一种主动的取向,即关注基层、社会层面的历史而非传统的高层政治运作。包老师直言宋代基层社会的一个层面就是乡村与农民,相较于上层政治氛围,他对底层生活与基层运行更加关注。包老师用“沉默的大多数”来概括底层民众的特点,人们尽管总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人民在历史叙述中却是失语的,因为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历史记载。包老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使人进入宋代的基层社会与乡村世界。
接着包老师分享了自己研究宋史的两点具体感悟,第一点是社会科学进入历史学之后带来的“技术化”倾向,依据科学理性使用技术手段和理论对史料进行处理,却容易导致一种视野的遮蔽和区隔,反而可能错过历史真实甚至与历史真实存在距离。包老师以自己所做过的一个研究“元初遗民心态”为例来说明。此前学界对于“元初文人心态”研究的主导思路是通过统计宋末元初不同类型文人——即以身殉国、隐遁不仕与降元入仕等不同类型——的数量,来分析当时士人的心态,而包老师认为全局性的统计,不得不按既定的标准在特定层面利用史料,无法解读出历史文献的所有信息,他的研究便选取了四明地区的个案,讨论由宋入元儒士的心态,尤其重视分析那些入元后“不得仕”儒士之主观处世方式,发现从总体上看一般儒士在新朝治下顺应时势的姿态是较为明确的。四明儒士为了保持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新朝长期不开科举的背景之下,为了避免“委为乡人”,不得不采取与新朝合作的态度,这也体现了儒学入世求用的精神。此外,后世记载中,不与新朝合作的事例常被渲染放大,而对“合作”的记载,则多有避讳,也有可能造成今人认识的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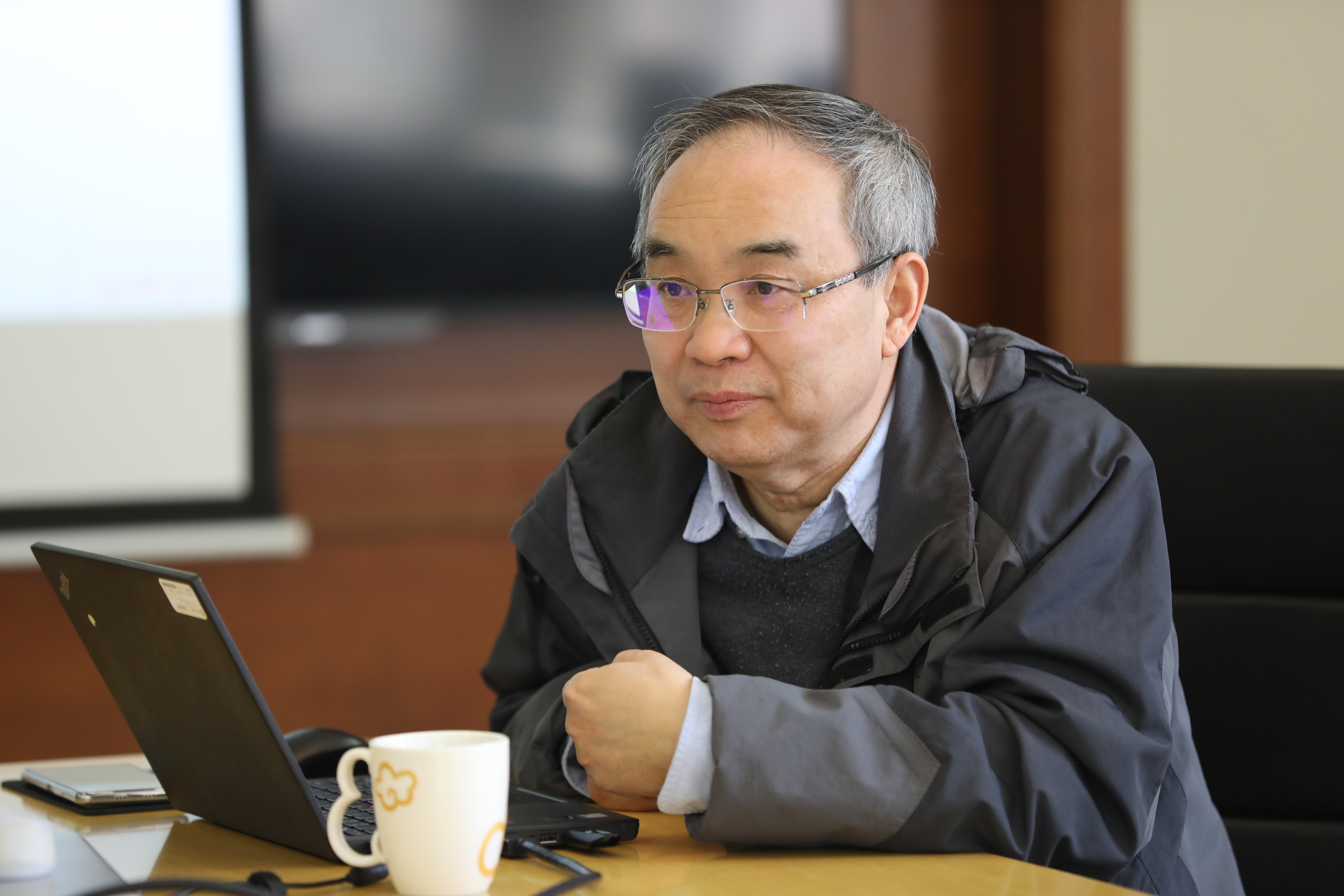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老师
第二点是如果我们的视野从上层的制度设计下移到具体的制度运行与基层运作层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内容。他以三个具体的例子为例来作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宋史研究中所看到的区域差异。从帝制晚期的财政史来作观察,可以发现,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地方财政管理各方面会受到中央的种种制约,北宋苏辙甚至称“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实际上,中央既难以保证地方财政的供赡,更无力督责各种法令真正的贯彻落实。至少就财政方面看来,大一统帝国的“全国一盘棋”并未形成,反倒呈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的双重特性。如果要从这种“无序”之中体会宋代国家财政中央集权的性质,恐怕主要就在于各地在轻重不均的赋税格局中保证了中央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征调一端。这样的境况,如果不从乡村(基层)来作观察,就难以发现。第二个例子是制度调适,包老师介绍了宋代的阶层性集权现象,每一个层级都可以看到它向下的集权。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地方政权的大多数资源看来也许被中央所控制,但大量法外实际操作现象的存在,使得每一级地方政权却又可以通过法外途径,将下一级的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第三个例子是视野下移之后所见到的民生百态。包老师在史料的阅读过程中发现,其实一般农民的日常生活距离货币是比较遥远的,农村的商业活动更多是直接以物易物的交换,而并不依赖货币这样的交换媒介。除缴纳赋税之外,农民一年到头使用货币的次数并不多。这样的现象似乎与我们所认知的宋代巨大的铸币量、商业交换活动的明显活跃、以及所谓“农商社会”的说法,出现矛盾。包老师因此指出,宋代铸造的大量铜币,其实主要是在官方财政领域内流通,国家要依赖货币以运作国家财政。商业贸易活跃的现象肯定存在,这就引申出新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景象,纳入整体的叙述当中。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感知到,当我们将视野下移或后移而不是只在表面,或许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陈文龙老师则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经历讲起,道出自己生活的家乡和社会环境为自己提供了对政府机构、官僚组织的第一印象。同时他也提到政治在中国弥漫式的影响力,这样的社会特点使得制度史研究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他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坦言学习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经历对自己在博士阶段研究中晚唐与北宋前期的官阶制度有很大帮助,既有阅读新材料的刺激,又获得了对前人研究的充分理解,还收获了一种历史的通贯意识,此外导师阎步克老师的分析框架也使他受益良多。同时,陈老师也介绍了陈寅恪、严耕望等史家对后辈学人研究宋史的吸引,并介绍了宋史的史料状况,大部头史料得到整理,新出史料整理也得到重视,做田野的观念与条件都具备,研究条件较此前大为改善,进入一个大有可为的时期。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化系陈文龙老师
陈老师具体介绍了自己研究宋代官制的状况。历来介绍宋代官制的第一句话是“宋代官制非常复杂”为什么是这样,学界不能满足于介绍现象,而要探明缘由。陈老师介绍并认同赵冬梅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化分为渐变和改革两种。改革型制度,伴随重要政治事件,一般会出台整齐划一的制度条文,关注者会更多。渐变积累型制度则在一个长时段平缓变动,容易被忽视。改革型制度在短期内必然出现混乱状况;渐变积累型制度则经过长期调整,一般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大多没有系统文字记载,容易被贴上“混乱”的标签,实际上并不混乱而是有迹可循。关于官制的整体结构,陈老师认为北宋前期等级制度研究,不能满足于解释某一项具体等级,而要将等级制度的整体结构揭示出来,进而把所有等级制度都解释清楚。他用职官分类、内职与王朝权力运作对此进行了具体说明。职官分类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王朝的权力分配。内职是皇帝重点依靠的群体,和皇帝关系亲密。担任者为潜邸随龙人员、勋贵后代。军职则具有控制与依靠双重性质。防止其他势力干涉军职,也要防止军职操控行政权力。宋朝建立后,外朝宰相可以不换,枢密院和三司等内职机构必须任用太祖亲信。军职则经过“杯酒释兵权”,受到重点掌控。北宋前期的文武问题,主要是内与外的问题。如狄青是军职出身,按惯例就是不能任枢密使副,而内职中的武选官是可以出任枢密使副的。北宋前期的“崇文抑武”,如果不讨论内与外,不区分军职和武选官,就是一个伪问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内职在真宗时期分化,三司、学士成为文臣,枢密、宣徽、诸司使也外官化,与外朝文武官逐渐趋同,和皇帝关系不再亲密。宋仁宗时期成为宋代相对最为开放的时期便和此时权力结构的变化有关。陈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今后深入的方向,认为单独把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拿出来研究不够全面,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完整的研究应包括中晚唐五代时期,以及宋元丰改制以后。另外,从地域上说,同一时期的辽、西夏、金,他们的官制如何从唐制演变而来,和宋代官制又如何互动,都是值得细致研究的课题。如元丰改制前后的官制就显示出官制的连续性。比如赠官,北宋前期赠官集中赠职事本官阶。元丰改制后,普遍可以赠寄禄官、职事官和职名。这是因为北宋前期更有秩序、元丰改制后更混乱吗?实际上并不是。元丰后寄禄官、职事官、职名都有官品,赠官必须得有官品,这与等级待遇有关。比如三品立碑、五品立碣,唐代的规定宋代一直执行很严格,体现出官制在改制之后的连续。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本次邀访学者交流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
撰稿:赵洲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