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环球同此凉热”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对外来者,以及“内部的陌生人“的警惕、歧视,正在撕裂着人类共同体。在全球化终结的担忧中,我们也发现,恰恰因为不同大陆的人们都在与病毒苦苦缠斗,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在此特殊时期,文研院依托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呈现他们在地的观察与思考,提供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远隔重洋,希望他们的书写,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无穷的远方与无穷的人们。
本期海外来信,推送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戴燕教授发自东京的文章《大疫之下的东京读书记》。因日本疫情发展迅速,原定寒假过后回国的戴燕老师也滞留东京,一册由竹内弘行翻译注解的《十八史略》意外成为戴老师的手边书。《十八史略》是元代曾先之为童子训蒙所编的一本通俗史书,叙述从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此书不为中国史家所重,倒是东传至日本后流传甚广,尤其在明治时代,被当作学童的教科书,笺注者众多。戴燕老师的这篇小文,就是在紧急事态中对竹内弘行译注本何以流行的一种解读。
戴燕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近代学术史、日本汉学。著有《玄意幽远》,《文学史的权利》,《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曾任职于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文研讲座“主讲人之一。感谢戴老师赐稿。
大疫之下的东京读书记
戴 燕

戴燕老师在文研讲座第56期“中古文学史的再脉络化”现场
一
原以为过完寒假就回学校上课,没想到新冠肺炎来势汹汹,且绵延不退,人只能被迫滞留在东京。到了4月上旬,东京等七都府县进入紧急事态,东京大学忽然关闭,最要命的是东大图书馆也停止了借阅,周围书店又陆续关张,客居异乡的我,于是,手里面只剩下一本书,就是《十八史略》。
当初借这本书,是因为过去读一些明治时代学者的东西,曾留下过一个印象,就是在那珂通世《中国(支那)通史》出版以前,这是他们提到最多的一本中国史,就像《论语》一样,几乎是必读的教科书。这让我在心中始终有一个悬念,很想知道,在中国并没有太大名气的这么一本书,它到底是怎样讲元代以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使它在大约16世纪传入日本以后,一直到近代,都为日本人所重视?
在图书馆借到的这一本,是由竹内弘行翻译、注释及解说的讲谈社学术文库本(2008)。借时没有细看,等拿回来一翻,才知道它并不是曾先之所撰《十八史略》的全本,只是一个节选本,不过,由于竹内的译注和解说占篇幅较多,整本书也有了厚厚的五百多页。然而,大疫当前,读书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究,何况这还是一个纸本,一卷在手,总比刷手机上网,看了更让人心安,不如随遇而安、将计就计。当然,这样的结果便是,原来我要读的是曾先之,现在变成了竹内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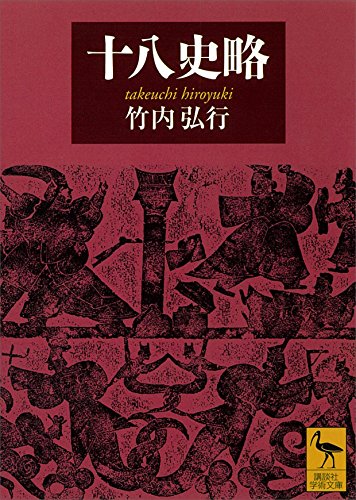
《十八史略》竹内弘行译(2008)
二
但必须要说的是,竹内做的这个选注本,其实颇见功力。
他的训读和翻译,不在我的关心范围,我要说的,首先是他的注释,做得相当到位。
虽然是针对一个通俗读本,可他有的地方注得很专业,比如,书中一开头写道:“天皇氏以木德为王,岁起摄提。”他便就“木德”与五行的关系、五行与政治的关系,做了一番解释,并说明“摄提格”是太岁纪年,怎样就等于后世的甲寅。又比如,书中写到春秋时的吴,“十九世至寿梦,始称王”,他拈出“称王”一语解释说,本来周王授其子爵,应该叫“吴子”,可是他自称为王,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出于蛮人不肯臣服于周的习惯。像这些地方,他都是不限于字面,结合各种文化史知识,而讲得比较深。当然,也有的地方,他注得平易近人,比如,书中引《麦秀之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他也摘出渐渐、油油,解释前者是形容麦子一点点拔高,后者是形容禾黍已经长大。
对书中提到的人物、地名、职官、制度、事件等,他都是这样巨细无遗地给以注解,注文写得清楚又浅白,即便是现代的日本普通读者,我想也能通过这样的注释,克服阅读中国古书的障碍。而就是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到《十八史略》为什么会在日本长盛不衰,有它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竹内弘行教授大概也是在有意识地保持这一阅读传统。
但是,竹内做得最精彩的部分,还不是注释,而是解说。他的解说,实际包含着评论。
比如,在太古这一章的解说中,他就指出: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没有神话,只有系统的历史叙述,的确,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历史的国家,留下了海量史书,就连古代神话,也穿上了历史的服装,从《十八史略》中就可以看到,从天皇、地皇、人皇,到伏羲、神农、轩辕,他们都是被按照时间顺序整编过的,都已经历史化了,以今日的考古学与严格的实证主义史学立场去看,这样的叙述没有一点价值,可是,如果换成古代神话的历史叙述这个视角,便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很深的意味。
又比如,在三国这一章的解说中,他指出:古代中国是以天命所授为天子的,史家也要根据这一点来判断王朝的正统性,并以之为历史书写的轴心,陈寿的《三国志》因此是按照汉-魏-晋的系谱来写的,到了曾先之写《十八史略》,从现存的二卷本可以看到,他本来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经后人修改过的七卷本,变成了以蜀为中心,而从学术上看,这是一种倒退。
还有一例,是在最后一章,对南宋末陆秀夫之战的解说。他认为《十八史略》写到陆秀夫在流亡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这本是有褒有贬,不过,《大学章句》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之一,也是宋代新儒家的基本教义,即后来所说“朱子学”,而视忠诚、贞节等个人品质为一种普遍道德,也就是“天理”,最后归结为绝对服从的尊王、忠君,这一“朱子学”理论,对东洋的精神世界,却曾经有过极大的影响,自然也表现在陆秀夫、文天祥这些人身上,他们都是“节义之士”。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写到过南宋的灭亡,在他看来,南宋毫无招架之力,可他就是没能看到这一点,而这也正是《十八史略》等史书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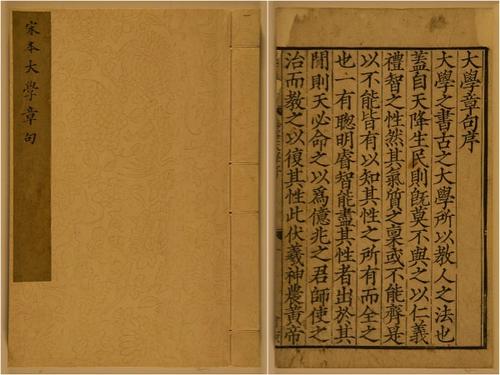
宋本大学章句
三
竹内弘行的精彩解说比比皆是,这里只是举出几个例子。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认为他讲得精彩?
首先,他就《十八史略》做解说,当然要依靠它来讲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给传说中的历史“去魅”,而这正是现代史家的本分,即使是在一个通俗史书的讲解中,他也照样本着严肃的、批评的学者态度。在日本,要做到这一点,可能还不是太难,因为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学者都是这个态度,只是我时常想到我们自己的环境,便觉得这是弥足珍贵。
其次,他对于传统的历史叙述,一面怀有警惕,可是另一面,也有相当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能够将它们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认识、去评价,显示他虽然坚持科学史学的立场,却并不固执,对于历史特别是历史中的人,依然能葆有温情和关怀。
最后,他还能从更广的“东洋史”角度,发掘《十八史略》这一类传统中国史书的意义,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还借以稍稍“批判”了一下西方中心史观,而这一点,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唯有日本学者能够做到,因为所谓“东洋史”的视角,虽然不涉及日本史,可是如果不懂传统的日本汉学,那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当然,我自己是读他的书而有所得,起码原来心中的悬念、疑问,在这里涣然冰释。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这一行的专家,事实上,并不了解在我看来如此精彩的解说和评论,有多少已经属于学界共识,又有多少是竹内教授个人的意见。好在我不是要写一篇认真的专业性书评,我只是觉得一个通俗史书的选本,可以注释得这么有耐心,而又解说得这么高质量,很是让人佩服。尤其是在日本现在扩大到全国进入紧急事态,政府一再呼吁“不要不急外出自肃”,而人们的心情却是在忍耐和焦虑中摇摆,漫漫长日不知何时结束,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时刻,能够读到既谈不上经典又和时尚话题绝不沾边的这么一本书,对我来说,本来也是“不(重)要不急(需)”,但读过之后竟很有收获的这么一本书,无论如何,都算得上幸运。
2020年4月20日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