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环球同此凉热”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对外来者,以及“内部的陌生人“的警惕、歧视,正在撕裂着人类共同体。在全球化终结的担忧中,我们也发现,恰恰因为不同大陆的人们都在与病毒苦苦缠斗,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在此特殊时期,文研院依托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呈现他们在地的观察与思考,提供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远隔重洋,希望他们的书写,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无穷的远方与无穷的人们。
今天推送的“海外来信”,来自一位特殊的作者,巴西著名文学研究学者、任教于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Francisco Foot Hardman)教授。自2019年8月起,哈德曼教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担任客座教授,在燕园开展教学工作。随着新冠病毒防控形势的升级,他体验了中国强有力管控措施的行之有效,也为万里之外巴西国内疫情的蔓延而担忧。受巴西媒体的邀请,哈德曼以日记形式记录下北京的生活点滴与感悟,表现出一位巴西知识分子对人类团结抗疫的呼吁。我们征得教授同意,特此摘译其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一位巴西教授如何看待中国的防疫经验?从巴西的知识传统来认识这次空前的危机,又有哪些思想资源?这篇日记选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文章原文为葡萄牙语,由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博雅博士后马琳翻译成中文,闵雪飞老师、樊星老师为促成该文章的发表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们对上述人员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巴西人在北京
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
翻译:马琳

哈德曼教授在北大葡语专业课堂上
写在前面:
中国朋友们将会读到的这些文字是我在巴西已刊发的随笔节选。我从1月31日起撰写文章记录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新冠病毒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几周后,成为了席卷全球的大流行。因为中国的初步防控措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也因为此前我在北京给旗士电视台(TV-Bandeirante)录制过视频,《圣保罗页报》邀我写下第一篇文章。其他文章在我所任教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校报上发表,每周一篇。此外,新闻网站“Carta Campinas”(坎皮纳斯来信)也发布了这些文章。在此我想感谢我在北大的同事们,樊星老师,闵雪飞老师,胡旭东老师,郭洁老师和范晔老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鼓励和热情的接待。我还要感谢我在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可爱的学生们,感谢他们的坚持与友谊。
2月14日 世上最隐秘的咖啡屋:
北京在小雨中迎来黎明。天气还要再冷一段时间,但最近气温已有所回升。这雨很好,净化空气,完全不同于在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降下的造成严重灾难的暴雨。这些日子,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降了,虽说比前几年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要好很多,但依然很差,现在,为了降低传染风险,人们不得不待在家里,空气益发差劲。海淀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如果你了解北京这座特大城市,了解这一个区,或是能够想象人口比圣保罗多一倍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尽管北京面积远大于圣保罗),便会觉得这里目前就如同一座鬼城,一片寂静,不同以往,简直是超现实。

北京地铁空无一人的车厢
在这能做什么?我用音频录课,通过微信和邮件把课程材料发给学生们。我和班长沟通,他的作用很重要,完全不是装饰性的。同学们都急着想回北京,想回到无比美丽的校园。这里有他们的宿舍,供本科生和研究生从入学住到毕业。目前学校已经停课,尚不清楚何时能返校。一位家在广东省吴川市的同学向我提问,关于格拉西里亚诺·哈莫斯的小说《干涸的生命》,我接下来要讲这本书,她已经开始自学。她和其他同学都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们多么亲切!多么友爱!多么体贴啊!他们和巴西学生肯定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相互学到丰富的知识。幸运的是,这种机会已经安排好了!
另一位同学,家在浙江杭州。她正在翻译米亚·科托的小说,随时会向我提问。还有三位同学,分别来自郑州、深圳和福州,他们正一如既往地努力,专注完成毕业论文。这三人研究的作家并不相同,分别是鲁本·丰塞卡,吉马良斯·罗萨和米亚·科托,但他们研究的中心主题都是“抛弃”:《八月》中在1954年悲剧般的八月里被抛弃的巴西;《河的第三岸》中遥不可及的父亲对家庭的抛弃;《一条叫做时间的河,一座叫做大地的房子》中被城市和历史抛弃的小岛。
如今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抛弃”,被抛弃的是最穷的人、病人、食不果腹之人、战争难民和资本主义文明自杀式发展导致的生态灾难所造成的难民。此时,一条来自学生的信息令我感动不已。这位同学正在她美丽的家乡武汉过着隔离生活。我之前给她发去一个视频,是由葡萄牙的学生制作的,给中国人民加油鼓气,表达国际团结。她回复了我:“老师,谢谢您给我发来这个充满热情的视频!这段时间,我的城市见证了灾难也见证了爱。来自各方的支持和鼓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您不用为我担心,我和家人都很安全,也很健康。非常期待能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和您在校园里重逢!”
如果说有一种文明经历过战争、半殖民地化和饥荒,在数千年中发展出了等待的智慧,那就是中国。因此,目前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等待。在被抛弃的风景中,我们可以探访马路、树木、未名湖、矗立在冷清街道上的过街天桥、小广场、小路、充满活力的胡同,胡同总是混乱的,带着一种破败的古典主义之美,这是最好的路,有时甚至从表面上都看不出有路。
在三里屯这个平时人群熙熙攘攘、如今空空荡荡的地方,有一位街头理发师,可不是塞维利亚理发师,但这位理发师在这个没有行人的周日独自一人坚持开工:女士剪发12雷,男士9雷(雷亚尔,巴西货币,1雷亚尔约等于1.3人民币)。谁准备好了?只有两位顾客在等,就站在路上。说实话我有些犹豫,因为这位剪刀大师没有遵守戴口罩这一安全规定。

三里屯的街头理发师
2月21日 通行证和其他忧虑:
我第二次被拦在了小区门外,目前只有一扇门可以通行。出入规则相比之前更加严格,这虽然会引起不便,但对防控疫情确实有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人们减少出行使得目前确诊人数没有超过400人,确定死亡仅4例,对于拥有两千四百万人口的北京来说,这一数据相对而言并不算多。我所在的海淀区目前官方确诊病例是61例。他们之中有人是我的邻居吗?那几位逝者里有人曾住在我附近吗?我隐隐有些担心。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总会有相似的忧虑。好在太阳出来了,鸟儿回来了,气温也升高了,“行凶作恶”的新冠病毒先生将会逐渐失势。
然而,巴西狂欢节打消了我的疑神疑鬼。在狂欢节的游行队伍里,尤其是在里约,“皇冠+病毒”装扮深受大众欢迎,无论男女。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是幽默讽刺。笑总归比哭好,尤其是在总有令人不悦的消息从巴西利亚传来的时候,现在的说法是:今天似乎比昨天更糟糕。或者借用路易斯·费尔南多·维利希莫(Luis FernandoVeríssimo)在报刊专栏中写到的一句睿智的话:威胁我们(巴西)的不是冠状病毒,而是一种更加悲剧、更加无法医治的病——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逐渐变得靠不住。

2月21日,2020年巴西狂欢节在里约热内卢开幕。图为以新冠病毒为主要元素的装扮。
我们都知道,无论某些记者、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如何努力用假象迷惑大众,人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就比如我现在的情况:如果不想睡马路被冻死,就得想办法进家门,为此就需要到小区管理部门重新报备我作为暂住访客的身份,那里离我的住处有50米远,与我目前所在的大门相距200米。我住的小区原本有三个门可以进出,以前行人、自行车、三轮车混在一起十分热闹,唯独汽车夹在其中不太和谐。小区面积约为十万平方米,有四条南北向的路、四条东西向的路,基本构成一个四边形。如今在唯一开着的大门前,有一块电子屏,上面显示着醒目的标语:万众一心,坚定信心,科学防控,战胜疫情。
两位向来十分友善的小区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有我的个人信息,这就是我在防疫期间的通行证,我感到一丝喜悦。护照在这时并不管用,访问学者证也不行,它们也都旧了,现在这张通行证上写有我的名字和住址,背面还有温馨提示:“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勤锻炼、不扎堆、讲礼仪、稳心态”。据我的同事樊星解释,最后三个字是不要过度担心的意思。“是指对病毒的担心还是对所有的事?”我问她。“卡上没有细说。”她回答,“但我觉得说的是不要过分担心病毒。”我明白了,仔细想来,这些提示我基本上都做到了。我觉得它们有一定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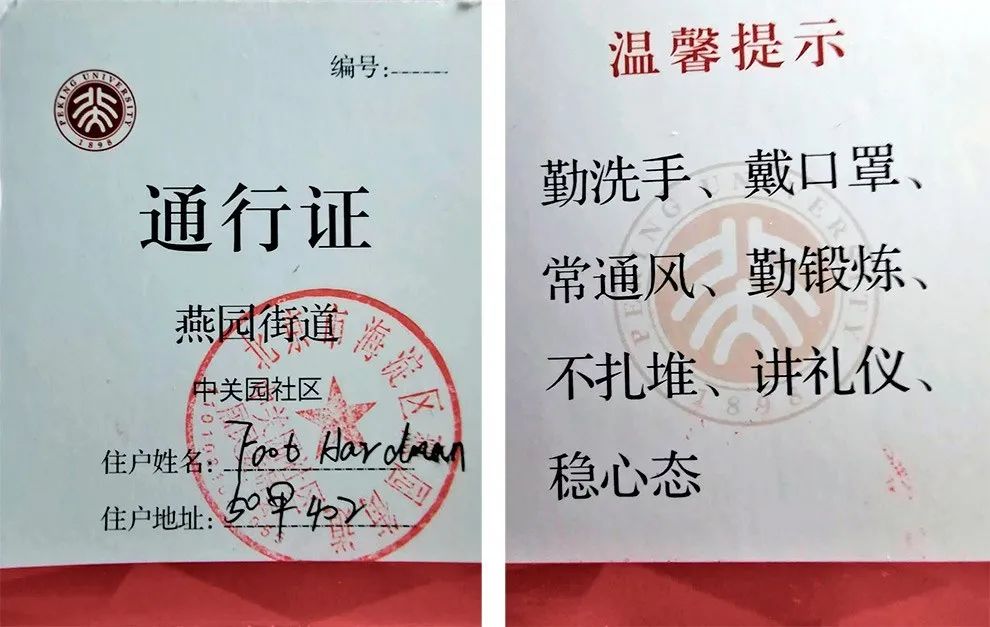
哈德曼教授的通行证
但如何才能够不为那些比我们更加痛苦的人担心呢?我想到在我亲爱的巴西还有很多食不果腹的人,很多失业者。我想到那些经历了政治暴力和刑事暴力的受害者,如今这两种暴力正危险地相互趋近。我想起玛里艾丽·弗兰科(Marielle Franco*)和那些下令将她刺杀的幕后黑手。我想起那些因为叙利亚战争而受伤、死去或惊恐地逃难的孩子们。这场战争已持续近十年,它标着一些大国虚伪的无能。
说到底,我们应该寻求一种团结的力量,它能将我们连在一起,拯救我们。我们可以且应该靠这种团结去拯救所有人共同的家园——地球,所有警示信号都已亮起来,剧烈闪烁着,发出刺耳的响声,我们正处在环境告急的时代。人类不只在为平等和多样性进行抗争,也应该去阻止——如果还来得及——那些对任何生命形式做出摧残的人继续支配世界命运。
这张通行证现在足以让我先平静下来。我确信我们并不孤单。
*玛里艾丽·弗兰科 (Marielle Franco, 1979-2018)是巴西政治家与人权活动家,长期关注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致力于保护贫民区居民权力。她于2016年当选里约热内卢市政议员,2017年上任,2018年遭到枪杀身亡。
2月28日 面包,白水和知识:我的心是共同体:
在这些天的半幽居生活中,我出门基本只去一个地方:目前仍勇敢开着的一个食堂。它位于小区的一角,离我住处有400米远。在这几个星期里,到食堂吃饭的人非常少,于是我慢慢成了厨师和工作人员眼里的熟客。查体温和居民通行证的保安也都记住了我。(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北京大学以前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那位平时一直闲不下来、很有节奏地收餐盘的女士如今掌管着食堂大门的钥匙。我和她几乎算是朋友了。
我在他们的帮助下点爱吃的素菜。这些菜很够味,搭配得极好,我对它们的喜爱仍在与日俱增。有土豆搭配茄子的地三鲜,有酸甜口味的鸡蛋炒西红柿,这道可谓是必点菜肴,还有西蓝花、菠菜和熟到正好程度的豆芽。现在已经用不着我说要米饭。后厨早就把饭从巨大的饭锅里盛出来,取小份放在餐盘中间的位置,等待着配菜与之会合。就这么简单,不需要过多交流,可以保护自己。全国对抗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北京目前似乎取得了大范围的胜利。负责卖饮料、汤、红薯和面食(馒头、包子、馅饼等)的女士总想让我再多买点什么,即便我每次都拒绝。
我知道在这我不会缺少每天所需的食物。饮用水也不缺,在离住处50米远的地方就有自助取水机,我最珍贵的一张卡便是水卡,6.5升好水花费相当于80分雷亚尔。
有水有饭,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上课了,现在都是远程教学,我的学生们分散在十二个省市,其中有些很遥远。你们相信巧合吗?我更喜欢“时空交汇”的说法,以避免用“等时性”这样的术语。也许我们正生活在同步的时空之中。我亲爱的巴西正经受着种种野蛮行为,这野蛮是由上到下的,面对此种情况,我们应该由下而上重新开始,从二十世纪伯南布哥(巴西地名)的两位思想家说起,没有任何一种野蛮能够将他们的遗迹抹去。约绪·德·卡斯特罗的(Josué de Castro)的杰作《饥饿地理》(1946)揭示的是最简单也最基本的问题,可悲的是,今天这些问题依旧存在。保罗·弗莱里(Paulo Freire)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1968)是被全世界人文领域学者广泛引用的佳作。弗莱里是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和平教育奖,是巴西教育的捍卫者,任何反教育的无能之人都无法将其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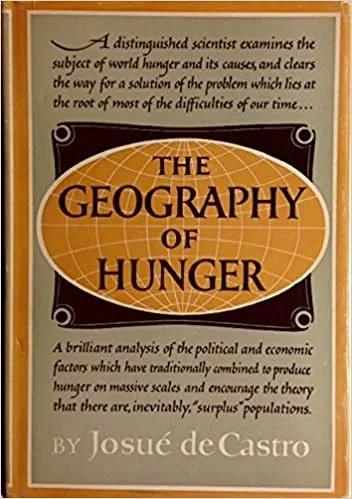
约绪·德·卡斯特罗的《饥饿地理》(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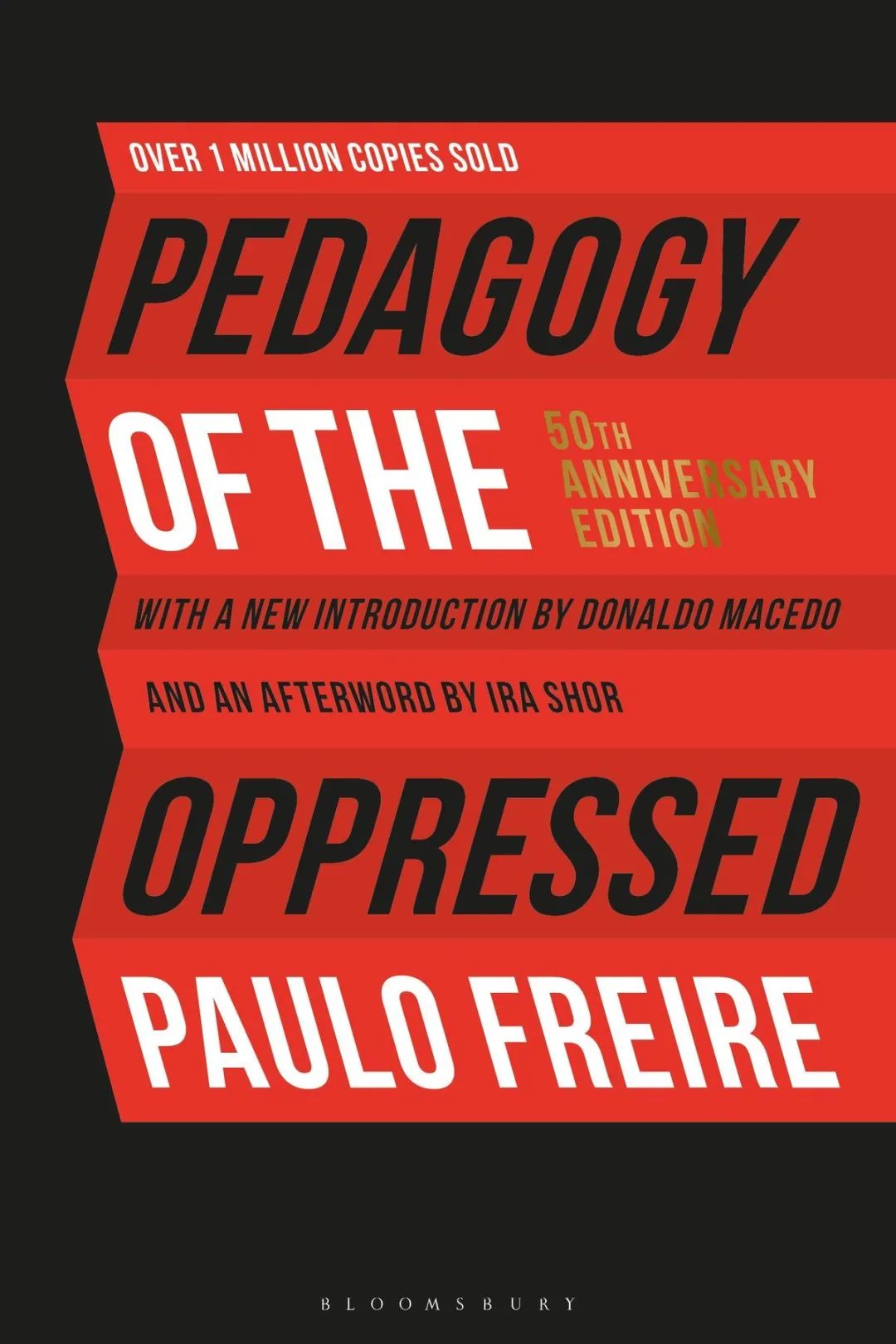
保罗·弗莱里《被压迫者教育学》(1968)
3月13日 加油,中国!
西方开始了动荡,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世界金融市场犹如被放到撒哈拉沙漠中的冰棍,迅速融化了。在这个时候,中国正逐渐从新年的冬眠中苏醒,准备好迎接下一轮战斗。冬眠只是表象,我们都知道,熊类中唯一不需要冬眠的就是熊猫。
北京的街上隐约能看到一些人,和之前繁忙的日常相比,人并不算多。China在中文里是“中国”,北京是这个“中心的国家”既古老又新潮的首都。
当疫情只在中国范围内的时候,从西方传来了一些声音,或悲观或不满,还有一些属于种族歧视,他们在西方笑着看亚洲巨龙跌倒。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但中国人并不习惯笑别人的不幸,因为他们知道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只有那些不作为的政府,比如正让巴西人民受罪的巴西政府,才会疯狂到忽视疫情的严重性,明知道这疫情仅在中国就已经夺去了3000条生命。如果说全球化在影响国际市场兴衰之外还能有其他作用,那就应该是帮我们形成一种全球生态意识,它以社会生态为原则,依靠所有人的共同参与。
通过这次的事,我们能明白,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学会了有耐心,学会了等待。虽然中国早已开放了市场,发展市场经济,但仍以人民集体和国际团结为主导理念。有霸权利益在影响吗?毋庸置疑。但中国在如今的国际版图中是国际和平的担保人,为不同半球、大洲和国家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北京大学食堂中张贴的宣传海报,远看为爱心,近看是口罩
3月20日 另一种全球化
克莱纳克和米尔顿·桑托斯有话要说,世界在快速运转。两个月前,疫情在中国全国范围内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大面积扩张。那时我们似乎陷入了不被中国之外的世界所理解的境地。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访客来说,仿佛是经历着彻底的流放。
但是现在,方向调转过来。在此我向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校长及整个管理部门表示问候,他们面对疫情的严重性勇敢地快速作出决断。我还要向教职工和学生们——尤其是语言研究学院——表达我的支持,他们正处在困惑与痛苦之中。我能确定的是,这一切终将会过去。照顾好自己是必要的,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人。
自十二月以来,疫情中心湖北省武汉市首次出现了零感染的情况。昨天中国的新增病例为34例,其中21例在北京。所有这些新增病例均为国外输入病例,主要来自欧洲。欧洲成了新的疫情中心,意大利成为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已确认那里出现了大规模疫情。
不能去我们最想去的地方,这确实很糟糕。也不能去原本为了工作、学习或情感维系而应该去的地方。我们的城市被飞速发展和数字化普及所吞噬。所有城市似乎都有只能下达一个命令的按钮:加速,加速,加速;消费,消费,消费。当如同战争一般的危险迫近,“停止”键造成了困惑、愤怒和恐惧。
我们需要再次向传统的人民学习生存之道,学习重新迎接四季交替的希望。但全世界确实正经历着社会生态性的崩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等待也许只能迎来一场美梦,一场世界末日前的“城市美梦”。反乌托邦这个词直到近年来都仅被用于哲学或科学层面,如今我逐渐明白,这个词将会在人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慢慢占有一席之地。不论是哪一方面。
乌托邦辩证地意味着对斗争的新的激励,这是一种为争取一个可供全体人类居住的世界而展开的斗争,所谓全体人类,是指朝向一种人类的新概念开放,将类人(quase-humanos*)包纳其中的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尚未建立,也尚未将自身认同于此。我在这里改写了艾奥顿·克雷纳克(Ailton Krenak)的一些旨在推迟世界末日到来的思考,见于他去年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但思想十分伟大的书中,我在北京大学和我的学生们一起阅读了这本书。它正好启发我们在2019年末到2020年初之际对世界进行反思。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类人”是巴西当代印第安领袖艾奥顿·克莱纳克(Ailton Krenak)发明的术语,用以指代印第安人、被奴役者等并不全面享受人类权益的弱势群体。在克莱纳克看来,这些群体目前并未被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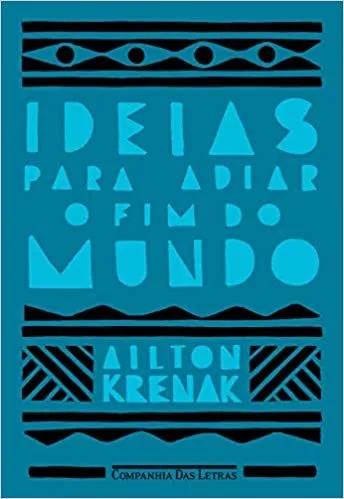
艾尔顿·克雷纳克《推迟世界末日的思想》(2019)
如今,远程教学已进行了六周,我们开始阅读米尔顿·桑托斯(Milton Santos)的作品。他是一位伟大的巴西黑人知识分子,来自巴伊亚州,是一位世界公民。桑托斯离开我们的前一年,时值世纪之交,他基本上预言出了接下来这不幸的20年里人类所遇到的困境,并说得十分详尽。这位始终心系城市土地规划的城市地理学家,再次以乌托邦、以人类仍需为捍卫人性而做出努力为主线,书写了这部作品。我说的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另一种全球化》(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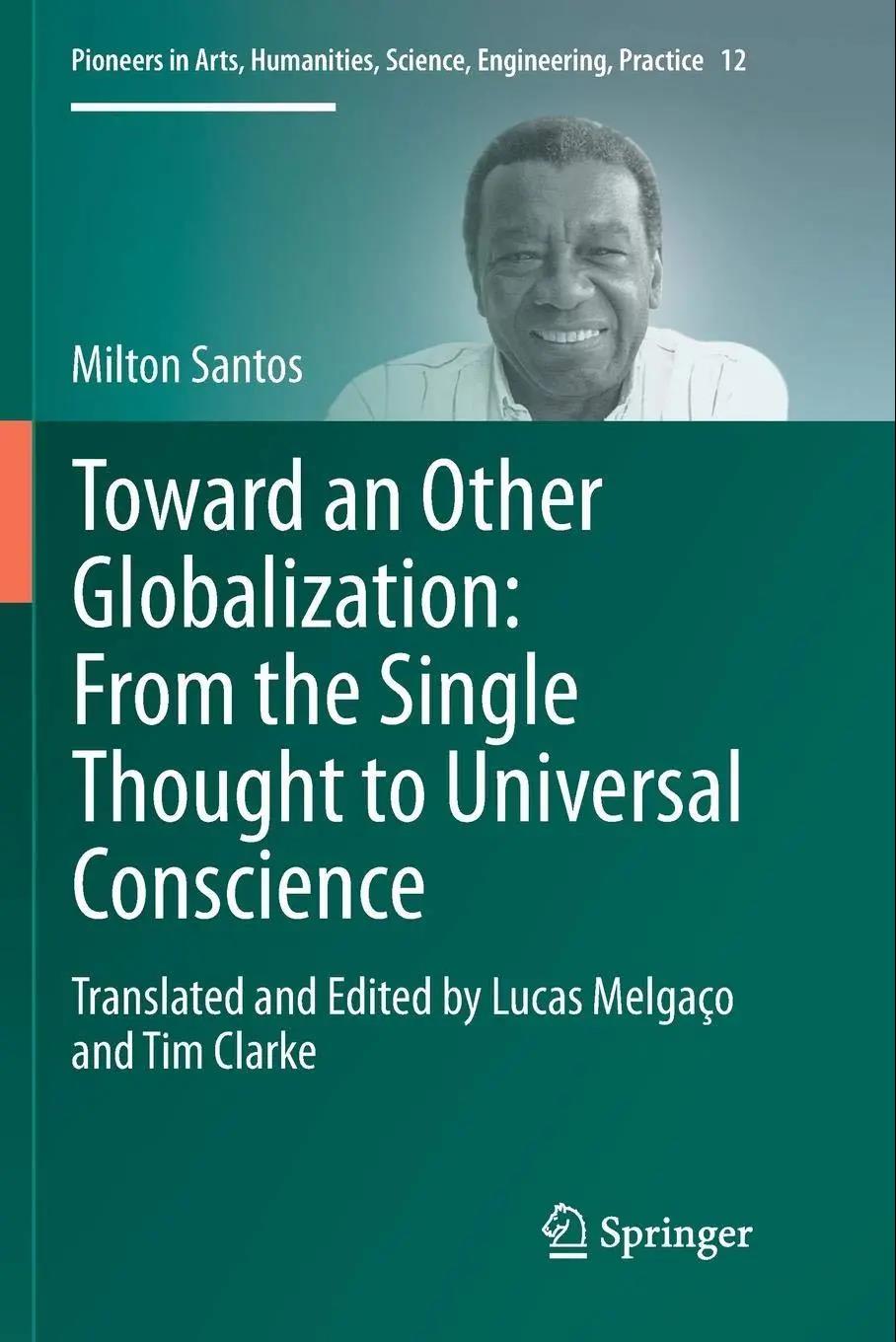
米尔顿·桑托斯《另一种全球化》(2000)
面对着虚拟货币的大肆流通和全球的无界化发展,我们必须回头看看,看向我们的本源所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如果人类还有点运气的话,那里将会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学者介绍:
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教授1952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1974年起先后于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和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学习,分别获得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本科学位,以及政治科学的研究生学位,并在1986年于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哈德曼现作为资深教授,任教于巴西排名第一的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院,同时也是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巴西文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并广泛涉猎于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自2019年8月起,哈德曼教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担任客座教授。在此之前,哈德曼教授已经与北大西葡语系进行了近十年的紧密合作,学术联系从未间断。2011年,北大葡语专业第一批本科毕业生赴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攻读学位,与哈德曼教授结识。2013年,哈德曼教授顺访北京,与葡语专业负责人闵雪飞老师作进一步交流。2015年,哈德曼教授在北大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活动,并最终促成艾青诗集《南美洲的旅行》在巴西出版。2015年及2017年,哈德曼教授在西葡语系巴西文化中心的邀请下,在北大举办了两场巴西文学的讲座。依靠多年的交往经验,哈德曼教授对中国及北大抱有深切的好感与信任,这是他选择在疫情期间留在北京并作出记录的首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