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燕京学派专题中,我们回顾了瞿同祖先生法制史研究的诸多面向,也介绍了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分三期推出“杨庆堃专题”。本期推送的是费孝通纪念杨庆堃的文章《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以及他早年和杨庆堃的通信,另外还有杨庆堃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所写的一篇调查记录《热河杂忆》。
杨庆堃于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1932年取得社会学学士学位,接着他继续在本校攻读硕士学位,于1934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杨庆堃与费孝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有三年时间同住一个宿舍,并且志同道合,立志“要靠走社会学这条路,在知识积累的上边来为人类作出贡献”。从1931年开始,杨庆堃就在山东省邹平县进行“农村社会观察”,受到帕克的“社区”研究方法影响之后,他系统地对当地的市集进行了调查,写成了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而“社区”这个概念的译法,也是他在参与《帕克社会学论文集》的翻译过程中,与费孝通一同确定的。本期推送的费孝通纪念杨庆堃的文章,不仅回顾了他们的学生时代,而且还着重赞扬了杨庆堃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杨庆堃和费孝通的通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谦谦君子之风。虽然杨先生中年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境外,但是他一直挂念着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恢复,并对此充满信心。通过阅读杨庆堃早年这篇忧国忧民的调查记录,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拳拳赤子之心。
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
文 | 费孝通
杨庆堃先生,很多人称呼他Dr.C.K.Yang,我也一直叫他C.K.。C.K.和我早在1930年相识。当时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他已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念了两年书了。我同C.K.是三年同住在一个房间的室友。我们一起搞社会学。当时我们志同道合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一个共识,一个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我们的一生,要用我们的大脑,来积累我们的一点知识,来贡献于我们自己人类,特别是要贡献给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两个人在这一点上有共识。那么我们学甚么知识呢?大家一同来学社会学。我们要靠走社会学这条道路,在知识积累的上边来为人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所以,我们是从1930年开始就决定要为社会,为社会学作出我们的努力。1933年我们听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派克(Robert Park)教授的课。我同杨先生一起跟Robert Park教授学了半年。他“不是教我们念书的,而是教我们写书的”,这是Park的话。怎么样写呢?他说,你们从生态学(Ecology)里面去找资料,认识人类生活,生态学是我们社会学的基础。教授这一个指导,给了我们灵感,我们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直接去了解中国社会,作科学的调查。

燕京大学圣哲楼,今北京大学俄文楼
实地调查(Fieldwork)是C.K.开始的。他于1933年的夏天到山东去调查市场政策(marketing system)。那一次我没去。我比他落后一步。他在前面,他开创了社会学方法的通路。
我继续去念人类学研究生,希望进一步研究,用人类学的方法补充社会学的方法。Park教授教我们的,他先去做了,开创了社会学的实地调查。这一风气我们一直继续下来,成为现在一个主要的方法。
到现在七十年了。我们两个人都先后要完成我们的“任务”。我虽然还没完成,也快完成了。那么他完成的是甚么东西呢?在历史上要记下来的,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就是社会学在国内历史上的一个经历。曾经有一段很沉重的历史,社会学停止二十几年。1952年我们停开了社会学,中断了各大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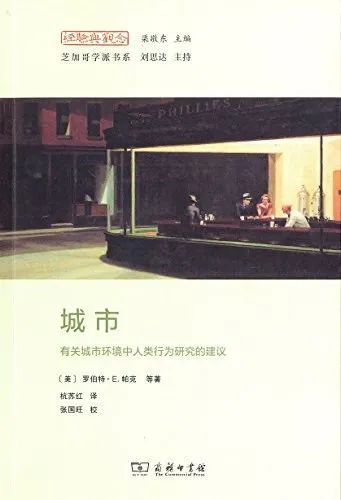
罗伯特·帕克著作《城市》,以生态学方法和田野调查做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这一段时间对我是生命中的一个曲折。我们两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机会见面。他在美国,我是在昆明教书的,大家没有接头。一直到1943年我到美国去,那是在抗战时期,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请了十名中国教授到美国去作文化交流,我就参与那个教授团有机会到美国见到了C.K.。后来他曾经到广州市的岭南大学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北京见过面。
我们对于社会学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我是没有他那么乐观。我是比较悲观。他的乐观表现在他在六十年代,他就同香港中文大学接触,找了李沛良先生等去匹兹堡。他当时在匹兹堡大学教书。后来我知道:六十年代我们正在文化大革命,他就对李沛良讲过,他相信社会学是可以重新在中国大陆恢复的。这一点他比我看得远,看得准。(李沛良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
一个学科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要求,是人类自己的自觉,觉得要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这是没有人能取消它的。可是中国历史里由于各种原因,各大学停止了社会学。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在执政的时候,决定重新恢复社会学。决定之后,我们社会学的人老的都老了,存在的没有多少了。记得1979年的时候,我到美国去,看见了杨先生,讲了我们大陆方面政府叫我组织社会学的重建工作,这个事情我很困难。我那个时候思想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当了二十几年的右派,脱离了国内的社会生活,关系都改变了。这个时候我到美国找了C.K.,我说这个任务怎么办呢?他替我出主意,作了一个计划。他说第一步,要培养一批能教社会学的人,重新办起来。不要恢复我们过去的东西,而是重新把社会学在中国建立起来。他说怎么样去培养一批人呢?便宜的办法是我们借助他打下的基础,在香港、在美国打下的基础。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匹兹堡大学,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他要用他在社会学方面的力量来帮助把中国的社会学继续下去,把社会学在中国的生命继续下去。

1980年,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合影
我听他的建议,回来之后想出各种办法来。在八十年代我们开始办第一、二期讲习班。谁来教我们第一批的学习呢?一看社会学大家很怕的。怕当成一个政治问题。说老实话我也没把握。我说那就冒个险吧。C.K.帮我打气,他说我们一定要把社会学重新建立起来。当时力量也不够。他是美国岭南大学基金董事会的一位董事,他帮助获得基金会的支持。用岭南基金会的钱,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人来讲课。第一个社会学研讨班是1980年在北京举行的。来讲课的有匹兹堡大学的Holzner教授,我们在匹兹堡见过面;香港中文大学是李沛良先生和刘创楚先生,当他们两人到北京讲学,C.K.叮嘱他们,要好好地搞,这第一个社会学研讨班是社会学在中国的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开始的一个起点,责任很大。杨看得很清楚、很远。
这个班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几天前我拿到一本书,那是张仙桥、赵子祥教授策划出版的,第一期讲习班学员的回顾,书名叫《我与中国社会学20年》。历史事实已说得清楚,没有杨庆堃的力量,那个班我当时不可能那么快办起来。是他支持我把第一班的干训班办起来的。那个班一共有四十个人。匹兹堡大学的Holzner教授就到那个班来上过课。还有捷克的Nehnevajsa,他如今去世了。这两方面的力量都是C.K.自己在外建立起来的基础。这个基础成为促成我们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力量。因为我自己这二十多年搞人类学了,也没有化工夫在社会学上边。所以叫我上课我不行了。可是对于社会的科学的研究,方向我们是一致的。
这一个学习班之后,我们第一班的学生,是很好的学生。从黑龙江、辽宁、吉林,到我们天津、北京、上海、广州都有我们这一班的学生。他们和1981年第二班的学员一起,成为我们重建社会学、开展社会学活动的主要力量,并已作出显著贡献。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可是历史的事情不会消灭的。人可以死亡,生命可以断了,而历史可以一直下去。我们在历史上所作的事情一直要为人类服务下去。

1979年3月15—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社会学座谈会。
近些年我仍在农村做社会调查,一直到小城镇的建设。新世纪开始,我在上海大学建立了一个上海社会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上海的变化。这个中心最主要的工作是作社区建设的研究。“社区”这两个字就是杨庆堃同我两个人想出来的一个名词,现在在国内很通行了,到处都在讲社区建设,成为一个热潮。这可以回溯到杨庆堃的《community studies(社区研究)》,这是他专门讲的一们课。
杨庆堃教授是1999年一月过世的。当时他的亲人未通知我。我们的老朋友陈郁立教授的夫人打电话同我说杨先生过世了。她加了一句话说:杨先生临死的时候要求亲属不要发布告,不要采取抢救的方式,所以未通知我。我听说后也很感动。我明白他的想法,是社会学家深刻的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学社会学的人一定很明白,我们的生命同我们社会的生命是有一个区别的。我们一个人,人生在世最多活一百年吧。在这一百多年里边所做的事情,它留在社会里边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传递下去,而且发扬光大。他叫我们注意,不要看他生物人的存在,不要看他生命的长短,我们要看他在这一生里边起的甚么作用,对社会作的甚么贡献。中国有一句老话讲立业,立功,立德,而他一生对社会学的事业确是这样做了。2000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共同悼念杨庆堃教授时,我的讲话就以立业,立功,立德为题,他的一生,就是为社会学,为中国的社会学立业,立功,立德的。
我们要继承C.K.的精神。把他所希望的、播下的种子成长起来。已经长成的更发扬光大,长得更茂盛。继承他的志向,这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历史的遗产。这是C.K.的遗产。他对于我们人类贡献是立业、立功、立德。有这三个“立”,他不会死的,尽管他现在人已经死了。如今他在岭南大学的学生出专集纪念他,为了弘扬他对社会学贡献的一生,也是为中国的社会学的存在和发展祝福,我表示支持。
现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中国要有一个新时代的、现代化的社会学。我希望下一代,继续我们重建社会学的工作,使中国的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里边有我们自己的贡献。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是我们老一辈社会学人的期望,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