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分三期推送费孝通先生的系列专题文章。本期推送《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以及节选自《重访英伦》的“访堪村话农业”。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是费孝通先生1947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演讲稿。该文高度总结了费先生在1940年代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比较研究背后的理论设想。文章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基于匮乏经济状态形成了一套知足和克己的社会心态,“礼”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心态,并以此成为一套文化制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现代西方社会则完成了从匮乏经济向丰裕经济的转型,也完成了社会组织和心态上的转型。其背后依靠的是基督教和罗马法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就要有适合于工业的社会组织。费先生在1940年代数次出访美国和英国,期间他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眼光观察并记录了英美社会的状况。这些内容,以及他早年留学英国时候的经历,都构成他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比较。从选文“访堪村话农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费先生所做的“绅士”研究和乡土工业研究,西方社会经验亦是构成他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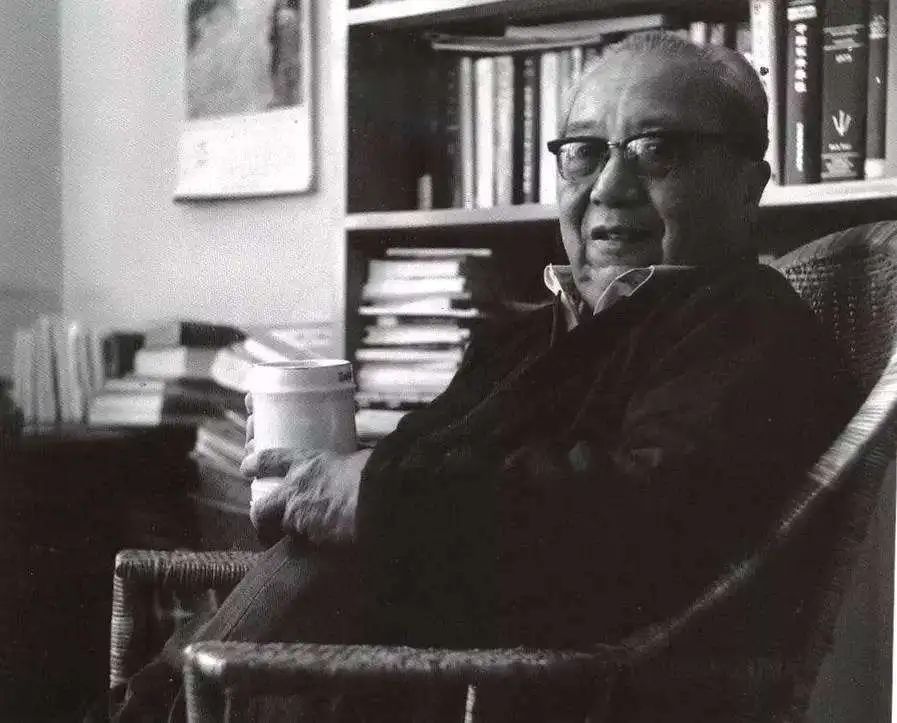
费孝通先生 (邓伟 摄)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文 | 费孝通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在开讲之始愿意很明白的交代清楚,我并不想讨论本题所包括的全部,我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我在这次演讲中,并不能把社会各方面,好像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等的变迁情形,一一枚举,只愿分析在这些方面所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的问题。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我说一“套”,因为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
讲到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位育这个字。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普通也翻作“适应”。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我们若要了解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对于第二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更有兴趣。因之,我在这次演讲中将要偏重于这方面,去分析那些失“时宜”的传统观念。
我这里所说的“处境”其实可以代以常用的“环境”一词。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任何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
对于变迁的概念,我也想作一注脚。变迁是一个替易或发展的过程,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若要描写这过程,最方便的是比较这两种状态的差别。但这是须在后起的局面多少已成形的时候才能有此方便。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敢说。所以我只能先说明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关于新兴的方式则除了可以观察者外,只能参考所采取新的要素在其他社会里所引起的变迁了。我并不愿承认中国从西洋传入了新工具必然会变成和西洋社会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借镜西洋指出这可能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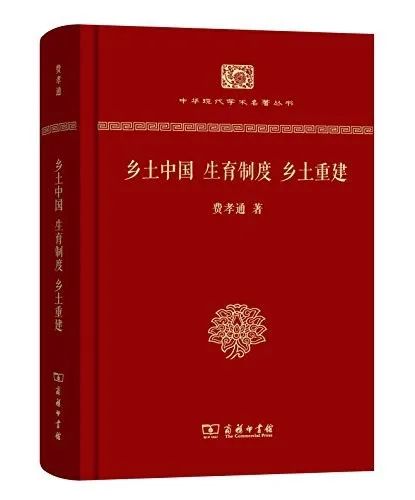
本文作为代序收录于费孝通先生著作《乡土重建》中
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让我从这一句笼统的说法作出发点,进而说明农业处境的特性和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我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单指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丰裕是指不住的累计和扩展,机会多,事业众(我在《初访美国》中有较长的说明)。在这两种经济中所养成的基本态度是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作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关于西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餍求得”精神的关系,已经由今天的主席Tawney教授分析过,我不必在这里详述。我在这里想用同样方法来分析的是匮乏经济和知足观念的关系。
传统匮乏经济的形成有着许多条件。首先,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少是直接用人力取给于土地的。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了中国资源的供给。其次,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北方有着戈壁的沙漠,而且日渐南移,黄沙覆盖了农业发祥地的黄河平原。西方有着高山。东方和南方是海洋,农夫们缺乏航海的冒险性。中华腹地,年复一年地滋长着人口,可耕的可说都耕了。悠久的历史固然是我们的骄傲,但这骄傲并不该迷眩了我们为此所负担的代价。这个旧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似乎最适合于中国的情势了。但是我却常觉得并不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口会这样多,使他们生活程度不能不降得这样低。人究竟不是普通的动物,依着生物原性去增加他们的后裔的。中国人口的庞大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在利用人力和简单的工具去经营农业的时代,这也许是不能避免的现象。农作活动是富于季候性的。在农忙时节,很短的时间中,必须做完某项工作,不能提早,也不能延迟。若是要保证在农忙时节不缺乏劳力,在每一个区域之内,必须储备着大量人口。农忙一过,农田上用不着这些劳力了,但是这批人口还得养着。生产是季候性的,消费却是终年的事。农田不但得报酬所费的劳力本身,而且还要担负培养和储备这些劳力的费用。农业和工业性质的不同也分出了担负的轻重。表现出来的是人多资源少的现象。
土地所需劳力的分量是跟着农业技术而改变的。若是农业中工具改进,或是应用其他动力,所需维持的人口也可减低。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碰着了一种恶性循环。农业里所应用人力的成分愈高,农闲时失业的劳力也愈多。这些劳工自然不能饿了肚子等农忙,他们必须寻找利用多余劳力的机会。人多事少,使劳力的价值降低。劳力便宜,节省劳力的工具不必发生,即使发生的也经不起人力的竞争,不值得应用。不进步的技术限制了技术的进步,结果是技术的停顿。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的社会。
我承认物质生活的享受总是人生的一种引诱。但是我们应当问的,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匮乏经济中这种引诱会引起什么结果?在村子里,每一方田上都有着靠它生活的人。若是有一个人要扩张他的农田,势非把别人赶走不成。一人的物质享受必然是其他人生活的痛苦。路上的冻死骨未始不就是朱门酒肉臭的结果。人不向自然去争取享受,而在有限的供给中求一己的富裕,结果不免于人相争食。这并不是东方的特色,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桑巴克曾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通性是“从权力得到财富”。在中国历史上固然不缺乏刘邦、朱元璋之类的人物,但是每个人若都像项王一般,存着“取而代之”的心思,这个社会显然是难于安定了。没有机会的匮乏经济中是担当不起这一种英雄气概的。刘邦、朱元璋究竟是亿万人中的幸运儿,不足为训;历史上读不到的是屈死篱下的好汉。尊荣享受所给的对象是个人,幻灭是社会的混乱。这史实,这教训,这领域,凝成一种状态,知足安分;一代又一代,知足安分的得到了生存和平安,谁能否认这不是处世要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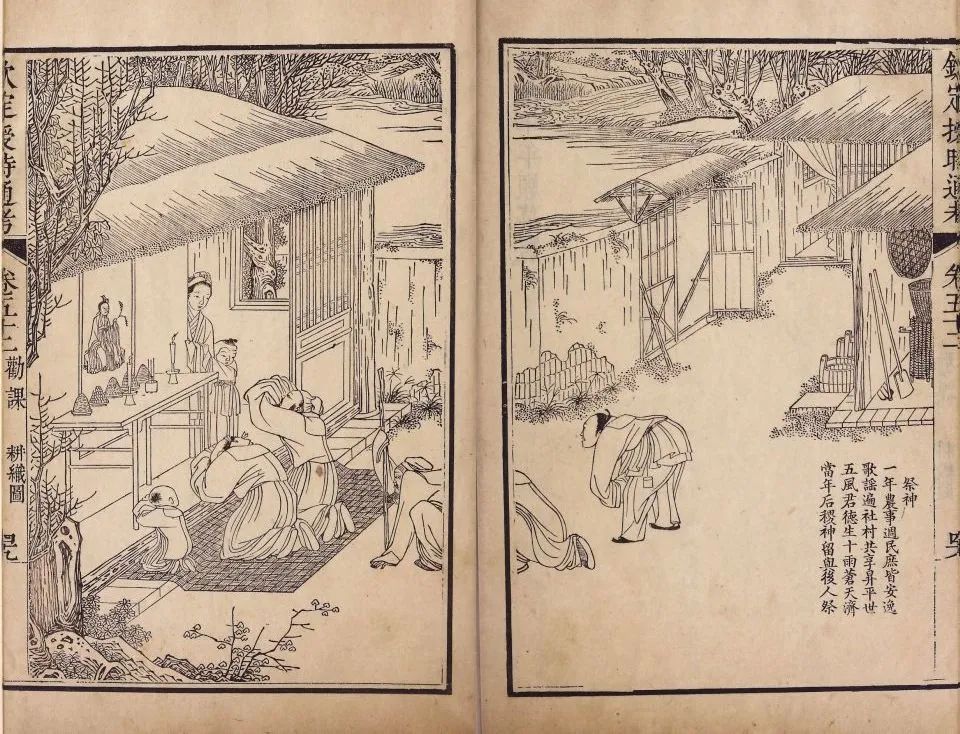
《钦定授时通考》
我这种分析并不想把价值观念只视作客观经济处境的心理反映。观念是文化中不能分的一部分;是一种帮助社会位育处境的力量。在资源有限的匮乏经济里有不知足不安分的人,而且对于物质享受的爱好,本是人性之常,但是这种精神并不能使人在这处境中获得满足,于是有知足安分的观念发生了。这观念把人安定在这种处境里。我并不是在批评这种观念,我不过想了解这观念。
从这个角度里去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对它的领会。我常觉得我们这位“万世师表”所企图的是在规划出一个社会结构,在这结构中有着各种身分(君臣父子之类),每个人在某种身分中应当怎样想,怎样做。社会结构本是人造的,人造的东西都可以是一种艺术。社会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身分安排定当,大家安分的生活下去,人生的兴趣就在其中——“吾兴点也”。这正是像英国的国术足球。球员们从不感觉到球场应当要加宽一些,球得加重一些,或是增加几个球员。他们是安“分”的。他们更不会坚持一套规则只许自己用手,不许人家用手,自己门上装个铁网,人家门前不许守卫。这样做不成了玩球了。人生的鹄的若在“游于艺”的话,我们似乎必须有一套社会结构。这结构的创立固然需要合于艺术的原则,大同之境,而人也需要安分的精神。这精神就是“礼”,我很想翻译成英国人民所熟习的sportsmanship。Sportsmanship是承认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动的服从于这地位的应有的行为,也就是“克己”。在北平街上,有些门上还可以看到“知足常乐”四字。快乐是人生的至境,知足是达到境界的手段。
我并不知道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否快乐;但是知足的态度却使他并不能欣赏进步的价值,尤其是一种不说明目的地的“进步”。孔子对于生产技术是不发生兴趣的,他是一个在农业社会里不懂农事的人。他的门徒中比较更极端一些的像孟子,劳力的被视作小人了。当时和儒家不太和合的庄子,在限制欲望、知足这一点上是表示赞同的,以“有限”去追求“无限”,怎么会不是件无聊而且危险的事呢?惟一对于技术有兴趣的是墨家,在中国思想上所占的地位远不如儒家,这也可以说明在一个劳力充斥的农业处境中去讲节省劳力的技术,是件劳而无功的事。我在这里并不能对中国传统思想多作介绍,我所想的是指出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
在这里我想对儒家偏重身分的观念再下一些注释。儒家的注重伦常,有它的社会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供给了显明的社会身分的基图,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这些身分比了其他社会团体中的身分容易安排,容易规律。而且以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关系,一表三千里,从家庭这个起点,可以扩张成一个很大的范围。而且在亲属扩展的过程中,又有性别、年龄、辈分等清楚的原则去规定各人相对的行为和态度。在儒家的社会结构中,亲属也总是一个主要的纲目,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模范。
以亲属关系作结构的纲目是同儒家以礼作社会活动的规模相配合的。礼,依我以上的注释,是依赖着相关各人自动的承认自己的地位,并不是法。法是社会加之于各人使他们遵守的轨道。自动的合作,必须养成于亲密、习惯、熟悉的日常共处中。“学而时习之”的习字,是养成礼的过程。足球的指导员一定明白球员的合作必须经过朝夕的练习。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也很近于哈佛大学Mayo教授所谓social skill,直译是“社会技术”,意译是“洒扫应对”。用普遍社会学的名词来说:积极的和自动的合作需要高度的契洽,契洽是指行为前提的不谋而合,充分的会意;这却需要有相同的经验,长期的共处,使各人的想法、做法都能心领神会。换一句话说,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场合。在家庭和亲属关系里,“社会技术”最易陶养,以礼来规范生活的社会也最易实现。儒家想创造一个礼尚往来的理想社会结构,中国原有的亲属组织也就成这结构的底子了。
也许我们可以问这种把社会身分规定住了的结构不是一种保守主义么?从人类文化的物质基础上说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儒家并不是反对物质的享受,孔子至少承认富人也可以为善,虽则和穷人为善的方法不完全相同。他对于贫富、财货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人和人的相处,并不在人对自然的利用。我们若要为儒家辩护,可以说不论人对自然的利用到什么程度,人和人相处相得还是和人生直接有关的问题。对于这问题,人类还得不住的用工夫,求善道。因之,儒家可以有理由对物质享受之道不加关心。不关心并不是疾视,“你去问别人好了”。若是我们从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儒家并不是保守的,而是有理想的,有理想的就不能对现实满意。孔子的栖栖皇皇,坐不暖席,为的是他有理想。社会结构的标准是完整,是大同。这个概念和法国社会学家的前驱Le Play和Durkheim很相近。大同或是社会完整,很不易加以简单的定义,若是必须要说的话,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程度,在这程度上个人觉得和团体相合,而且在作这整体的一部分时,个人从团体中获得他生活需要的高度满足。Durkheim在他的《自杀论》里反面的说明了不完整社会的形态。在他之前Le Play已有6册巨著分析工业初期欧洲社会的解组。这两位大师对于英国人类学的影响之深早已显著,但是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却并没有引起海峡对岸的回响。可是,远隔大西洋的美国,这基本概念,社会完整,却被许多研究工业组织的学者们所重视了,可惜的是数十年中,人类已经受到两次大战的打击了。回念我们被视为古旧的中华文化,几千年来这问题久已成为思想家的主题。东西相隔,我们的传统竟迄今没有人能应用来解释当前人类文化的危机。人类进步似乎已不应单限于人对自然利用的范围,应当及早扩张到人和人共同相处的道理上去了。
我对中国传统秩序已说了不少的话,可是我还是只能粗枝大叶的提出一些问题罢了。我这篇话只想说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社会的性质相配合的,而且互相发生作用的。希望并没有引起一种误会,认为我是主张回返传统或是盲目于饥饿的群众。即使我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人生活的幸福或乐趣,我也决不愿意对传统有丝毫的留恋。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是已经走了,去了。最主要的理由是处境已变。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悠然见南山”的情境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是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我不反对我们能置身当年情境欣赏传统的幽美,但这欣赏并不应挡住我们正视现实:这一个利用自然动力,机器和庞大组织的生产方法;这疾如流星,四通八达的交通;这已经发现了利用原子能的新世界——回到我最初的命题,这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丰裕的经济。
我并不觉得自己配谈西洋文化,我缺乏分析这新处境所需的知识,但是从别人的著作中看去,似乎工业革命曾在欧洲社会引起过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在西洋人民的生活中已有一套新的原则在活动,在若干方面正和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种生活方式刚刚相反。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方和西方事事相左,我们的白天是你们的黑夜;你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人类文化有着基本的相同点,但是今天我是在讨论变迁,变迁是出自相异。
若是匮乏经济和丰裕经济只是财富多寡之别,东方和西方正可以相邻而处,各不相扰。贫而无谄,富而好施,还是可以往来无阻。但是这两种经济的不同却有甚于此。匮乏经济是封闭的、静止的经济,而丰裕经济却是扩展的、动的经济。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洋,代表着一个扩展的过程,一个无孔不入的进取性的力量。甘地想从个人意志上立下一道匮乏经济的最后防线,显然是劳而无功。这世界已因交通的发达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在这一体之内,手艺和机器相竞争,人力和自动力相竞争,结果匮乏经济欲退无地,本已薄弱的财富,因手工业的崩溃、生产力的减少,而益趋贫弱。在这方面说,确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场合。尽管你可以瞧不起锦衣玉食,但是当饥寒交迫的时候,谁也不能不承认生活确是有一道物质基础的。当经济的竞争把人推到不能不承认物质生活的重要时,怎能不憬然醒悟最初不重视物质生活的失策了。
即在东西接触之初,西学的实用是早经公认的了,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说,直接使东方受到患难的是西方的武器和生产技术。这就是“西学为用”的用的方面。在学习和接受西学之用的方面时,我们逐渐发现了用和体是相关联的,是一套文化。技术是人利用自然的方法,重视技术,发展技术是出一种人对自然的新关系。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的方式上是修已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在丰裕经济中则相反,是修天以顺己,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这种对自然的要求控制使人们对它要求了解,于是有了科学。西学确是重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根本上脱不了利用厚生之道,是重“用”的。但是这偏重的背后却有一种新的看法,这看法规定着人在宇宙里的地位,是出于西洋宗教的基源。第一点,今天的主席Tawney先生已经分析过,不必重述。我想指出的是在基督教传统中所孕育的那种无餍求得的现代精神,只有在一个丰裕经济中才能充分发挥,成为领导一个时代的基本力量。我在论匮乏经济时曾指出一种循环: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在丰裕经济中也有一种循环: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到现在至少已有一部分人感觉到,科学发达得太快,技术进步得太快,人类已不知怎样去利用已有的科学和技术来得到和平的生活了。这两种循环比较起来,前者已造成人类的贫穷,后者已造成了人类的不安全,都可以说是恶性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决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的知足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我不敢说在人事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很大的早就,但是在科学上没有发达,那是无法否定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说中国的科学已有基础。我怀疑在中国经济得到解放之前科学在中国是会入土滋长的。我们要知道过去100年东西的接触,并没有造下中国能在本土发达科学的处境。这远东的大国至今不过是西洋工业的市场,本身并不是一个工业的基地。我似乎觉得工业化和科学化是相配的,分不开的。日本工业发达之后,科学上的成就并无逊于西洋,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中国经了100多年,在接受西洋文化上还没有显著的成效,在我看来,是在我们匮乏经济的恶性循环并没有打破,非但没有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反而因为和现代工业国家接触之后,更形穷困。在这生产力日降,生活程度日落的处境中,绝不会有“现代化”的希望的。
在接受西洋生产技术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困难,我愿意在这里加重的提到,那就是利用现代技术的社会组织。在西洋,因为现代技术的需要产生了集中的工厂。工厂在中国都市里也发生了,机器也装上了,工人也招来了。虽则在规模上比不了西洋,但是这新的生产组织至少也传入了中国。中国乡土工业的崩溃使很多农民不能不背井离乡的到都市里来找工做。工厂里要工人,决不会缺乏。可是招得工人却并不等于说这批工人都能在新秩序里得到生活的满足。有效的工作,成为这新秩序的安定力量。依我们在战时内地工厂里实地研究的结果说,事实上并不如此(可参考史国衡著《昆厂劳工》)。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的工厂里,扩大一些,现代的都市里,正表示着一种社会解组的过程,原因是现代工厂的组织还没有发达到完整的程度。

开平矿务局
我在上面已说过社会完整的意思。在完整的社会里社会所要个人做的事,养孩子,从事生产,甚至当兵打仗,个人会认真地觉得是自己的事。这就是我所谓“个人觉得和团体相合”的意思,要使人对于社会身分里的活动不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享受——孔子所谓“不如好之者”的境界——至少要先使人对于他所活动的关系有认识;活动、生活、社会三者要能结合得起来。这里,在我看来,必须要一个完整的人格,就是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得在一个意义之下关联起来,这意义又必须要合于社会所要求于他的任务。现代技术的发达在社会组织的本身引入了一个“超人”的标准,那就是最小成本最大收获的经济律。在这标准之下,再加上了机械活动的配合律,串成一套生产活动,支配这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参加活动者的个人目的,甚至并非社会的目的,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效率而效率的超于人的目的。资本主义的不断累积,是出于积财富于天上的动机。
在这种活动体系中,一个工人实在不易了解在这体系中他个人活动的意义何在,除了从这活动中所得到的报酬。他们能吸收到个人生活体系中去的只是这报酬,并不是活动的本身,他们对于活动本身并不发生兴趣,没有乐趣,更谈不到“好之”的境界。于是在现代工业里的劳工最主要的要求是,少做工,多得报酬,这还是欧美劳工运动的基本目标。在社会学的观点上看,是社会解组的现象,因为这里充分表现了社会缺乏完整。Le Play和Durkheim很早的见到这个趋势,感觉到人类社会的危机。
西洋这社会解组的趋势并没有很快的走上危机,因为现代技术虽则一方面打破了社会的完整性,但是另一方面却增进了一般人民的物质享受。而且他们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的用“法”把社会关系维持下去。基督教和罗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两大遗产,和现代技术结合,造成了个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在中国,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反的,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
在歧途上的中国正接受着一个严重的试验。我当然希望欧美的文化既已发生了现代技术,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创造出一个和现代技术能配合的完整的社会结构。这可以使在技术上后进的东方减轻一些担负。但是我不能不怀疑现在这种结构已经存在,虽则我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出现确表示着对这方面的迈进。以往只在技术上求发明,而忽略各社会组织上求进步和配合,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憾事。我们的传统,固然使我们在近百年来迎合不上世界的新处境,使无数的人民蒙受穷困的灾难,但是虽苦了自己,还没有贻害别人。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若是西方经过了这两次大战而不觉悟到非注意到人和人的关系时,我想也许我们几千年来在这方面的研讨和经验,未始没有足以用来参考的地方。在这里记起Radcliffe-Brown教授的话,他发挥了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之后,在中国的一次旅行中,发现了荀子的著作里有着不少和他相同的见解。在欧洲曾有过一次文艺复兴,为这现代文化开了一扇大门,我不敢否认世界文化史中可能再有一次文艺复兴。这一次文艺复兴也许将以人事科学为主题,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传统可能成为复兴的底子。我不必在这方面多作猜测,在我们中国立场上讲,我们只有承认现代有的弱点,积极地接受西洋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明了怎样去利用现代技术和怎样同时能建立一个和现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是两个不能分的问题。若是我们还想骄傲自己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出我们的贡献来。
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若是东方的穷困会成为西方社会解体的促进因素,则我们共同的前途是十分暗淡的。我愿意在结束我这次演讲之前,能再度表达我对欧美文化的希望,能在这次巨大的惨剧之后,对他们文化基础作一个深切的研讨,让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
1947年1月30日
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术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