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文藻先生对非汉族团的民族志倡议开始,燕京学派就开始了将社区研究的方法运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尝试。这种尝试,主要是基于功能理论的基础,希望将民族志社会学发展得更为全面。吴文藻先生给费孝通和王同惠合著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序言对此理念有明白的阐述,也最见他与学生之间同道而共情的缘分。1938年吴文藻离开燕大,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在直面战时中国之现实的同时,又将燕京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理念前所未有地推进到第一线的田野工作中。燕京学派第二代中在边疆民族志中最有成就的两位学者,李安宅和林耀华,在西南后方的不同田野中,以非凡的毅力将燕京社会学的社会学民族志设想与甘南,川康地区的宗教与社会结合起来。李安宅将格鲁派重镇拉卜楞寺视为政区单位,佛寺和社区三位一体的结构,仍然可见早期燕京学派对社区边界的概念构造。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出生于1910年代末的社会学子,在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组织和亲身教导下,成为继承燕京社会学理想的第三代学人。
本期我们分别选取了吴文藻为《花篮瑶社会组织》撰写序言第三节、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正月祈祷”一节以及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中“社会结构”一章,以呈现燕京学派三代学人在边疆社区研究中的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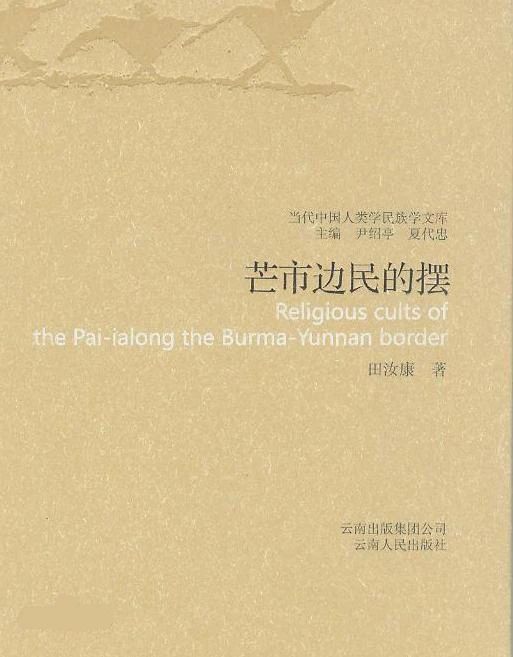
社龄结构
文 | 田汝康
摆夷女性的生命先可以划作四个阶段。一个女性自出生后即跨入了第一期。这一个时期等于普通的养育时期。她完全接受家庭的抚育,一直等到她能够自己独立生活为止。这时期中她的名字有着一定排列方法,头生叫“小耶”,次生“小玉”,以下依次叫“小安”、“小爱”、“小娥”、“小矮”,至第六位为止,假若依姐妹行列中第七、第八,就叫做“小七”、“小八”,以此类推。她们的衣着也有一定:穿裤,着短袄,颜色并不规定。头上梳有小辫,有的还戴一顶圆形的瓜皮小帽。到八岁左右每人再添上一块短的围腰布系在腰间。这个时期社会加给她们的名称叫做“小人”。
从开始曳裙起,她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由“小人”一变而为“小菩色”。个别的名称虽则仍旧,而衣着上的改变则很大:短袄一概改穿淡色,其中尤以穿白色的为多,辫子不再拖着而盘在头上。在内衣里面更用丈多长的布带从胸部起一直缠到腰部为止,借此来保持体态的苗条。在这一个时期当中,她们开始接受社会的训练,为社会事业做种种的服役。她们虽仍是家庭之一员,有时也常代替家庭出外服役,不过这样的人员仅占少数。大多数人由工作所得的报酬仍完全花费在自己的消费上。她们可以自由组织团体,也可以自由交纳异性,工作上的繁重自是事实,但是生活上的享受也要算她们最为丰富。由参加青年团体在摆中服役起首,一直到结婚为止,这个时期方告结束。
 结婚仪式是她们第三个阶段的开始。第三个阶段的女性,衣着上的区别是将盘在头上的辫子改梳成一个冲天髻,再在发髻的附近用黑色布条密密地围成一顶圆帽的形状。等到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名字亦因而发生变动。第一个孩子若是女性的话,她的名字就改称“咪耶”,在夷语中,Mi(咪)是母亲,Je:(耶)是第一个女孩的普遍称号。若第一个孩子是男的,则她将改称“咪恩”。aan(恩)是头生男孩的普遍称号。这个时期内的女性差不多将所有精力全致力家庭事务上。摆夷社会中,结过婚的男女差不多全数脱离父母出外另组家庭,不管公婆已否留有遗产。在独立谋生中,她们得竭尽能力去工作。因为,第三阶段中的女性,既不能有小人们那样受父母养育的权利,也不会有小菩色那样尽量享受的闲情;一旦再加上膝下儿女抚育的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将更限制在这一个小天地内。
结婚仪式是她们第三个阶段的开始。第三个阶段的女性,衣着上的区别是将盘在头上的辫子改梳成一个冲天髻,再在发髻的附近用黑色布条密密地围成一顶圆帽的形状。等到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名字亦因而发生变动。第一个孩子若是女性的话,她的名字就改称“咪耶”,在夷语中,Mi(咪)是母亲,Je:(耶)是第一个女孩的普遍称号。若第一个孩子是男的,则她将改称“咪恩”。aan(恩)是头生男孩的普遍称号。这个时期内的女性差不多将所有精力全致力家庭事务上。摆夷社会中,结过婚的男女差不多全数脱离父母出外另组家庭,不管公婆已否留有遗产。在独立谋生中,她们得竭尽能力去工作。因为,第三阶段中的女性,既不能有小人们那样受父母养育的权利,也不会有小菩色那样尽量享受的闲情;一旦再加上膝下儿女抚育的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将更限制在这一个小天地内。
她们辛苦工作,积蓄到能够做大摆(不论她丈夫做或是她自己做),她就走入第四个阶段。能做摆的大致家庭生活线已超过水平线以上。这时衣食丰裕,儿女成行,多年的辛苦又为她们腾出一些空闲的时间。做了一次大摆之后,她们的名字是巴戛了。年龄的增加使她们的兴趣也有改变。短袄的颜色由白淡色变为深色。此后的生活也将由家庭跳到冢房里面。一块黑色的围肩是她们这时期的标识,念佛祈祷成了她们日常的功课,她们生活的重心已不再是家庭工作了。
男性的生命史也分为四个阶段,一般的情形和女性差不多。第一个阶段是由出生开始,称作小人。个人的名字却和女性不同。以出生的次序,第一个称“小恩”,第二个称“小二”,第三个称“小三”以此类推。在四个阶段里,男性衣着都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能在身上找到的区别,仅是一些装饰品。可是佩戴这类装饰品的亦不是人人一律,例外的情形常常可以见到,第一个阶段上男性所有的装饰是耳上穿环,但仅在左耳。在这时候,他们全在家庭保护中生活。稍长常也帮着家庭做些事情,大致工作的性质是很轻松的,如放牛、割草之类。工作中常常带有游戏的性质在内。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参加青年团体在摆中服役。他们这时一般的称号是“小菩毛”。有的耳环已经除去,有的则留着。普通多在左手上添戴一只银手镯。这一个阶段的青年逐渐有脱离家庭范围的趋势。他们除了参加村寨中公共青年团体之外,另外自己还有种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例如以聚餐为目的的吃饭会,结婚时经济上帮忙的钱会。不单在摆中大家做种种的服役,有的青年这时已经代替家长出来应付政府的种种差遣。他们效法中年人练习各种事物,有的也合资请位先生来学习文字。总之,这一个时期可以算是真正接受社会训练的时期。
 结婚是一条分水线,它将摆夷青年男女割分在两个不同的区域里面。第三个阶段是一个青年经过家庭抚育,社会训练,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成为社会上的工作干部。他们自立门户,也是社区中独立的生活单位。衙门里的户册上有他们的名字,将担负公共事务的责任。这是人生最艰苦的一个时期。他不能再像在小菩毛时期那样放荡了。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未必再有这样的心情。这时他同他的妻子所积极寻求的是如何维持生活,如何抚育子女。当他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也改用另一个名字,孩子是男的,他称作“波恩”,孩子是女的则称“波耶”,这一个阶段上的男子,耳环已脱去,不过手镯却仍戴在手臂上。
结婚是一条分水线,它将摆夷青年男女割分在两个不同的区域里面。第三个阶段是一个青年经过家庭抚育,社会训练,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成为社会上的工作干部。他们自立门户,也是社区中独立的生活单位。衙门里的户册上有他们的名字,将担负公共事务的责任。这是人生最艰苦的一个时期。他不能再像在小菩毛时期那样放荡了。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未必再有这样的心情。这时他同他的妻子所积极寻求的是如何维持生活,如何抚育子女。当他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也改用另一个名字,孩子是男的,他称作“波恩”,孩子是女的则称“波耶”,这一个阶段上的男子,耳环已脱去,不过手镯却仍戴在手臂上。
他做摆的时候,才踏入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他可算是退休的人物了。多年饱尝人间辛酸之后,大多数人已经不必再从事劳作了,生活所需一切由他的儿女来负责。他们现在所追求的只是人生最后一步,同时也是他们最渴望的一步。大家对着这一个最后的目标不断前进。戒烟酒,禁腥荤,终日焚香礼佛。最终与人世脱离,结束了他们整个生命的历程。
这四个人生的阶段在人类学现有的词汇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词。相近的是“年龄级”,但是年龄两字严格说来是指生命的时间段落,过一年就长一龄。摆夷的人生阶段并不以实际年龄作为升迁标准的。因之在同一阶段上的人,年龄可以有相当的参差。第一个阶段中有十八岁未曳裙的大姑娘,而第三个阶段中也有着十六岁就做咪耶的女孩。年龄的大小且不计,而其中的差别也整整超越了一个阶段,甚而有的人还始终逗留在一个阶段里不能上升的。小菩毛若找不到相当的配偶,他岂不是一生逗留在第二个阶段上么?这种人在摆夷中称作“饿毛”。那时调查那木就有不少饿毛。一生没有机会做大摆的事实上也有相当的人数。关于这一类人就爬不到第四阶段,白首童生,真是马齿徒增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摆夷人生中四个阶段和年龄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年龄组一词既不能表示出摆夷社会结构的特性,所以我只能采用社龄这个新名词了。社龄可以包括两层意思:它是生命史上的阶段,一级一级有个次序,所以称作龄;这些阶段并非代表体制的成熟和衰老,而是代表社会的身份,各级享受的权力不同,应尽的义务又不同,这种社会性的划分正可用个社字来表示,它的意义有如教育心理学中的智龄和学龄。
摆是转换社龄的仪式。最明白的是做摆主人经了这番热闹之后,由大和尚颁布了他是巴戛,他就升入了第四社龄。不做摆的永远升不进这第四社龄。这个社龄中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权利呢?最好是举两桩我亲自知道的事实来做例子。当我在那木寨做调查的时候,有一次寨里的项老辛要请我去喝他五儿子的喜酒。他说这是他最后一件喜事,千万务必请我赏光,并且说新娘子从弄木来,假如要看新娘的话,时间不妨晚一点。我当时想弄木的老辛我也认识,按照惯例,他的五儿媳准是弄木嚢老辛的女儿。因为老辛虽不是贵族,不过大小也是一寨之长。这桩喜事既然一旦临到素来最爱面子的项老辛份上,他总不至娶一个寻常村民的姑娘做媳妇。可是当我问他,“你同嚢老辛几时打的亲”,他却连忙回答,“不,不,不是老辛,而是弄木一位巴戛”。接着更补充说“Pa:go:‘raunmu:’kaunhe:”这是说他的亲家已经做过两次大摆,而且还造了一座桥,他表示他亲家的身份是相当高的;嘴角上两道凹纹,更露出他的得意之感。另外,我在坝子里遇见过一位由小贩起家,现在已经成为邻县大财主的内地人。当他驾着卡车来坝子里面做买卖的时候,摆夷都叫他作朱巴戛。邻县走夷方的人并不少,而成功的要数他。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现在所有汽车、田地、商店从哪里来呢?和他多次接触之后,我并不能找出他具有哪一种特殊的才能。不但不如其他走夷方的精明强干,而且还有点傻气,就因为他傻,所以他能够发大财。事实是这样。当他初进夷方坝,略略找得几文钱之后,由于看到摆夷做摆的热闹,传说巴戛死后可以升天,他也忽发奇想,想做一次摆。不过尽其所有也不过百多元钱,事实上又做不成摆,于是他把这几文钱亲自送到城子官冢里面去做功德,要求大和尚给他一个巴戛的名号,同时还向土司去纠缠。这样奇特的举动,弄得大家莫名其妙,结果不得不敷衍一下,真的把巴戛的名号给了他。转瞬之间,他就钻进了摆夷社会里去了,得到了一般走夷方坝所独有的权利。巴戛是善人,买谷米少给些价钱也无所谓;向朱巴戛买东西价钱多些也不在乎。巴戛衔头的魔力使他换取了不少实际的利益。巴戛的称号本来就是预备死后在天上兑现的期票,但从现在的事实看来,却在人世里兑现了,甚而可说是提前地兑现,因为它可以在现世得到很大的效用。依我在坝子里面五个多月的观察,很可以看出一般对于这张期票的重视。土司即使做了十件富国利民的新政,其价值倒不如老祖太,土司的母亲,做一次摆。大家所希望的不是要像金火头那样富有,一年可以出卖几万箩谷子,更不是要像大总管那样膂力过人,一手可以敌过几十个人,而是要像城子的一位老头,为做十二次大摆以致倾家荡产衣食俱无的豪举。对于这样的人,大家决不敢笑他傻,反而极端地敬仰他,万分地尊重他。有机会还想尽力效法他。要不是土司善言的劝告,希望大家留一点钱婚男嫁女的话,也许弄砍做过十次摆的线老头,那木做过九次摆的老干会来一次打破纪录的举动。他们这种比赛的干法,已不能再以获得天上宝座的信仰来解释,因为做了六次摆以后已没有新的尊号可加,他们显然是为了社会的赞誉,为了自己的身份,才这样起劲。
 参加做摆的不只是做摆的主人,在这活动中,服役的人一样重要。而且我在上文中已经提过这项服役甚至可以说是小菩色、小菩毛的责任,也习惯强制他们。他们参加服役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因为从参加服役中他们才能由第一社龄进入第二社龄。可是进入第二社龄会有什么意义呢?
参加做摆的不只是做摆的主人,在这活动中,服役的人一样重要。而且我在上文中已经提过这项服役甚至可以说是小菩色、小菩毛的责任,也习惯强制他们。他们参加服役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因为从参加服役中他们才能由第一社龄进入第二社龄。可是进入第二社龄会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哪一家的女孩子允许他人可以自由求爱的时候,总得有一个表示。这个记号就是穿裙。穿裤是小人,穿裙是菩色,这个身份的改变就在她第一次参加做摆的服役。这可并不和年龄有一定关系的。有不少生理已成熟,年龄也已相当大的,还穿裤的;穿裙的女孩子中也有年龄很小,生理已否成熟尚成问题的。据摆夷自己的说法:有的说通例一家人只许一个未嫁的女儿穿裙;假如姐姐未嫁,妹妹无论年纪多大,只能穿裤子;有的说,少一个女儿穿裙,做摆时可以少负担一份费用,因为我已提起过,别人做一次摆,小菩色、小菩毛都得赔一笔支出。没有穿裙的小人是没有资格公开结交异性朋友,谈恋爱,准备结婚。第二社龄给一个女孩子可婚的权利,同时我们也已看见青年男子们有各种团体的组织。有一种是互相帮钱应付结婚的费用。入了第二社龄的小菩毛才有参加这类组织的权利,这也表示要取得可婚权利得先摆脱小人身份。摆脱这身份的机会就是参加做摆服役,因之,我们可以说摆不但是从第三到第四社龄的转换仪式,也是由第一到第二社龄的转换仪式。
在摆的仪式中,摆夷如何从第三社龄阶段进入第四社龄阶段,第一章中已经有过详细地描述。至于在摆的仪式中,摆夷如何从第一个社龄阶段进出第二个社龄阶段,如何又从第二个社龄阶段进入第三个社龄阶段,在这儿将值得我们详细的加以叙述。首先我们叙述关于青年团体的情形。青年团体夷语统称作Evency;分别称谓起来,男青年部分又叫做Kwenmou,女青年部分又叫Kwensou。这一类团体的组织纯由青年自主,而有时候也受到村寨中老干老辛的指导。大致村寨人口较少的,一村寨组合一个团体;村寨人口较多的,一村寨可以有几个团体,那木寨一寨便有三个团体同时存在着。一个团体中,男青年算为一部分,女青年算为另一部分,各分别有男女队长统辖着。人数多寡不一,多的可到百人左右,少的亦不下三十余人。在团体中,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队长,但公众的意见最为重要,队长有时候不过是一个经常事务的管理人而已。普通担任队长的不外乎是一个在团体时期最久的饿毛或饿色。加入团体的资格,概以未婚青年男女为主,成年男子太太已去世的鳏夫或与太太离婚的,仍可以加入男青年部分,没有丈夫的寡妇(无论丈夫死去或是与丈夫离婚的统称为寡妇)则仍可以加入女青年部分,已婚男女有的亦例外地加入这一类团体,不过团体对于他或她所希求的与一般普通团员并不相同,而他或她自身也有很多困难必须自己设法事先有所解决。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要再度讨论到。
对于团员入团的手续也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最主要的要看这个团员家庭情形如何而定。所谓家庭情形是指家庭是否富有,父母为人不至于太令人讨厌,以及这个团员行为表现上不至于太令人看不起而言。设若一家人家境很好,父母待人很和气,孩子又很出色,则这家孩子加入团体的时期亦必很早,否则就要迟一些。入团只要团中有人来邀约即可,来邀约意旨可以出自老干老辛的示意、队长的命令,以及团员的提议,自动加入的也有,不过主要是团体中人不拒绝方能成功。每一次做摆,尤其是大摆、挺塘摆和干躲摆这三个时期,团体中均增加一大批新的团员,习惯上成为了青年团体招收团员的一定时期。因为平常青年团体并没有了不得的工作要做,在摆中青年团体发挥了它最大的效用,而且只有在摆中,青年团体才真正获得了一个公开社交的机会。一个摆夷青年若是失掉了参加青年团体的机会,那无疑剥夺了他生活的乐趣。这是人生旅途中一个最大的打击,我们应该知道青年团体虽在摆中表现了它服役的功用,而另外在这个团体内,青年男女还可以很方便地选择自己理想的伴侣。虽然习惯上并不禁止男女青年与另一青年团体中人互相嫁娶,但事实上一个男青年很不容易到另一个团体中去选择他的恋爱对象。同时一个团体中的团员也决不愿意另外一个团体的人和同性闯入本团体中来作平行的竞争。在摆的仪式中,常会发生两个青年团体殴打的事实,有时甚而可以引起两个村寨的纠纷,进而上控到土司衙门里去。这表示青年团体在训练团员间极坚强的团结意识,而社会所希求青年们受到的训练,也正就是这些。
一个人结了婚,就从第二社龄阶段进入第三社龄阶段,其中婚礼是一个最大的转变关键,可是这个身份转变必须从摆的仪式中才表现出来。可以显示身份改变的,第一个机会是结婚后冷细中的干躲,凡是初二到冢房里干躲的,都指明这些男女已经向佛祖告过别,今后将另是一个团体中人了;第二个机会是在摆的仪式中参加另一种团体组织,这种团体称作Bubobumi:n,团员竟是些成年男女。在摆的仪式中,这种团体并不曾负有什么特殊任务,至多也不过集合做些贺客做的事情,集合地看看热闹而已。在第一个机会中,一个刚结婚的男女是被习惯强迫参加的。而在第二个机会中,则第一次中是为了好奇的心理,几次以后,大多抱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这种团体并未曾规定一种成年男女必得参加的条件,况且这时候成年男女所需要的已大有不同。这种身份一直维持到他们自己做摆,脱离第三个社龄阶段为止。
一个已结婚的男女习惯上也可以再度回到青年团体中去。不过在团体中他应该担负更多的用费,或是一大笔意外的捐款,否则他的参加会遭遇到全体团员集体的攻击。而且即使团体中允许他这样做,另外他还得考虑到其他人的批评,至少夫妇间是否彼此同意这样做。不存了非分的企图,谁愿意出一笔钱去做这种事情。设若家庭间彼此默认这样做法,则真正重返这种团体的机会已是日益迫近了。
这里可见个人身份的转换都得在做摆的仪式里。摆的功能之一就在安排社会中的个人社龄,维持摆夷社会的结构。
摆既是安排社龄的结构,摆在摆夷生活上的重要性就跟着社龄在他们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定了。摆夷社会结构所根据的原则,和其他社会一般是多种的:亲属、性别、地域、阶级等被采用来组合他们的各种团体,配合他们人和人的行为。但是在各种原则中,社龄却占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我可以简略地在这里比较一下各种原则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