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0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史研究中史学与经济学方法的异与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圣民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评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周建波也出席并参与了讨论。本次讲座为“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系列活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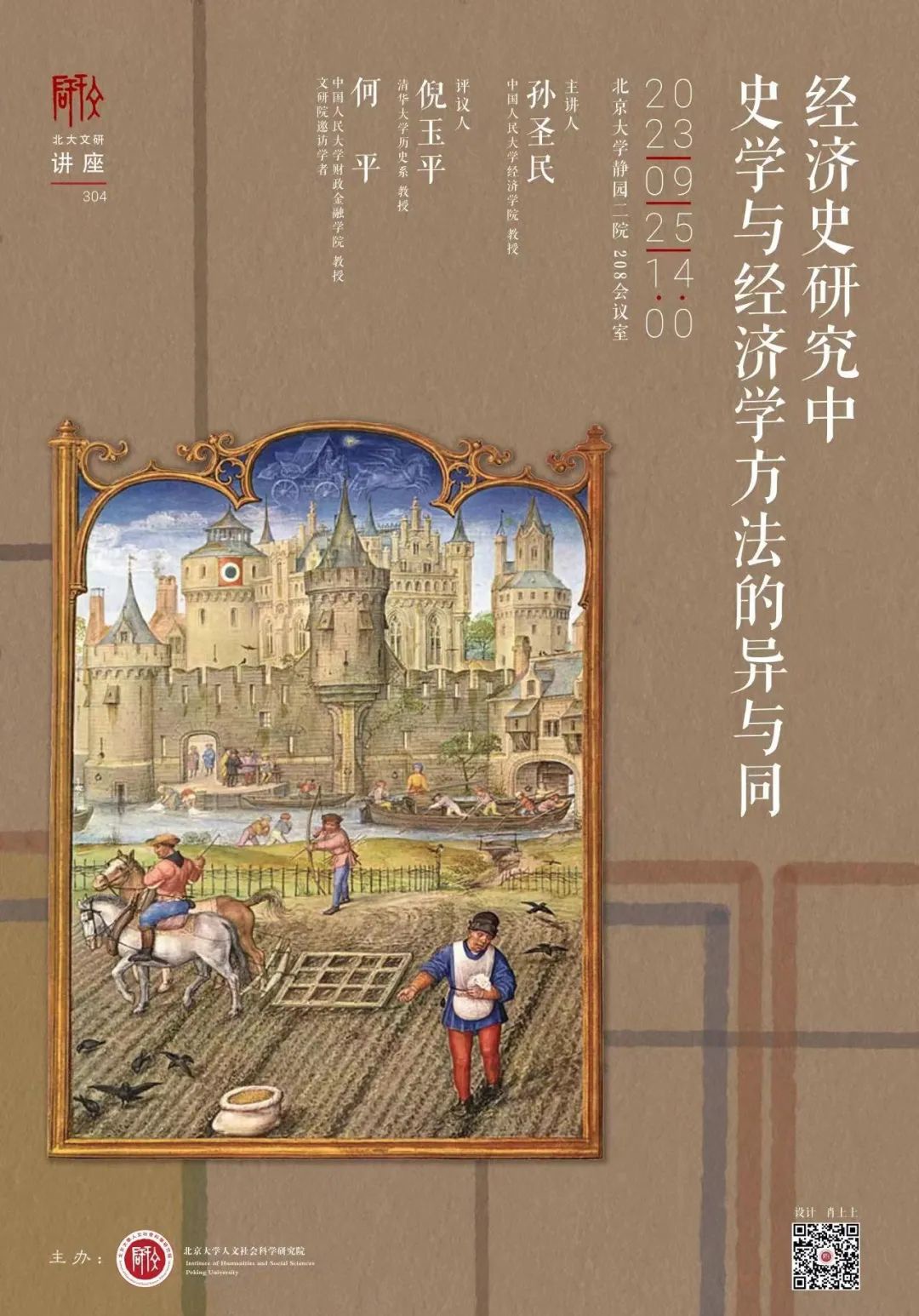
讲座伊始,孙圣民老师以事实引入: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两种范式,一种偏重历史学方法,注重文献诠释和史料考证;一种偏重经济学方法,注重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一直以来,经济史学家对于后者的使用持有异议,批评者认为,相关研究过窄地关注某些特定的制度,以及太过专注于量化,使得学者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及其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识。经济学方法的经济史研究受到的这种批评,不是中国经济史领域特有的,也存在于海外相关经济史研究中。
对两种研究方法,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都进行了诸多反思。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的经济学研究相比,存在“复现结果困难”的特殊性,这导致其不易在其他地域得到类似结论,也产生了可能汇报虚假显著性的问题。另外,受限于数据和技术,经济学范式下的分析往往压缩了历史。更多的批评和反思来自历史学等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认为,此类的一些研究经过复杂实证技巧所获得的结论,往往是证明史学家眼中或众所周知的共识,研究重心仍在证实上而非历史本身。在进入讲座的主要部分之前,孙圣民老师引用了一句话:“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

▴
傅衣凌先生(1911-1988)
我国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奠基人、著名明清史学家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孙圣民老师介绍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求同存异。从事人类社会的研究活动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方法,“通常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客观主义的或称实证主义的观点,和主观主义的或称解释主义的观点。”马克斯·韦伯在其“理解社会学”中提出了一种“存在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折中态度,既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又强调主观理解的作用”,这一点对经济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采取折中的态度,可以保持经济史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多元化。
从实证主义的线索看,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自古就有考据和实证的传统,这也成为近代西学得以落地生根的基础。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传播,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也获得了广泛关注,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范式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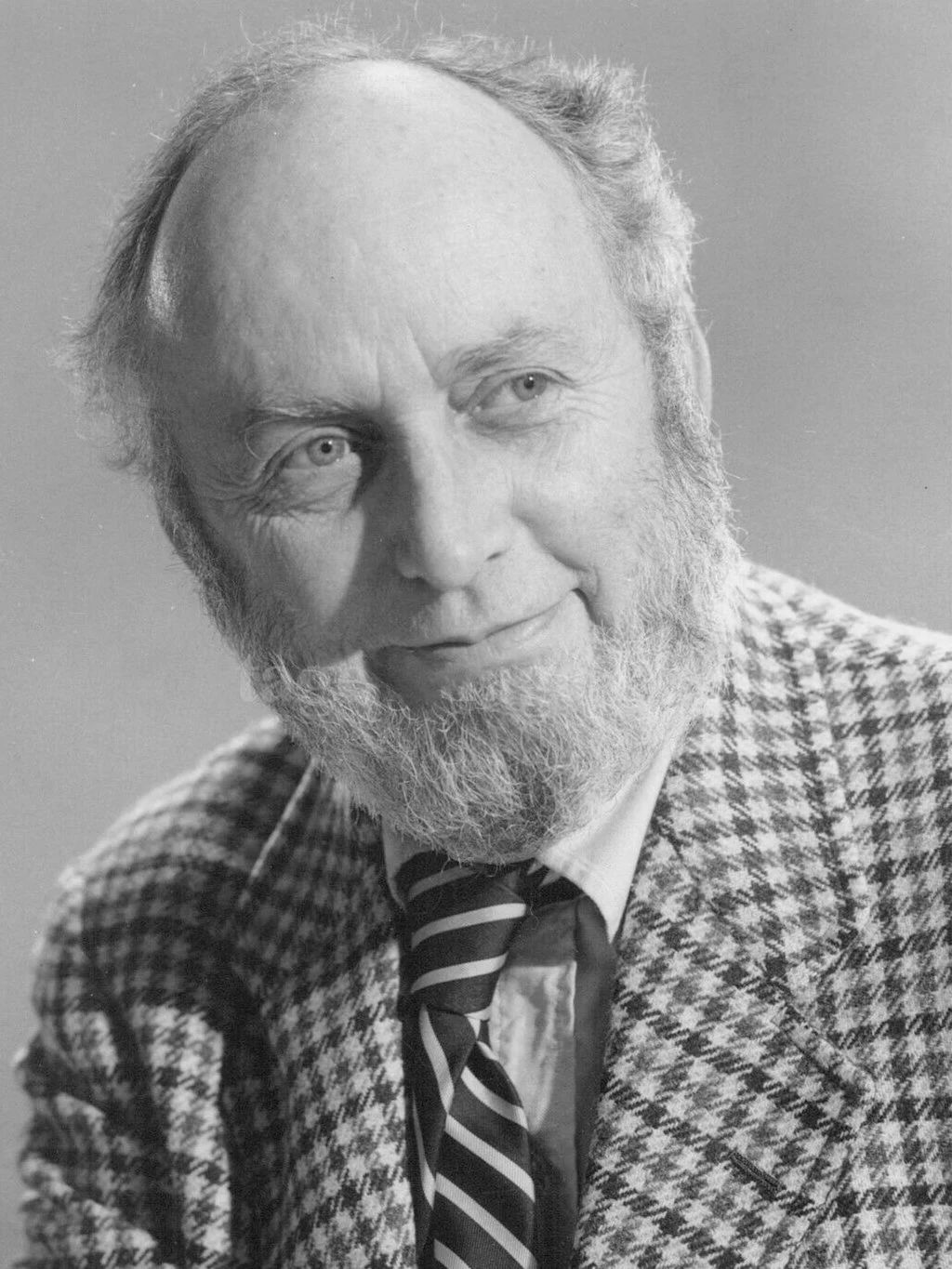
▴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20-2015
诚然,实证主义也存在诸多缺陷,这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无论是以经济学还是历史学范式开展的经济史研究,都无法绕开对大量经验证据的收集与归纳,只不过在前者的范畴中往往表现为数据形式,而后者则呈现为文物、文献等各种形式的史料。然而,在有限时空范围内获取的证据必定是不完备的,这来源于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以及学者本身在证据收集时的选择偏误,这时时动摇着实证主义者结论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实证主义者为了避免受到个案、反例的质疑,尽可能缩小论题的范围,以便穷尽例证。近年来这种在历史学界广受争议的“碎片化”之说,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时空局限性。经济学尝试改进实证主义,理性下的归纳演绎主打的是逻辑严谨,将结论普遍性置身在概率论和数学科学的保护之下,提高归纳完备性、突破时空局限。主要表现为计量分析和数理模型的并用,其中前者依循实证主义的归纳路径,从经济事实中提取或证实假说;后者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总体框架下展开逻辑演绎,实现假说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化,这也是目前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常见模式。由于追求科学性和普遍性,导致经济学研究更侧重证实过程和技术细节。归纳与演绎的功用多是负责证明,触发灵感并不是其强项。欠缺思想和观点创新,也是当前经济学界进行经济史研究时存在的问题。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思想和观点创新都是难点,也是追求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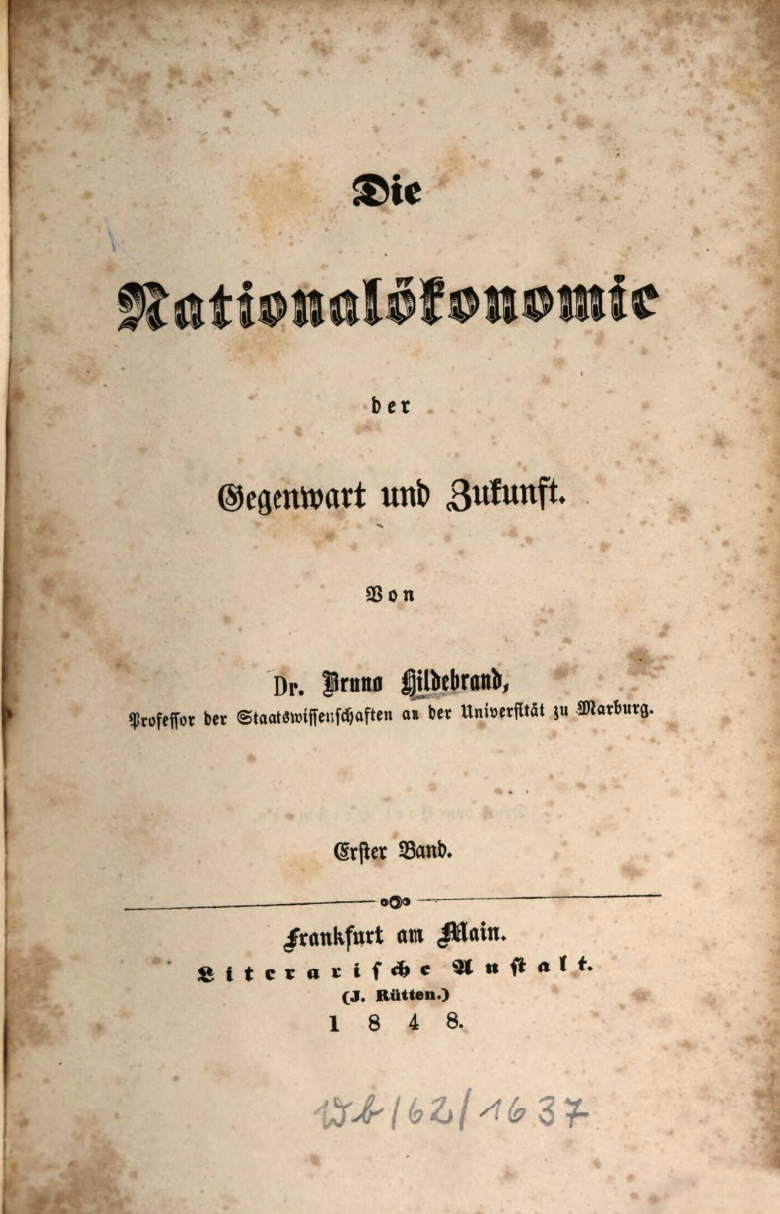
▴
布鲁诺·希尔布兰德《当前和未来的国民经济学》书影
讲座第二部分,孙圣民老师就如何看待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局限、经济学科学性的核心是趋势律以及体现经济学趋势律的分析方法展开讨论。首先,历史学和伦理学出身,使经济学天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气质。其次,经济学科学性的核心是趋势律。再次,就体现经济学趋势律的分析方法,孙老师作了进一步的介绍。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分别归属于经验归纳与抽象演绎,从方法论来看,归纳是不完备的,演绎并不产生新知识。但无论计量经济学的归纳框架,还是数理经济学所代表的演绎框架,都是判决工具而非真理,二者的相互配合十分必要。趋势律及其分析方法,是知识积累的有效方法,也是学术交流的科学工具。
正所谓“史无定法”,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可以用在经济史研究中,选择数据证明或历史叙事,既是方法论的要求,也是学术共同体对话的需要。我们允许批评的存在,同时也无法完全杜绝学术研究中的主观性。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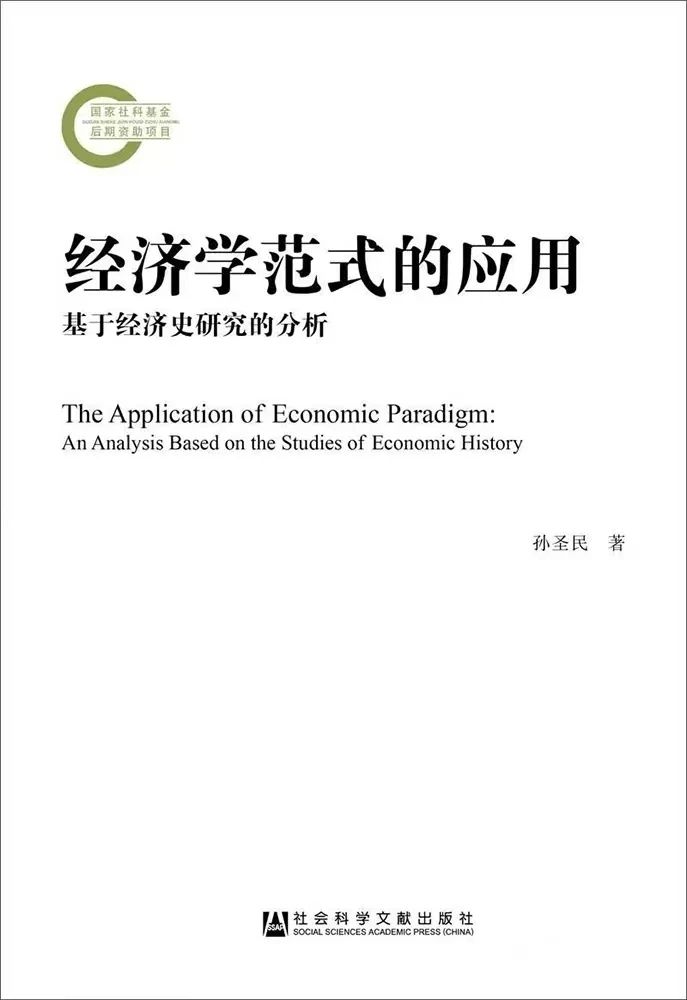
▴
孙圣民《经济学范式的应用:基于经济史研究的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
最后,孙圣民老师讨论了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主要有三方面的体现:理解历史,理解经济学和理解当代结果。孙圣民老师在具体阐述了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后,进一步总结和思考,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跨专业合作,以期产生创新性研究。与历史学家合作,可以弥补经济学家在史料知识和史学观点上的不足,史学家也应该了解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新方法。从知识进步的方式看,从每个学科发展的进程看,从一个学者的成长周期来看,创新性研究都是概率事件。方法上的摩擦和磨合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有效的交流、沟通与合作,可以提高经济史研究创新的概率。
评议环节
评议环节中,倪玉平老师首先发言。其一,他认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谈及经济史的方法论时,都不应过于悲观,而是应该从对方的研究中吸取养分,有些话题因为研究范式和关注重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争论的必要。各个学科对于历史的理解类似盲人摸象,即使大家的认知都是片面的,也在共同推动着历史研究的发展,以期在未来刻画出“大象的全貌”。
其二,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是很复杂的,因此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提炼出单线程的因果关系。历史学是求真的,而非追求模型的完备性或者逻辑的自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历史学研究中常伴随主观感受,因此问题的发现和剖析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感”。但是有些历史问题并非历史学家可以回答的,例如“清代经济是停滞还是发展”这一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的数据计算和分析,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跨界合作往往是难得的。
其三,倪老师认为,孙老师在讲座中谈及的更多是经济学视角下的方法论反思,偏重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而非历史学的经济史。经济史不是谁的私有财产,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经济学,它是独立的开放的存在,应该作为交叉学科发展。过分追求整齐划一可能会带来教条主义,反而约束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接下来,何平老师就本场讲座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点评。在他看来,以下三点需要注意。第一,西方学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阵地的美国学者,面对他们所研究的早期经济史材料时,基本不存在语言问题。而在中国,经济学阵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民国前的经济史研究者,很少有能力阅读和使用古代及近代原始文献,大多引用二手材料。这样,从经济现象抽象出来的经济学理论说明,由于缺乏可信材料的支持,就失去了依托,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让人心生疑虑。他们与从历史学视角出发的经济史研究者之间,存在认识出发点的错位。

▴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audia Goldin
第二,历史学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的经济史,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历史学对于事实和影响因素的认定,是经济史研究中计量分析的基础,只有变量确实可信更加合理,才能进行有效的计量研究。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方面,除了单纯的原始文献的文字识读之外,更重要的,对许多问题的解读需要职业经验甚至生活经验,以及社会阅历。初学者没有年长学者的合作和引导,不可能进行科学合理的变量选取和合乎人类活动规律的文本解读。第三,历史学的经济史,也要学会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像1902年经济学出现学科独立以前那样进行笼统的文学描述,应当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相关知识和理论框架,对历史时期的经济事实和意义进行科学的解读。我们不排除可能出现有真知灼见的、单纯致力经济史方法的研究者和评论家,但从研究实践和学术发展来看,历史系和经济系的学生培养,必须破除研究者原有的藩篱,既具备原始文献的直接解读能力,也熟稔经济学基本概念、理论框架以及计量方法的理解和应用。理想的情况是,如同戈尔丁那样,经济史家也应当是经济学家!(注:戈尔丁[Claudia Goldin]最为人所知的是她关于美国经济中女性角色的历史研究。在这次讲座的两周后,当地时间2023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
最后,何平教授认为孙圣民老师的研究意义重大。方法论层次上的理论思辨是相对独立的命题,这一研究需要敏锐的捕捉力、品鉴力和洞察力,是极为难得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