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27)”。文研院特邀教授、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因(John Keane)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约翰·基因(John Keane)
本场讲座中,约翰·基恩教授主要介绍卡尔·施密特对自由主义议会的看法和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缺陷和议会未来改革的方向。讲座伊始,他首先介绍了自由主义走向没落的背景以及施密特的个人经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逐渐兴起,自由主义议会很难再吸引人们的兴趣,许多曾经坚定支持议会精神的人也开始质疑代议制民主的效率。而卡尔·施密特则是欧洲这一时期最精明、最具争议的议会评论家。施密特曾任职于纳粹政府,在此期间,他担任过“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的主席和“德国法学家日报”主编,参与了焚烧犹太书籍等活动,并为希特勒的政治屠杀进行辩护。但同时,他对议会制度的研究直指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质疑议会是否有协调二者的能力——研究涵盖了道德、政治、人性、国家主权、独裁制度以及民主的未来发展等多个方面。因此,施密特的作品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次讲座中,约翰·基恩教授从多个方面对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思想进行论述。

卡尔施密特(1888-1985)
一、自由主义
施密特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其反政治特质,即对国家权力的反感。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仅仅是为了提高公民社会内部的个人自由。因此,政治家们的任何特权都是邪恶和不公正的,都会被自由主义指责为暴政。与边沁、基佐、霍布斯等人所主张的在内部统治、殖民扩张、军事发展等方面强有力的国家不同,施密特强调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和言论自由。公民社会中言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存在不仅能够中和国家过于庞大的权力,有时甚至会使后者变得多余——社会力量的均衡也因政治监管的缺失而得以存在。
二、议会
在此基础上,施密特指出,议会是保障国家与公民社会平衡的关键机制。议会应当公开、公正、平和地解决公民间的分歧,并且使国家机构和行政部门按照法律规范履行职责。施密特认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谈判和妥协不是议会的专有特征,这些过程也存在于其他地方,例如公司或者政党的会议上。因此,议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公开和讨论。它假定人们都愿意被其他观点说服,同时保证自己的观点不受效忠对象或私利左右。为了实现这两个原则,议会程序不应被限制;议员们应当享有言论自由和豁免权,同时不受党派或选民的控制,而是服从自己的良知。在这个意义上,议会可被视为公开的政府,议员们要接受新闻的公开报道,并被置身于公民的注视下;而公民则可通过自由媒体了解真相,并向议会传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
三、议会的精神危机
施密特关于议会时代自由主义的论述是简短的,但他依然指出了其在二十世纪面对的深刻危机。在他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议会及其理想正在逐渐消亡,它或许会存活下来,但如同君主制一样变得残缺不全。施密特认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导致议会产生危机的根源。随着民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政府不得不扩大其权力范围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例如工作权和生活权。然而,这种“行动的民主”模糊了国家和社会的界限,从而改变了十九世纪非干涉主义宪政国家的趋势,使公开的议会过程被大众民主(特别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破坏。自此,议会变得混乱而平庸,并成为党派实现特定政治或经济目的的工具。据施密特解释,因为议会和民主的基本原则相互矛盾,“议会民主”这个混合词是不可能存在的。民主决定公民享有决定和修改法律的最终权力,国家可以并且应当与民众的意愿保持一致。因此,议会乃至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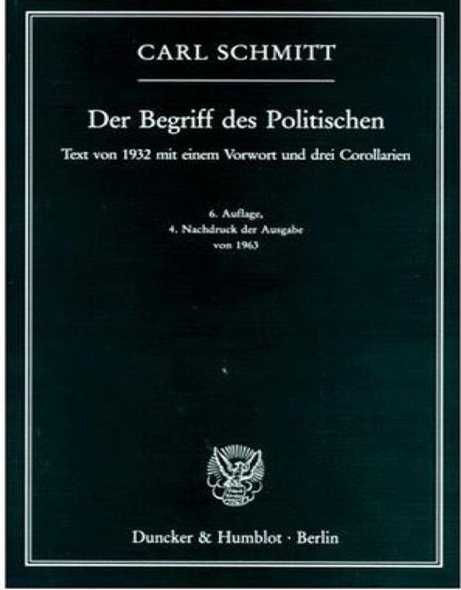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书影(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四、政治
简而言之,施密特的政治观点就是反对他所谓的“人类学乐观主义”。政治世界是多元化的,伴有自私、背叛、公开分歧、暴力冲突等行为。施密特认为,政治的精髓就在于“朋友”和“敌人”间的紧张关系。真正的政治家可以分辨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而那些无法做出区分的人会被敌人玩弄于掌中。在此基础上,他引申出五点启示:首先,所有的政治概念、图像和术语都具有争论的意义,诸如国家、共和国、社会、阶级等等。同样的单词在敌对情况下可以同时作为信号、密码甚至武器。其次,领土国家是政治的表现,而非来源。战争同样也是政治的表现,而非其“其它方式的延续”。第三,国家定义了“朋友”和“敌人”,并保护它的公民不受后者侵害。第四,道德是由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定义的,而政治则描述了不同领域中敌友的竞争强度。最后,暴力或战争会一直存在,即使是公开的议会讨论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有政治智慧的人必须牢记,他们的对手总有实施暴力的可能性,议会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五、独裁统治
施密特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谁在危急时刻享有决定权,而只有精明、意志坚定和武装良好的政治领导层才能决定这类危机问题。因此,最终决定权既不在议会,也不在宪法及法律中,而是在压力下行使决策权的个人或小群体。施密特以此为基础划分了两种不同的主权领导形式:其一是“主权专政”,它力图推翻旧政,并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政治法律秩序。主权专政是短暂的,它只有在民众能够自由地表达其意志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才能持久下去。其二是“委员会专政”,它并不反对现有宪政秩序,只是希望克服危机并重建常态。虽然委员会是暂时的,但它依然要尽可能强大。它需要拥有采取一切措施恢复秩序的权力,甚至包括暂停宪法的部分内容。在施密特看来,专政独裁对于解决危机是必要的。在紧急情况下,公民必须敬畏国家,允许专政政权取代议会进行决定。施密特的这种观点虽然确保了国家权力和行政官僚机关的统治地位,但也会导致议会的影响力下降,同时放大反民主运动和专制政党的吸引力。另外,施密特没有意识到当独裁者面临着反对派的压力和各种诱惑时,临时独裁总是有成为永久制度的倾向。宪法,即使是由独裁政府制定的,也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宪法修正案(包括旨在恢复社会和政治多元化的宪法改革)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六、自由主义时代前的议会
施密特忽视了议会在自由主义时代来临之前的历史。在议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贵族、神职人员、农民和市民为代表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议会协调其与世袭君主间的关系,捍卫自己的权力。同时,君主也会为了寻求意见而召集议会。因此,早期的欧洲议会绝不是软弱或间歇性的,而是实际上的权力轴心,它参与到立法、行政和外交政策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忽视了自由主义议会在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施密特关于议会制兴起与衰落的理论很难有说服力。早期议会很少会通过明确的政治理论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而是将自己的要求建立在古老的习俗和特权之上。施密特关于议会是质疑政权的始作俑者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早期人们通过议会在环境破坏、强制征兵、农民过度劳动等一系列问题上争取自己的权力,甚至抵制君主的决定。因此,议会不仅是服务了特殊利益阶层(比如自由资产阶级),更是平衡了公民社会与独裁政府的关系,从而捍卫自由和宪政精神。
七、议会改革
施密特没有考虑到二十世纪议会民主改革的可能性,因此,他得出了议会必然衰落的结论。但是,议会现在面临的危机仍然值得我们进行分析。首先,议会通常由组织良好的政党控制(特别是议会高层),这不仅体现在对议会程序的直接控制上,还存在于非正式关系的影响中,比如行政人员与议会议员的私人交往。由于这种做法,下议院几乎沦为了咨询机构。其次,传统的议会程序或正式的宪法设计正在逐步加强纪律和行政权力对议会的控制。比如,政府通过确定优先级间接确定议会议程,并防止议会在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组织辩论或通过法案。第三,大众传媒对政党领导和公民社会的报道降低了议会的权威,加强了政治领袖领导权,同时将政治的重点从议会转移到议会外领域。此外,政府不受限地扩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许多秘密机构的出现让议会无法就关键问题作出决定。最后,二十世纪下半叶,北约、联合国等跨国或超国家组织开始迅速发展。这些组织的存在将决策权转移出了议会,并且改变了政府原本应当坚定的谈判立场,从而阻碍议会“干涉”超国家的谈判。
面对这些危机,约翰·基恩教授对未来的议会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如果人们能够承认政党作用的局限性,政党对议会的过度控制也会随之减弱。其次,由议会多数党或者联盟定期选举部长,可以削弱总理及其他行政权力对议会的干预。灵活的议会召集时间、地点,舒适的办公环境,加之议员们的平等发言权(特别是在紧急事务上的话语权)都有助于议会克服当前面临的危机。这些变化反过来也会改变议会的媒体形象,加深民众对议会的了解。更进一步的,民众甚至可以通过常设委员会参与并监督议会和国家机器。最后,议会应当设立更强大的常务委员会对国家在超国家机构中的行为进行协调和监督,这不仅有利于恢复议会权威,更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