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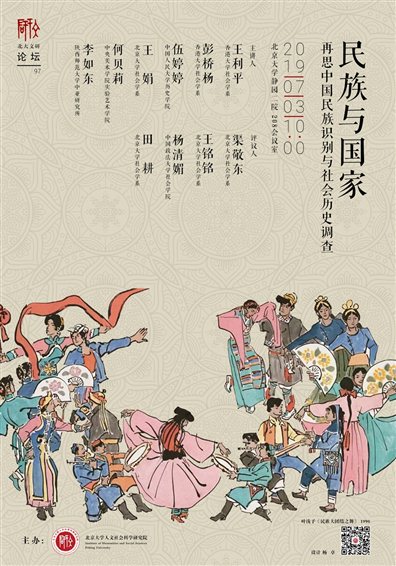
2019年7月3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族与国家:再思中国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利平、博士彭桥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伍婷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何贝莉,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李如东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教授王铭铭、助理教授田耕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清媚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教授马戎、教师菅志祥出席并参与讨论。
伍婷婷老师首先就本次论坛作主旨说明。作为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1949年所发生的重要变革不但在当时产生了“新知”,而且对当今的学术讨论乃至民间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学术思想的更替往往并非断崖式的转变,而需要一个连续的过程。为了更加真实地分析1949年前后的转变,并对当下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加以反思,如今的学者有必要以去特殊化的态度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下,对当时所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再次进行探讨。王铭铭教授补充,近代以来,所有帝国与殖民化国家都展开过大规模的民族志调查,并为此建立专业研究机构。在此背景下,当时参与民族调查与研究的不仅有历史学等传统学科,也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本次论坛将主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识别进行探讨。
一、反思民族识别:广西争议少数民族的划定
王利平老师与其学生彭桥杨带来了本次论坛的第一场报告,主题为“反思民族识别:广西争议少数民族的划定”。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是以1950年代起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为基础的。而建国前,岭南一带所存在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则经历了被识别与归类的过程,被官方以附近较大的少数民族作为参照进行比对,从而被并入较大少数民族,或作为单一民族获得独立席位。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是以1950年代起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为基础的。而建国前,岭南一带所存在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则经历了被识别与归类的过程,被官方以附近较大的少数民族作为参照进行比对,从而被并入较大少数民族,或作为单一民族获得独立席位。
关于这一过程,学界有“国家视角”与“批判国家视角”两种理解,前者认为少数民族的构建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后者则强调前线学者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对该过程的影响。从这一分歧出发,王利平老师讲述了三个争议族群的案例:龙胜“伶人”、金龙“傣人”和环江“毛难人”。1958年的文件中,前二者的归属分别被确定为苗族与壮族,“毛难人”则被定为单一民族。王利平老师指出,在认定某一民族是否为“少数民族”的过程中,语言是重要依据,如“毛难人”因拥有独立、完整的语言体系,首先被承认为独立民族;同时,与周遭民族的关系也影响着独立民族身份的立或废,如龙胜的“伶人”语言与苗人相似,故随后者共同被归入苗族。这一识别方式也会带来争议,如金龙“傣人”并不满于自身被归入壮族的结果,但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认同是在和“权威”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

渠敬东教授对此作出了点评。他指出,民族作为现代概念,与现代国家的秩序、主权、自我定位等均有密切关联,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西方的现代秩序并不是纯然借助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形成的。进一步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下区别于西欧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局限于从帝国模式中寻求答案。此外,民族识别运动并非单纯由国家意志所主导,而是由国家与知识分子共同进行的、受到整个民国年间学术体系积累影响的运动,对当时的国家秩序与建设影响深远,需要以文化的方式理解与评价。
二、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史观”之形成与演变的社会学考察
王娟老师带来第二场报告,主题为“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史观’之形成与演变的社会学考察”。进入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接受中国并非天下中心这一事实,并将中国转型为“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这一似有内在矛盾的概念?汉本位思想在中国具有连续性,而到了近代,传统思想体系中不同维度的变迁则具有不均衡性。以此为背景,王娟老师将近代以来的民族叙事分为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清末革命背景下的“民族史”方案。此时,专门的民族史尚未形成。在清末革命思潮与日本史学的影响下,虽然出现了新兴的、以民族国家为书写对象的国家史,但其内容与汉族史仍高度重合。这一时期的国家史大多涉及有关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讨论,而历史节点的划分则以汉族的兴衰或其与异族的竞争态势为标准。其中,最早将“民族”二字列于标题的是两部革命派的作品,即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与陶成章的《中国民族势力消长史》。第二种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专门的民族史。这种叙事方案可以追溯至梁启超1906年与1922年专论民族史的文章,其中提出应超越“主权上主族客族之嬗代”的视角,而以“混合”、“同化”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流变。王娟老师指出,梁启超所言“同化”仍旧以汉本位作为立场,其纲领在于民族混合与汉化,但同前一阶段叙事所强调的的民族竞争与汉族兴衰相比差别很大。第三种是唯物史观下的民族史叙事。吕思勉在《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中重新将斗争的视角带回了民族史叙事,但与清末叙事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唯物史观下的叙事把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其所言的斗争可分为两种: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各民族被压迫人民反抗异民族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一观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娟老师进一步指出,这一理念的进一步延伸,即建国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共有55本,每个少数民族均占其一,在形式上体现了平等,但同时也应看到,调查中对各民族进行的社会发展阶段区分仍然带有进化意义上的等级性特征。而三种叙事模式的内在关联,则是“汉本位”这一立场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三、书写白族族性:从民家到白族的汉化问题
伍婷婷老师带来了第三场报告——“书写白族族性:从民家到白族的汉化问题”。1930至1940年代,对于白族,即当时所称的“民家”,存在着历史、民族志与语言三类研究。历史研究的兴趣在于追溯白族的族源,其共同特征有二:认为民家的血统具有混血性,并通过民家文化中汉化特征古今相似性的对照来建立民家的族源谱系。民族志方面,费子智(C.P.Fitzgerald)曾在其作品中指出,民家的独特性体现在其文化特征中,如信仰、风俗、节日等,但同样有人批评道,费子智并未阐明民家、汉人社会与其他非汉人群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因而并不彻底。同样,民家的语言也具备许多汉族特征。总之,白族在当时被认为是汉化较深的族群。
那么,为何白族仍在建国后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被认定为非汉人群?其身份特征又应如何界定呢?伍婷婷老师指出,通过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查与讨论,《白族简史》验证了汉族对白族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及白族的民族混溶性。这种思路带来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白族简史》并不纯粹讲述白族的历史,另一方面,《白族简史》在事实上论证了白族与汉族社会发展相似性形成的历史过程。 最终,白族成为官方识别并指定的民族身份后,加之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其民族意识与自我认同感得到了增强的机会。但仍应认识到,汉化特征始终是白族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汉族与白族的关系则是在互动中彼此界定的。 最终,白族成为官方识别并指定的民族身份后,加之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其民族意识与自我认同感得到了增强的机会。但仍应认识到,汉化特征始终是白族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汉族与白族的关系则是在互动中彼此界定的。
点评中,田耕老师指出,白族于1954年被确定为独立民族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其背后的动力与机制是值得关注的。此外,在对多民族汇集区进行分析时,可将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相结合,注意到非汉族群彼此之间的转化、组合与合并空间。菅志祥老师补充道,探讨民家为何未被识别为汉人这一问题时,可以将其在国家政府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纳税身份等纳入考虑,从而为有关历史关系与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分析提供思路。
四、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宗教生活
何贝莉老师带来了主题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宗教生活”的第四场报告。报告核心关注如下问题:藏族宗教生活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体现形式是什么,又因为什么原因而未得到充分展开? 有关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可追溯至1950年代初,主要进展集中于1956年至1964年,并于此后进入尾声,直至1999年结束。其中,1956年至1958年为主体时期的第一阶段,学术思考活跃、接近原初设想;1958年至1964年为第二阶段,其间民族学全面政治化,转为以政治任务为导向,调查人员也经历了较大换血。 有关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可追溯至1950年代初,主要进展集中于1956年至1964年,并于此后进入尾声,直至1999年结束。其中,1956年至1958年为主体时期的第一阶段,学术思考活跃、接近原初设想;1958年至1964年为第二阶段,其间民族学全面政治化,转为以政治任务为导向,调查人员也经历了较大换血。
与调查开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报告文本的内容也侧重不同。第二阶段,即以1958年至1964年的调查内容为基础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宗教”内容已被隐去,而其余经济、政治与法律、生活习俗与文艺等内容则仍可以与最初的“封建社会调查提纲”相互对应。李有义所描述的西藏土地制度下,拥有土地最高占有权的政府处在土地关系的顶端,剥削阶级——寺庙与贵族占据土地管理与经营权,实际使用土地的农牧民、农奴则属于被剥削阶级。这一结构中,政府角色可进一步复杂化,对中央政权与行政机构加以区分。但关键在于,这一结构中并未体现寺庙的神圣性,也未对平民与普通喇嘛的联系与流动加以分析,而仅描述了去宗教化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分析《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可进一步发现,关于寺庙的文本有三种形态:将寺院作为社会组织纳入讨论;以寺庙为线索叙述庄园的土地占有;运用马列主义考察并撰述寺庙的“整体性社会事实”。此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宗教信仰的内容则均为间接提及,散见于医疗、宗教支出及自然灾害等其他领域类目,呈现为“宗教”的外延部分。

五、共同体与阶级:《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阿吾勒”及其知识建构过程之考察
李如东老师因通过委托代读报告的方式与会,主题是“共同体与阶级:《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阿吾勒’及其知识建构过程之考察”。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提纲,可以发现当时国内的研究者存在分歧:应该将哈萨克社会定义为原始的共同体社会,还是封建的阶级社会?报告以这一张力为线索进行了挖掘。
阿吾勒是游牧民族哈萨克族基于父系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其社会组织形态在夏季完善,冬季则离散在各个家庭中。根据1950年至1953年的报告,阿吾勒内部存在事实上的贫富对立、财产集中与无偿劳动,但并不意味着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为无偿劳动是嵌入在共同体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核心工作在于考察少数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并从中发现阶级关系。但人类学对游牧民族的认识偏重于“平等主义的共同体”,同时,国内少数民族内部亦无明显阶级属性。因此,调查者需要从中“发现”阶级。 1956年的调查中,哈萨克社会的阶级问题成为了核心问题,其封建特征在考察中越发被彰显出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即阿吾勒被认定为具有阶级属性的封建经济组织,其生计传统亦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为公社所借用。阶级化趋势之下,合作化运动改变了牧区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组织形态,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强调关系平等与合作互助,牧民也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简言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结果成为了社会改造的依据,并加剧了社会变迁。 1956年的调查中,哈萨克社会的阶级问题成为了核心问题,其封建特征在考察中越发被彰显出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即阿吾勒被认定为具有阶级属性的封建经济组织,其生计传统亦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为公社所借用。阶级化趋势之下,合作化运动改变了牧区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组织形态,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强调关系平等与合作互助,牧民也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简言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结果成为了社会改造的依据,并加剧了社会变迁。
王铭铭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民族识别涉及两个关键概念:分类与关系。进行研究时,不应从 开始就将研究对象视作预先设定的民族实体,而应“把人当成人”来从实求知。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1976年《人类学在科学中的地位:西方和苏联的看法》会议中所指出的,“ethnography”的“ethno”在西方与苏联有着不同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着眼于被研究的社会内部看待问题的方式,苏联模式则持政府视角对民族进行先入为主的分类,并进一步考察其起源。后者则恰恰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存在深刻影响。此外,苏联人类学家通常把研究归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结论,但对亲属制度这类既具备经济属性、又涵盖社会与文化的组织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又难以展开。总之,在千差万别的国家形态之中,不同国家均需关注的共同议题,正是对其所容纳之人口的分类、控制与整合。这正是本次论坛带来的启发与学习之处。 开始就将研究对象视作预先设定的民族实体,而应“把人当成人”来从实求知。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1976年《人类学在科学中的地位:西方和苏联的看法》会议中所指出的,“ethnography”的“ethno”在西方与苏联有着不同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着眼于被研究的社会内部看待问题的方式,苏联模式则持政府视角对民族进行先入为主的分类,并进一步考察其起源。后者则恰恰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存在深刻影响。此外,苏联人类学家通常把研究归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结论,但对亲属制度这类既具备经济属性、又涵盖社会与文化的组织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又难以展开。总之,在千差万别的国家形态之中,不同国家均需关注的共同议题,正是对其所容纳之人口的分类、控制与整合。这正是本次论坛带来的启发与学习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