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1月28日(周二)19:00,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天岳副教授将主讲未名学者讲座第26讲。主题为“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吴天岳副教授的文章《〈儿童法案〉中的宗教与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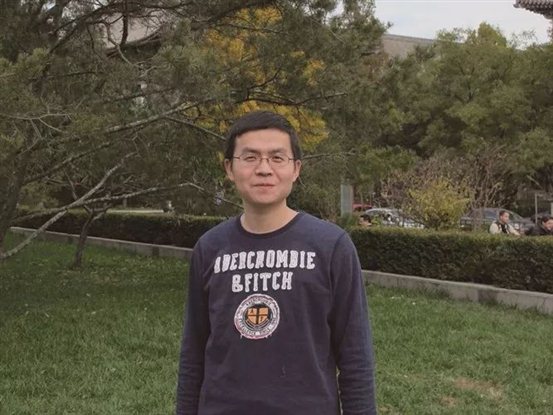
《儿童法案》中的宗教与身体
吴天岳
提要:宗教和法律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2014年的小说《儿童法案》的核心论题。本文从身体和宗教的关系入手,重新考量《儿童法案》的核心案例所带来的理论挑战。通过展示身体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其与自我的亲密性等核心特征,扼要梳理了西方世界建构濒死身体的主导话语从宗教到医学再到法律的历史,由此揭示当代有关宗教与身体的研究中被不正当地忽视的一个基础问题: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宗教是否还有权构建我们的身体观?
关键词:身体、世俗、个人福祉
宗教和法律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2014年的小说《儿童法案》的核心论题。[1]小说的主人公菲奥娜·迈耶是伦敦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她所处理的来自家事法庭的案子往往和当事人的宗教信仰纠缠在一起:恪守清规的摩洛哥穆斯林父亲试图从在大学任教的前妻手中抢夺女儿的抚养权;来自传统犹太教社区的一对夫妇当庭激辩,两个女儿该进严守教规的犹太女校还是相对开放的男女混合犹太中学;信仰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家庭的连体婴儿面临绝境:如果不施行分离手术,两个婴儿都将衰竭而死,而施行手术挽救其中一个则要切断另一个的动脉,几近谋杀……。
菲奥娜需要在超自然信仰和世俗道德的对峙中给出符合法律原则的判决,其中最让她和读者纠结的案件则涉及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少年亚当·亨利,他必须接受一系列会对骨髓和身体免疫系统造成损害从而使他不能自我造血的治疗,如果不输血就只能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然而,亚当一家的宗教信仰却成了他接受治疗的巨大障碍。亚当的父母都曾受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感召,在新的信仰中找到了新生,成为忠实的信徒,并在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中将亚当抚养长大。

麦克尤恩
耶和华见证人是成立于1870年的新兴基督教团体,他们不接受传统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学说,强调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耶稣作为神的独生子不具备神的位格,但被立为即将来临的天国的君王。在尘世间重建天国,被耶和华见证人看作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唯一希望。耶和华见证人主要通过定期发表的官方杂志《守望台》(Watch Tower)来传布和发展他们的基本教义,其内容涵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诸多另类(如果不算异端的话)教义中,拒绝接受输血可能是最为世人所知的一条。[2]耶和华见证人视血液为生命的源泉,它是造物主神圣的馈赠。将自己的血同动物的或他人的血相混,是对生命这一神圣馈赠的亵渎。从1944年起,他们就认为《圣经》中有关带血的肉的禁戒同样适用于输血,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等血液主要成分制成的药品。[3]而在1961年出版的官方文献中,他们不仅将自愿接受输血看作脱离教会的行为,而且直接警告:“它(案:指输血疗法)可能带来生命当下非常短暂的延长,但其代价是一个虔敬基督徒的永恒生命。”[4]
小说中的亚当即将年满18岁,也就是英国法定的能够决定自己接受或者拒绝救命治疗的年龄。亚当天性敏感,才智超群。在教会长大的他熟读《圣经》,也熟悉以上有关输血的禁令及其神学理由,他可以清晰地表述他的抉择理由,也清楚自己这一致命决定的后果。甚至作为法官的菲奥娜也承认:“他对宗教原则了然于胸,并且有着超出他年龄的成熟与表达能力。”[5]亚当以殉道般的激情下定决心,要坚守已有的信仰,直面即将来临的惨烈死亡。然而,医院方面并不认可亚当的选择,他们诉诸法律,寻求法庭的指令来合法地给这个重病的男孩输血,哪怕这违背他本人的意愿。
菲奥娜一如既往地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亚当及其家人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尽管它偏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同时,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亚当根据自己的意愿所作出的选择也应得到尊重。[6]因为个体的意志自由常常被看作现代社会的精神柱石和道德实践的根基。与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内容不同,接受某种特定宗教信仰的自由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核心要素。此外,英国的司法实践也肯定所谓的“吉利克资质(Gillick Competence)”,认为16岁以下的儿童,“在达到心智成熟,能充分理解议题的前提下,有权决定自身的治疗方案。”[7]另一方面,在法律上亚当仍是未成年人,在是否拒绝救命的治疗一事上并不享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因为当选择危及其根本福祉时,亚当的父母或法庭有权推翻他根据吉利克资质所做出的选择。[8]在此案中,他的命运需要通过法律来决定。同时,医院的要求也表达出世俗社会几乎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直觉:如有可能,应当竭尽全力去挽救一个人的肉体生命。当这里的对象涉及一个未成年人时,现代法律更有必要介入,以保障孩童的权利不受包括父母在内的外界侵犯。菲奥娜自己就坚信:“在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9]
菲奥娜最终选择通过法律干预来挽救亚当的生命,她所依据的正是这本小说标题来源的《儿童法案》。根据这部1989年通过的法案,在涉及儿童抚养的问题上,儿童本人的福祉(Welfare)应当成为司法裁断的优先标准。菲奥娜承认这里的福祉包括美好生活(well-being)和利益(interests),[10]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肉体生命,还应涵盖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包括经济与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美德、同情心、利他主义、人际关系、尊严、友爱等等。[11]菲奥娜之所以断定亚当的最大福祉在于肉体生命的延续,是因为她深信耶和华见证人这一“非黑即白的偏激世界观”深刻影响了亚当的心智,使他无法成为一个严格意义的独立个体,从而拥有决定自己道德命运的自由。简而言之,未成年人亚当的抉择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抉择,不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因此不应得到司法的保护。[12]
我们暂且悬置小说人物最终的命运。这个虚构案例包含着的复杂要素和内部张力,已经敞开了从不同视角深入反思的理论空间。
首先,我们可以继续谈论超自然信仰和世俗道德在塑造孩童心智上的冲突,正如小说作者在评述有关犹太女孩应该进什么样的学校的争论时所言,“这是在争夺她们的心灵。”[13]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当一种宗教信仰合法但与世俗社会主流价值存在冲突时,它可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合理合法地培育未成年人的心灵。我们如何在儿童的福祉中安放他/她可能拥有的另类信仰?或者一般地来说,个人福祉与其宗教信仰有何关联?
其次,这里所涉及的独立个体及其自由本身都是宏大而界定不明的概念。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它具体体现在一个行动主体是否有能力在和自己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相关的医疗事务上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能力被称之为“决断能力(decision-making capacity)”,它同理解、评判、推理、选择、情感等其他心智能力的关系,以及它在医疗和司法实践中的可判定性等问题,本身就是当代生命伦理学争议的重要话题。[14]
再次,从我们所关心的宗教实践维度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在什么意义上一个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儿童,能够具备上述决断能力,能够成长为一个法律和世俗道德所认可的独立个体,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决定自己的选择并为之承担责任的行为主体。菲奥娜对亚当道德自主性的否定似乎暗示了传统宗教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因为缺少自我批判和反思,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成熟的、独立的心灵。
最后,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去追问这里所隐藏的现代性问题。耶和华见证人对于由血液所产生的污染的道德恐惧,无疑表达出一种向尚未祛魅的前现代神秘世界的回归。就此而言,它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相关食物禁忌并没有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亚当在他即将成年时所面临的根本抉择,可以描述成前现代世界观和以世俗化为标志的现代世界观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见,作为法官的菲奥娜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现代性内部的冲突,即个体自决和社会保障一切儿童福祉尤其是其生存权这两条现代社会原则之间的冲突。[15]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福祉等概念一样含混空洞,缺乏明确的界定,被称之为现代的各价值要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并不打算直接刻画或澄清这些宏大概念,而是计划如本文的标题所预示的那样,从身体和宗教的关系入手,重新考量《儿童法案》的核心案例所带来的理论挑战。以上的讨论聚焦于宗教信念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忽略了亚当一案最直接的对象是他的身体和他的身体所承载的肉体生命:耶和华见证人所纠结的血液首先是身体的一部分,医疗事务中的决断能力所针对的对象无疑是身体及其疾病与康复,法官最后的判决也预设了对身体及其道德价值的肯定。在稍后的分析中我们还将展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在于它对身体的态度,尤其是通过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来重新规划我们的身体观。与此同时,身体因其独特的本体论地位,它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甚至比上述宏大概念还要隐晦不明,需要进一步的澄清。以下只是一些非常初步的尝试,其宗旨更多地在于展示我们所面对的理论难题的复杂性,而不是给出某种现成的答案。
那么,什么是身体呢?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工作定义或者初步描述来展开我们的思考。首先需要限定的是,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人的身体。它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正如一般辞书告诉我们的那样,它通常指的是我们的整个生理组织,是生命的物质承载者。与五官、手脚、内脏等具有明确功能分化的物质部分相比,身体这一概念突出的是我们的物质结构整体,它不能被化约为其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失去了某些构成部分之后仍然保持为我们的身体。作为整体的身体看起来仍然保持某些物质的、生理的或自然的特征,例如它经历生老病死的变化,它有性别之分,它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有病的。这一切使得身体可以成为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
然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史家却不遗余力地提醒我们,这种将身体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实体的自然主义想象只是一种迷思。人类的身体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莫斯注意到,人类都具有行走的能力,但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体在行走时却有着独特的姿态,以致于我们可以通过步态这一身体特征来识别一个人的社会身份。[16]以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则极力声张,即使是通常所谓自然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本身,尤其是它对我们的身体观的规范和约束效果,也不能脱离社会话语而得到理解。[17]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身体的理论反思要取消身体的自然特征,只是强调人的身体及其特征往往是在社会实践和具有社会性的话语体系中被构建出来的。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在反对输血疗法时,也会提到输血容易导致艾滋病、肝炎等疾病传染,以及排异性等生理不良反应。但这些医疗危险始终从属于血液污染对生命神圣性的道德威胁,并不构成其反对输血的实质理由。[18]
我们在此无意介入有关身体本质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进路之争,去断定究竟是生物特征决定身体的社会行为,还是社会技术、话语和权力塑造了身体。一个相对开放但是确定的事实是:我们可以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谈论身体,作为自然物的身体是相互独立的个别有机体,它有着明确的边界和内部结构,而作为社会现象的身体则是在相互交往中表象出来的社会权力关系,它只有在一个社会群体的历史实践中得到笼统的刻画。
在身体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之外,我还想提到与之紧密相关的身体的第三个重要特征:身体与我的亲近性。这里的“我”既是社会实践和社会话语的参与者,也是在自然的身体中活着的个体。这里的亲近性因此有两重内涵,一是从个体的层面而言,我的一切活动,包括心智活动在内,即使不能还原成身体活动,至少也伴随着身体活动。换句话说,身体活动至少构成了自我存在的一个必要要素。二是从社会的维度看,我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话语的主体始终是一个具身(embodied)的存在,身体不仅是社会活动作用的对象或客体,同时也实质地参与了社会活动主体本身的自我实现。借助这一系列术语,我想要解释的其实只是一个我们熟悉的现象:对身体的有意伤害往往不仅仅是对肉体的侵犯,而首先是对自我尊严或者人格的践踏。例如文革时给批斗对象剃阴阳头。我们的自我形象首先在身体中得到实现,它也首先在身体中受到威胁。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的描述给出一个关于身体的初步定义:人的身体是承载生命的有机体,它在社会实践和话语中得以表象,它与人的自我及其尊严有着其它存在物难以比拟的亲密关系。由此出发,正如论者所见,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刻画身体和宗教的关系,作为自然物的身体,它的生理机制、进化方式、感知模式、情感反应机制等等物理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宗教信念和宗教行为,这是从(自然)身体到宗教的研究模型;而作为社会物的身体,它本身就是宗教这一社会话语体系和实践机制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的宗教传统塑造了我们对身体的表象方式,这是从宗教到(社会)身体的研究近路。[19]显然,这两种基本近路都会推进我们在宗教语境中对自我与身体的理解。
《儿童法案》中的案例并未触及自然身体对宗教的构建,它更关注的是宗教传统如何通过塑造我们的心灵来支配我们的身体。在以上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的叙事在忽略身体的同时,也预设了一种简单的身心二元模型来刻画信念、意愿、自由抉择同身体的关系。心灵被看作真正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通过它的理性谋划和自由意志做出决断,以此决定身体的命运。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对这一启蒙以来盛行的哲学图景有精确的刻画:“一个孤立的意愿,受理智的引导,随意地同一系列令人相当不满的情感勾连在一起,它碰巧寄居在一个同样让人不满的人类身体之中。”[20]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身体只是碰巧作为一个客体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因此也不难理解身体本身的意义为何被遗忘。这里不是讨论身体应有的本体论地位的恰当场合,但它足以向我们表明,要重构身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或者价值范畴的意义,尤其是要展示身体与自我的亲密性,我们至少需要悬置这样一种粗糙的二元论模型,越过心灵这一理论中介,直接考察宗教对身体的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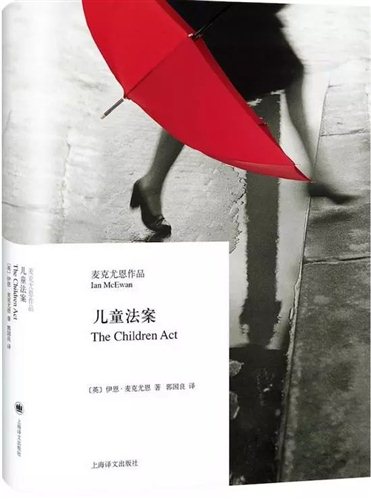
《儿童法案》中的输血案例和连体婴儿案例,都直接呈现出宗教信仰和世俗法律在面对濒死的身体时的话语冲突和权利冲突,我们接下来的考察限于篇幅也将聚焦于这一特殊情景中的身体。而在亚当是否应当接受输血的法庭争论中,医院方的陈述则展示出医学作为另一种话语和实践体系对身体权利的要求:小说中作为证人出庭的血液病专家卡特从一出场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法律程序都是胡扯,应该一把抓住亚当的脖子,拽着他立即进行输血。”[21]他接下来给出一系列数据,不容置疑地断定亚当如果不接受输血,就只能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同时断定亚当为他父母所接受的宗教而死毫无意义。[22]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医学对濒死身体的态度作为法律和宗教之外的一个独立话语体系进行考量。而从历史的演进来看,西方世界建构濒死身体的主导话语恰恰经历了从宗教到医学再到法律的转移。简单地重构这一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儿童法案》中的叙事和当代有关宗教与身体的研究中被不正当地忽视的一个基础问题: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宗教是否还有权构建我们的身体观?
在中世纪的欧洲,尽管传承自古代异教文明的医学和科学理论影响着知识阶层的身体观,普罗大众面对鲜活身体的生死爱欲时的态度混杂着基督教传统之外的文化因素,但主导这一时期身体话语的无疑是基督教教义。[23]无论从肯定的方面还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基督教都可以说成是身体的宗教。一方面,基督道成肉身,正如论者所言,“基督教建立在身体的毁灭,耶稣身体的毁灭之上。”[24]基督的肉身又通过圣体圣事中的“这是我的身体”来祝圣面饼,使之成为信徒日常的生命食粮。[25]基督教坚信肉身的复活。正如著名中世纪史家拜纳姆(Caroline Bynum)所论,“在整个中世纪,处理末世论的理论家都倾向于不把人说成是灵魂而说成是灵魂与身体。”[26]另一方面,《圣经》中也会谈到肉与灵的对峙,教会很早就有苦修的实践。身体及其欲望常常被看作尘世和罪的象征,一个有待被征服的领域。这种充满张力的身体观同样鲜明地体现在健康护理领域。照料病人被看作教会主要的慈善事业之一,作为上帝造物的身体理应得到尊重和呵护。英语的医院一词本就起源于法语Hôtel-Dieu,意为“上帝的客栈”。中世纪的医院多由宗教团体创立,不仅用来照料病患,而且用来收容麻风病人、朝觐者和无家可归的穷人。疾病和尘世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但与此同时,对身体神学地位的尊重在中世纪意味着身体所遭受的恶同样具有神学内涵。疾病象征着神的意旨,身体所承受的致死疾病既可以看作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也可以看作对灵魂的考验。[27]在中世纪的神学话语中,疾病不仅仅是自然现象,而是同个体生命的罪与赎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疗治病苦也不仅意味着身体症状的改善,而直接指向个体的得救。
近代身体观的变化因素繁多,有三个重要事件值得一提。一是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将心智与身体剥离,把身体表象为一个如钟表般精确运作的机器;[28]二是16世纪维萨里的解剖学工作,它使人们对身体的理解从理论推断向经验观察转变。[29]三是福柯所说的临床医学的诞生,18世纪末和19世纪医学的发展使得医生能够以科学“凝视”的方式重新解释有如机器般的身体。[30]然而,医学真正成为我们谈论身体的主导话语,是在20世纪。有历史学家断言,“20世纪身体的历史就是前所未有的医学化过程。”[31]医学的突飞猛进重新解释了疾病和健康的内涵,身体被去魅,被表象为一个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观察、计算、拆解和改造的自然物。实验医学的诞生和发展将这种身体物化和中立化的努力推到极致:人的身体不再是罪与赎征战的领域,而成为各种生物技术得以运用的试验田。疾病在不再被妖魔化的同时,也失去了它可能的神圣意涵。
医生的权限前所未有地增强,他们不仅断定生死,而且通过参与公共卫生政策的指定,规范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此而言,医学话语中的身体绝非价值中立的表象:无论是在实验室、手术台还是我们的餐桌、健身房中,医学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界定都直接规范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准则,左右着我们对于生活福祉的理解。而在我们所关注的濒死身体以及医疗手段的选择这一话题上,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取得了无可置疑的主导权:“医生说了算”不仅仅是医生们的自我标榜,也是大多数病患尊奉的行为准则。这也就使得耶和华见证人们的选择在大多数现代人眼中显得不可理喻。
现代医学在20世纪疯狂扩张的同时,也遭遇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某些医生滥用医疗实验和手术权限,例如臭名昭著的脑白质切除术,人们迫切地意识到医疗实践同样需要规范。晚近兴起的患者赋权运动就是对医学话语霸权的一种纠正:它强调在涉及患者医疗方案等重要的医疗选择时,医生不能越俎代庖替病患作出选择,而必须在保障患者充分知情的前提下,由患者赋予医生选择的权力。[32]在《儿童法案》一书中,我们看到参与论争的各方对于一个成年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决定放弃治疗并无异议。
与此同时,将身体高度医学化和技术化的努力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试管婴儿、克隆、基因改造等技术都在引发人们伦理上的担忧,20世纪70年代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和繁盛就是对这一现状的回应,它推动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制定和发展,而具有宗教背景的身体话语无疑是这一运动的关键推手。另一方面,基因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身体的所有权问题,界定身体和可以作为商品的其他自然物的区别。例如某位癌症患者的细胞可以提取出具有商业价值的不死细胞,他是否因此有权分享该不死细胞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所有这一切,推动着身体的话语主导权从医疗技术向法律转移。[33]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儿童法案》中所描述的场景,医学话语不得不放下固有的傲慢,与前现代的另类宗教主张对簿公堂。与此同时,法律被不加反思地看作现代世俗社会裁断身体话语是否合理有效的最终权威。
由此我们回到从一开始就困扰我们的问题,在涉及身体的话语权争议时,法律的权威究竟来自何处?在《儿童法案》中,菲奥娜法官一再宣称她要尊重宗教信仰,要在形形色色的宗教和道德体系中保持中立。她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福祉概念,它看起来既独立于医院对白血病和输血疗法的数字化和程序化描述,也独立于耶和华见证人神秘的血液禁忌。菲奥娜希望它可以体现“当今理性之人的判断”。[34]我们并不清楚这里所谓的“理性之人”具体指哪个人群,但从《儿童法案》所给出的一系列与宗教相关的判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是世俗之人的意志体现,例如犹太夫妇的女儿更应该进男女混合、风气开放的学校,为了防止连体婴儿中的一个无意识地伤害另一个,法律应该终止前者的生命等等。正如小说作者麦克尤恩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说,“世俗的心灵在做出合理的判断时要出色得多。”[35]然而,如果我们要认为理性之人的判断并不仅仅只是在口头上尊重宗教信仰,我们就必须去追问它所依据的世俗道德是否向宗教信仰开放,是否允许宗教话语去构建我们对身体的理解。遗憾的是,小说作者选择了耶和华见证人的输血禁忌这样一个特殊的、很少有人支持的宗教身体话语,忽略了当前法律之所以占据身体话语的主导地位是近代身体观陷入危机的历史后果,从而掩盖了我们在当前的身体话语危机中必须面对的根本挑战: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上去面对曾经在历史上主导过我们的身体观的各种话语,无论它是来自超自然的信仰,还是科学的观察,抑或是法律本身所体现的人民的意志。这个虚构案例中的宗教身体观缺少应有的理论活力和可辩护性,它使得我们没有机会去进一步拷问菲奥娜所依循的世俗道德,是向主流宗教话语开放的世俗道德,还是从一开始就拒斥超自然信仰的世俗道德。[36]菲奥娜和小说的读者太容易不加反思地断定,受耶和华见证人这样一种专制封闭的宗教左右的心灵不能成为世俗道德认可的心灵。但是,我们不应遗忘,更多主流宗教是具有自我批判和更新精神的信仰体系。难道它们教养的儿童也要排除在成熟、独立的现代心灵和世俗道德之外吗?
小说没有给出回答。菲奥娜法官的判决当即生效,亚当在经历了生死的剧烈起伏之后,放弃了他固有的耶和华见证人信仰。与此同时,他爱上了这位改变了他人生的年近六旬的法官。这段不伦之恋注定得不得理性的菲奥娜法官的回应。一年后,亚当的白血病复发,已经成年的他拒绝接受输血,在痛苦中死去。失去了宗教话语的亚当,并没有为他自己的身体找到福祉。
[1]以下引文据中译本伊恩·麦克尤恩《儿童法案》,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个别处依原文(Ian McEwan, The Children Act, NewYork: Nan A. Talese/Doubleday, 2014)有改动。
[2] Andrew Holden, Jehovah’s Witnesses:Portrait of a Contemporary Religious Mov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pp. 22-29, esp. p. 28. 《儿童法案》的中译本中将《守望台》译为《瞭望塔》,与其官方中文译法不合,见第87页。
[3]耶和华见证人经常引用的《圣经》文本包括《创世记》9:3-4、《利未记》17:10-14、《使徒行传》15:29等,参见George D. Chryssides, HistoricalDictionary of Jehovah’s Witnesses, Lanham, 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Inc., 2008, p. 21.
[4] Blood, Medicine, and the Law of God, Watch Tower Bible andTract Society, 1961, p. 54.转引自Wikipedia contributors, "Jehovah's Witnessesand blood transfusion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ehovah%27s_Witnesses_and_blood_transfusions&oldid=793608903 (accessed August 21, 2017).
[5]麦克尤恩,《儿童法案》,第128页。
[6]亚当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写道:“我是独立的个体,不是我父母的附属品,无论我父母怎么想,我都是在自主做决定。”见麦克尤恩,《儿童法案》,第89页。
[7]麦克尤恩,《儿童法案》,第90页。中译文作“吉利克能力”。
[8]Wikipediacontributors, "Gillick competence," Wikipedia, The Free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Gillick_competence&oldid=790504376 (accessedAugust 22, 2017).
[9]麦克尤恩,《儿童法案》,第4页。
[10]同上书,第130页,原书将well-being译为“安康”。
[11]同上书,第16页。此处转述与译文有出入。
[12]同上书,第130-131页。
[13]同上书,第11页。
[14]相关讨论综述,参见Louis C Charlan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The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5 Edition), Edward N.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5/entries/decision-capacity/>.
[15]在此我们不需要断定这两条原则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个体及其自由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起源,近著可以参见Larry Siedentop, Inventing the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关于西方儿童观的演变,可以参见艾格勒·贝奇和多米尼克·朱利亚主编,《西方儿童史》(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6]参见布莱恩·特纳著,《身体与社会》,马海亮、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46页,第58-59页。约翰·罗布和奥利弗·J. T. 哈里斯主编《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第28-30页。
[17]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New York: Roudedge, 1993, pp. 1-2;参见罗布和哈里斯主编,《历史上的身体》,第29页;Ivan Crozier (ed.), A Cultural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in the Modern Ag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0, pp. 6-8; 10-12.
[18] Holden, Jehovah’s Witnesses, p.28.
[19] Robert Fuller, "Religion and the Body." Oxford Research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23 Aug. 2017. http://religion.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9340378.001.0001/acrefore-9780199340378-e-18.
[20] Mary Midgley, “The Soul’s Successors: Philosophy and the ‘Body’,” in SarahCoakley (ed.), Religion and the Bod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3-68, at p. 56.
[21]麦克尤恩,《儿童法案》,第70页。
[22]同上书,第71-74页。
[23]关于中世纪身体所呈现出的教义身体、医学身体和鲜活身体的多元形态,参见罗布和哈里斯主编,《历史上的身体》,第226-254页。
[24]乔治·维加埃罗主编,《身体的历史(卷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张竝、赵济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25]参见维加埃罗主编,《身体的历史(卷一)》,第17-19页。
[26] Caroline Bynum, “Why All the Fuss about the Body?” Critical Inquiry 22 (1995), pp. 1-33, at p. 9.引自罗布和哈里斯,《历史上的身体》,第234页。
[27]参见特纳,《身体与社会》,第134-136页。
[28]罗布与哈里斯,《历史上的身体》,第285页;第291-292页。
[29]参见维加埃罗主编,《身体的历史(卷一)》,第262-265页;罗布与哈里斯,《历史上的身体》,第298-300页。
[30]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参见罗布与哈里斯,《历史上的身体》,第297-298页;特纳,《身体与社会》,第238-245页。
[31]让-雅克·库尔第纳主编,《身体的历史(卷三):目光的转变:20世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亦见罗布与哈里斯,《历史上的身体》,第332页。
[32]有关这一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参见彼得·于贝尔著,《生命的关键决定:从医生做主到患者赋权》,张琼懿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
[33]参见让-皮埃尔·博,《手的失窃案——肉体的法制史》,周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该书对法制史传统,尤其是法国民法传统中的身体概念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
[34]麦克尤恩,《儿童法案》,第16-17页。
[35]引自Deborah Friedell, “The Body’s Temple”,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14/books/review/the-children-act-by-ian-mcewan.html?mcubz=0
[36]关于这里提及的两种不同世俗道德或者世俗性的区别,参见Charles Taylor, “What Does Secularism Mean?” in id. Dilemmas and Connections: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MA and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3-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