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8年5月24日(周四)19:00,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德敏副教授将主讲未名学者讲座第35讲。讲座主题为“托克维尔论自由与权威”,将探讨自由与权威这一对关系在托克维尔思想中所展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意涵。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段德敏副教授的文章《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帝国时刻》,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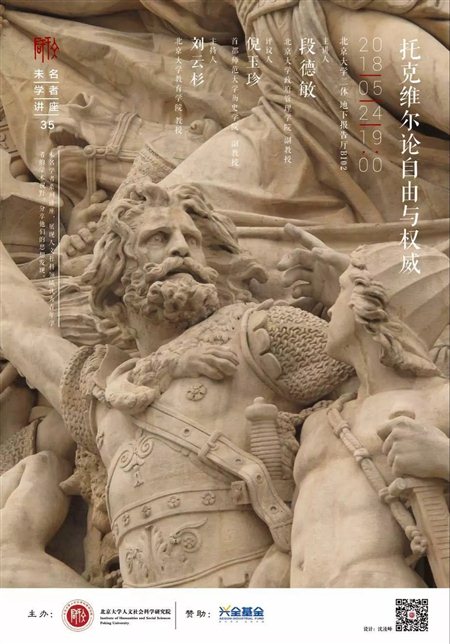
也许我们很难想象《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论自由》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曾激烈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而更需要在理论和思想上厘清的是,他们为什么持这种立场,这种立场对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意味着什么。珍尼弗·皮茨(Jennifer Pitts)的《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不仅记述了欧洲17、18世纪自由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生的“帝国主义转向”,而且试图在理论上对其作出系统的解释,这在晚近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是少见的。
随着法语版《托克维尔全集》的陆续出版,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者”形象逐渐清晰。事实上,早在1833年(即在《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出版之间),他就写了一篇题为“如何使法国获得好的殖民地”的短文,试图从法国人的国民性中找出法国之所以未能建立强大海外殖民地的原因。而这篇文章又明显呼应了1830年首次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末尾处的感慨:“有一个时期,我们也曾有可能在美洲的荒野上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同英国人在新大陆上平分秋色。……但是,一连串不胜举的原因,使我们失去了这笔可观的遗产。”1837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如何能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维持统治,并尽可能地扩张势力。而此时他的写作依据仅是搜集来的各种资料,文中对阿尔及利亚部族政治的描述非常详尽,足见他在此问题上所下的功夫。1839年托克维尔当选为国会议员,对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兴趣日增。1841年和1846年,他两次亲自访问阿尔及利亚地区,一如他在北美旅行时一样,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访谈记录。1841年有《关于阿尔及利亚》一文,1847年则有两份长篇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问题的国会报告。而这些,仅是托克维尔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字中的冰山一角。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书影
而最能说明托克维尔帝国主义一面的,恐怕莫过于这样两段话。第一段来自1837年的《阿尔及利亚信件》:“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竖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另一句则来自1841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当论及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所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时,他说:“我经常听到我尊敬的法国人说,我们焚烧收成、清空筒仓以及最后抓捕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坚定地站在帝国主义扩张这一边,这一立场终其一生都没有大的改变。自由与帝国在此碰撞:一边是温文尔雅、追求自由和自治;另一边则是征服、压迫和暴力。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写作的时代已经是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颁布后的很多年,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观念早已存在于当时知识界的语言之中。这不禁让我们思考,这是同一个思想家吗?如何解释这种矛盾?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梅尔文·里希特(MelvinRichter)的反应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态度:愤怒,甚至失望。他在《托克维尔论阿尔及利亚》(“Tocquevilleon Algeria”)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立场,最后总结道,“托克维尔明显未能将他在研究美国时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和伦理自觉运用到法国在北非的行动上去。”他甚至宣称,“托克维尔值得被称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要走到这一步尚可存疑,但起码另一位政治理论家希瑞·威尔奇(Cheryl Welch)也大体赞同里希特的看法,她将托克维尔的帝国立场看成一种自由主义者面对世界政治时表现出来的典型的“软弱性”,而且这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也不少见。
皮茨在这方面的思考要细致和深入得多。她并没有简单地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与其帝国立场相对立,而是将这些所谓的“帝国自由主义者”(imperial liberalist)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思想史脉络中,试图寻找出一些历史变化模式,进而探索这一变化的意义所在。而根据皮茨,较托克维尔和密尔早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狄德罗(Denis Diderot)、边沁(Jeremy Bentham)等,都是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比如贡斯当在其著名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之前,就曾写过一本题为《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的小册子,在其中他说:“有些政府,当他们派兵到遥远的地方时,仍然在谈论保家卫国;人们会想,他们可能是将所有他们放火的地方叫做祖国。”皮茨将18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帝国主义对外征服的态度作了一个历史纵向的比较,她发现这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转变:
在1780年代左右,对特定帝国主义行为和无限止的扩张计划的怀疑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识。然而,仅仅五十年之后,我们就很难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确,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是热心的帝国主义者。
如何理解这一转变?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既可以与帝国主义对接,又可以与帝国主义相排斥。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一个死胡同,或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自由帝国主义悖论”(Paradox of liberal imperialism)。自由主义往往强调普世性的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和对个体的尊重等,它们完全可以被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对外征服和扩张,因为自由和征服在字面意义上就不契合。然而,在另一些时刻,它们又可以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对普世价值的过分强调往往导致文明话语的单一性和文化上的等级观念,对外的征服可以被“解释”为更高级的文明向外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要借助于一些暴力和强制手段,但其目的却是世界的大同和普世性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帝国式的自由主义认为征服即是“使人自由”。典型的如密尔,他认为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即起到“提升”印度人文明水平的作用,从而使其更接近《论自由》中所描述的自由社会。
在这一点上,印度裔的政治理论家乌代·梅塔(Uday Mehta)有着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在《自由主义和帝国》(Liberalism and Empire)一书中,梅塔指出,自由主义经常持一种狭隘的进步观,无视特定地域中文化群体的特殊性,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在信念上的基础正在于此,他们相信—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其帝国主义政策是正当的。正因为此,梅塔认为自由主义即便不被完全放弃,也需要严肃地被修正。但皮茨对此并不以为然,她相信思想史纵深的维度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同样可以用来反对和批判帝国主义。或者,在皮茨那里,真正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反帝国主义的,而所谓的“帝国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说一定是一种伪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密尔,都在理论上于自由主义的“理想”而言都有所欠缺。那么,如何解释自由主义思想家转向帝国这一现象?
皮茨诉诸的是一种历史维度和社会语境的解释。她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形态,事实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所谓“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但它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从来都是多样化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这方面极端的例子。从广义上说,狄德罗和托克维尔都可以被归入“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但他们对法国帝国政策的态度却大相径庭。皮茨认为,在理论上寻找个中的原因是徒劳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大转变”主要在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个体思想家所造成的影响。
皮茨列举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期间这样几个重要的变化:在政治方面,随着对印度南部和非洲地区的占领,英帝国从一个相对“自由”的殖民帝国转变为极具压迫性的帝国。而同时,法国失去了北美和亚洲的大片土地,大革命使法国的民族自尊膨胀,但也进一步加强了其不安全感。在文化方面,随着欧洲霸权向东方的扩张,东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但这种交流带来的直接结果却是文化上的进一步隔阂。如果说伏尔泰的时代许多欧洲人还将东方看作某种理想社会,并能反衬出欧洲社会的腐朽的话,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明显开始将东方看作文化上更为落后的存在。在经济方面,19世纪初期欧洲工业和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拉大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这在塑造欧洲知识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最后,在种族观念方面,皮茨总结道,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欧洲人开始形成一种普遍的种族上的优越感,在对非欧洲人的描述中,“野蛮”和“落后”这样的词汇明显多于前代。
在皮茨看来,正是这种“大气候”的转变,影响了个体思想家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和态度。如果说自由主义都支持某种普世主义的话,那么多元、开放和承认文化差异性的普世主义在19世纪逐渐让位于单一、封闭和线性进步观的普世主义。在微观层面,具体的思想家在历史“大势”面前也会作出一些反应或选择,尽管他们本人并不一定意识得到这一点。就托克维尔来说,他非常强调共同体(community)的价值,而当时法国在大革命后被专制和革命的动荡不断撕扯,国家内部存在前所未有的分裂。因此,法国急需一些能够加强国民凝聚力和共同归属感的东西,而战争和对外征服在这方面看起来非常有用。皮茨认为,正是托克维尔对这种国民凝聚力的过分强调,以及他在这方面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得他倒向了一种接近民族主义的立场。无疑,对皮茨来说,这种思想倾向是幼稚的和未加深思熟虑的。皮茨指出,托克维尔并没有能够具体分析对外征服到底是如何转化为国民荣誉感和凝聚力的。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的思考往往受一厢情愿的影响,而非仔细的社会学分析。”因此,皮茨认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本身也在其帝国立场面前显得不再那么真诚和透彻。
本文作者段德敏副教授
但是否真的如此?这里起码有两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心理学式的解释实际上将托克维尔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字降到一个很低的层次,皮茨和里希特最终都将这部分文字看作托克维尔整体著作中的“边缘”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一个“错误”。但事实上,托克维尔自己可能并不这样看。如前所述,托克维尔关于帝国的文字与其他更为“严肃”的作品的形成时期几乎重合,有许多正是在他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期间所作,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并不亚于美国。如果自由和帝国在托克维尔那里看起来有矛盾的话,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其“自由”的观念,而不是一味地为这一自由主义的“历史性错误”惋惜?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皮茨的解释中,托克维尔对共同体价值的关心也被看作是一种负面的倾向,对它过度的强调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因而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观念不符。这一点尤其值得重新检讨,托克维尔的自由观念到底是如何?他与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又是如何?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托克维尔自己给出的支持帝国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实际并不需要依赖隐晦的心理分析。在《关于阿尔及利亚》一文中,托克维尔明确说道:“我不认为法国可以认真地考虑放弃阿尔及利亚。在世界眼里,这将被看作法国衰落的明显象征。”而在另一处,他指出,如果法国放弃阿尔及利亚在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它们将迅速落入其他欧洲列强之手。而这一旦成定局,法国将不可避免地在欧洲强国之争中被降为第二等的国家。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法国无法承受的后果。因此,就本人而言,他盘算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一种国际领域中残酷但无法回避的权力较量。这种盘算极具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以至于他所用的语言也很有马基雅维利的色彩。托克维尔称占领阿尔及利亚的行动为“政治上的必要性”,这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由”在内涵上实际并无二致。而且这里的关键在于,“政治上的必要性”独立于道德、价值和文化观念,托克维尔并未试图在后者的意义上贬低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从而为其帝国立场寻找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在这一点上,他同密尔构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对比关系。
密尔同样支持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但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他试图从道德和文化方面为这种帝国主义立场提供合法性论述。在《论自由》中,密尔说,“专制主义是对付野蛮人的合法统治方式,只要目的是为了他们的进步,手段因达成这种目的而合法。”这句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帝国的等级结构是以文明进步为合法性基础的,对落后人群的支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说,在托克维尔的著作—包括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字—中,很难找到这样的文化等级观念。事实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花了大量笔墨描述美洲印第安人在与欧洲“高级”文明接触时的悲惨遭遇,他曾激烈批评当时法国著名的种族主义知识分子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观点,称其为“极其错误”。从而,皮茨关于历史大势的论述,尤其是19世纪欧洲人对外部文化态度的转变,在托克维尔身上也并不是很适用。托克维尔为帝国的辩护主要是出自“政治”上的需要,其基础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由”。而如果国际领域的权力制衡关系不再如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那样依赖对外扩张的话,他很可能会反对帝国主义政策,正如其20世纪的追随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后来的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一样。
在自由与帝国的对勘中,自由也包含共同体的独立和自主。如果法国被降为第二等的国家,在托克维尔眼中,法国人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将沦为受其他国家支配的地步。显然,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局完全与法国人的自由相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帝国似乎并没有乍看上去那么针锋相对。而这种自由观念事实上早已存在于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那个共和主义传统之中,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与战争和征服从来也都不是绝对矛盾的关系。这种自由并不是以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描述的个体私人领域中的自由,它不仅强调共同体的价值,而且以它为核心;它也不是霍布斯所说的外界障碍的不存在状态,而更接近昆延·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所阐释的“支配的不存在状态”。为了免除支配,人必须参与政治,具有一定的公共美德。由此而延伸,人们需要爱共同体(或祖国),并在必要的时候为它而战。而这正是托克维尔的自由观念的重要内涵。明白这一点,我们便也不会对《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这一句话感到惊诧了:“我不想贬低战争;战争几乎总是能扩展人民的思维,并提升其心灵。”
这两种自由传统的对比在托克维尔和密尔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更有甚者,这二者不仅在思想和私人层面有过密切交往,而且就帝国这一问题本身也有互动。在一封写于1841年的信中,托克维尔对密尔说:
我不必向你指出,亲爱的密尔,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的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民情的逐渐软化、心灵的降格、品味的平庸化,……我们不能让这一民族轻易染上这种习惯,使其心中的崇高为安宁而牺牲,使伟大事物让位于微小事物;让这样一个民族相信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其实应该更小,它已经从其祖先留给它的位置上掉落下来,它应该用建造铁路和在以任何代价获取的和平环境中使个人富裕来安慰自己,这是不健康的。
密尔的回信同样值得一提,他对托克维尔说:
我最近常常想起你为英法之争中的自由派所作的辩护—民族骄傲的情感是仅存的公共精神和崇高的情感,因而不能允许它衰落。……(但是)最愚蠢和无知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在外国人眼中,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对自身重要性的喧嚣和吵闹的强调,这给人们的印象是愤怒的虚弱,而不是力量。一国的重要性实际上依赖于工业、教育、道德和良好的国家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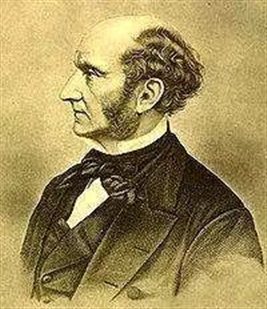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在密尔这封语带讥讽的回信之后,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告一段落,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他们的帝国立场在这两段话中也清晰可见:托克维尔强调国家的荣誉,密尔则强调文明进步的成果。如果说在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帝国的时刻,那么这一时刻中不同的自由传统也值得仔细区分和理解。托克维尔所处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最终的走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独有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同样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上持非常激进的立场。我们当然不必为帝国主义辩护,反而应该在道德上极力批评帝国主义,但我们实际上也并无太大必要因这种立场而降低对韦伯或托克维尔思想的赞赏。在思想史中,流淌着一些传统的暗河,思想家在现实政治问题上作出一些个人的抉择往往也在河岸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