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教授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2019年秋季学期担任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周教授在宋明间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其代表作《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本公众号特别推送向辉先生对该书的评介,以飨读者。注释从略。
士人的书籍世界与书籍世界的士人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读书笔记
摘 要:本文通过对周绍明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一书的阅读,讨论周著所要揭示的主要问题以及其对我国书籍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籍 雕版印刷术 书籍流通 知识共同体
书籍,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以来的印本书,作为文字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工具,在中国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人甚至将文字和书籍视为神圣物品加以崇拜。据周绍明说:彭绍升早年痛失一只眼,汪缙直到快二十岁还是个迟钝的学生,王丙在科场上屡屡失意,钱近仁必须克服贫困和家庭冷漠以学习认字。他们在获得识字能力的道路上的苦难和牺牲,无论是何种层次和类型,都没有动摇他们各自对书籍的热爱,及他们对儒家圣贤书中教导的敬畏。他们把书视作道德智慧的神圣载体而加以礼敬,这些智慧使所有读到这些书的人受益。诸如此类的个案在中国书史上层出不穷。那么,作为道德智慧之神圣载体的印本书究竟与士人和文化有着何种关系,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又起着何种作用?雕版印刷术与印本书的关系如何,雕版印刷术又为什么最终会走向没落?它与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入侵有着何种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研究中国书史的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更准确的说是资料太繁杂,需要从大量的文献材料中细致搜寻)很多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周绍明的这部著作通过对大量文献材料的爬梳,梳理出中国书籍流通的路径,细致考察印本书在士人中的流布过程,通过对江南地区的一些个案的讨论,探讨了书籍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提供了从11 到18 世纪中国书籍世界最完整的长时段图景,揭示了识字精英的知识世界的演化,它在帝国范围内文人和非文人共同分享的文化的形成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展示了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所构成的社会史景观,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思了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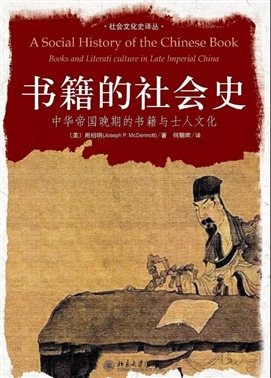
一、关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是以反体文字或图画制成版面,然后着墨(或其它色料);就纸(或其它表面),加以压印以取得正文的一种方法。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一直以来是传统中国科技发展史的重要标志。关于雕版印刷术与印本书的研究中有若干问题值得细致探讨。周著深入讨论了雕版印刷的书籍何时取代手写本及其取代手写本的原因,以及雕版印刷又为什么走向消亡这两个问题。周绍明说,虽然当代中国书史元宿张秀民颇为自得的认为(其实这也是很多国人的看法):我国不但发明了造纸术,又发明了印刷术(雕版与活字版),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中国的印本书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和妥善的保存,关于印刷术以及书籍生产管理的翔实记载也没有留存,以至于一些韩国人声称印刷术是韩国最先发明的(虽然韩国以外极少有学者认真对待这一说法),因为有人于1966 年在韩国东南的庆州一个佛塔里发现了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一件长约14 英尺的武周末年汉译之《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刻印本。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详细描述更是缺乏。吊诡的是,现存关于中国雕版书籍如何生产的详细记录刊印于1820 年;关于印刷技术和过程的这一记录是在中国之外的马六甲写成和出版的;其作者是一个当时住在马六甲的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82),出自他的英文书《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但不管怎么说,印本书籍在最近一千年的时间内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由中华帝国向四周扩散,按照周绍明的说法,大约从明代中后期(16 世纪中期)开始取代(超过)手抄本的地位7,成为士人追捧的对象。即便如此,手抄本直到现在仍是其他抄本或印本的鲜活母本,甚至直到今天,它们还在继续塑造着中国印本书的内容8(当然,作者并没有考证当前网络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使用电脑写作,手写本的年代好像越来越遥远,并逐渐成为图书馆、博物馆的珍惜品种了)。搞本、抄本也一直是中国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有证据表明,无论印本书在中国的发展如何迅速,手写本和印本一直是中国书籍生产中持续并存的伴侣。通过对现存古籍书目的考察和私人藏书家各种书目的分析,周绍明发现,从宋代到明清时期,印本书所占的份额在起伏波动中逐渐增大。当然,他也注意到,书印的越多、流传得越广,就越有可能在其传播的某一个阶段产生手抄本。这种相互影响是如此持久和普遍,以至于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中手抄本和印本之间无法划出清晰和绝对的界限。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图书馆里充栋盈架的印本,承载了一种丰厚的手抄本文化的印记,它在中国的书籍世界中比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要持续得更久、渗透得更深。
 那么,为什么雕版印刷——作为不晚于8 世纪的技术创新——未能立即对书文化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与因为传统抄写劳动的持续低劳动力成本、纸张的高成本等变量有着密切关系。它最终能够取代大量的手抄本生产,主要归因于对某些书籍的更大需求,以及来自活字印刷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包括匠体字及其刊刻方法的采用)而带来的价格下降、在书籍生产的所有四个环节(不仅是印刷过程,也包括印刷所使用的纸张价格也显著下降),生产成本都出现了显著降低13。直到16 世纪,印本书次才全面进入士人的书架,并不断挤走手抄本的份额。大约从16 世纪开始一种要求更多样化的精神食粮的更加强烈的愿望,推动了哲学关注点的扩展,最终反映到印刷上来。明中期,非哲学类出版物也发生了类似变化。出版者开始推出范围很广的早期历史著作——《汉记》、《唐六典》、《文献通考》和《吴越春秋》——的新版本,这些书的印本此前流传不广。当然,与我们今天的印刷出版行业一样,商业利益总是居于首要地位,雕版印刷最多的还是有商业利益的书籍,比如应试之书、应酬、娱乐之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以至于有人抱怨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官方刻书的商业化意味要清淡得多,可是这些书很少能够进入普通士人以及非士人的手头。 那么,为什么雕版印刷——作为不晚于8 世纪的技术创新——未能立即对书文化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与因为传统抄写劳动的持续低劳动力成本、纸张的高成本等变量有着密切关系。它最终能够取代大量的手抄本生产,主要归因于对某些书籍的更大需求,以及来自活字印刷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包括匠体字及其刊刻方法的采用)而带来的价格下降、在书籍生产的所有四个环节(不仅是印刷过程,也包括印刷所使用的纸张价格也显著下降),生产成本都出现了显著降低13。直到16 世纪,印本书次才全面进入士人的书架,并不断挤走手抄本的份额。大约从16 世纪开始一种要求更多样化的精神食粮的更加强烈的愿望,推动了哲学关注点的扩展,最终反映到印刷上来。明中期,非哲学类出版物也发生了类似变化。出版者开始推出范围很广的早期历史著作——《汉记》、《唐六典》、《文献通考》和《吴越春秋》——的新版本,这些书的印本此前流传不广。当然,与我们今天的印刷出版行业一样,商业利益总是居于首要地位,雕版印刷最多的还是有商业利益的书籍,比如应试之书、应酬、娱乐之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以至于有人抱怨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官方刻书的商业化意味要清淡得多,可是这些书很少能够进入普通士人以及非士人的手头。
雕版印刷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西方文化和技术的进入,比如,米怜死后,他的忠告最终还是被用活字来印刷中文书籍的论调所压倒。该技术的倡导者认为,一旦有了印刷机,一旦有了一副中文活字,实际上活字印刷更便宜。而且,他们相信既然这项西方技术的操作几乎不需要来着中国工人的任何帮助,将使传教团摆脱清廷对中国刻工的控制,使其出版活动更经常化。
二、关于书籍的流通过程
传统书史的研究对于印本书的流通过程不是特别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分散,一方面是流通过程对版本目录似乎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这一过程对于书史本身来说极具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书史的细致考察,周绍明用一幅简图描绘了印本书籍在中国的流通过程:
.png) 从上图可见,古代中国的印本书籍流通过程从书籍主要有官刻和私刻的区分(也有更为细致的区分,比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的分类为:官刻本、私宅本和坊行本三类;李致忠分为中央机构刻、地方机构刻、私宅坊肆刻、寺院刻、藩府刻等),藏书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印本,并且在藏书家内部形成一种内部循环机制,这里有着“知识共同体”的雏形(最终并未形成)。藏书家获得书籍的渠道是比较多的,他们在尽可能的扩充自己的藏书量,让自己占有更多的书籍,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和条件获得他所希望获得的书籍。需要注意的是: 从上图可见,古代中国的印本书籍流通过程从书籍主要有官刻和私刻的区分(也有更为细致的区分,比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的分类为:官刻本、私宅本和坊行本三类;李致忠分为中央机构刻、地方机构刻、私宅坊肆刻、寺院刻、藩府刻等),藏书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印本,并且在藏书家内部形成一种内部循环机制,这里有着“知识共同体”的雏形(最终并未形成)。藏书家获得书籍的渠道是比较多的,他们在尽可能的扩充自己的藏书量,让自己占有更多的书籍,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和条件获得他所希望获得的书籍。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私刻书籍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并不完全的循环关系,只有一部分消费者(包括作为士人或者非士人的藏书家)主动刻书;
第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寺庙在书籍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书籍一旦非人格化,成为印本,就已经脱离了原作者,藏书家们的意图更多地影响了书籍的流布;
第四、书籍流通中最重要的循环过程是在藏书家们的手中传递;
第五、书籍的流通过程不是简单的从刻书到买书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各种精彩故事的冒险历程,每一个环节都有待深入考察,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书史要么是藏书家的个人史,要么是印刷书籍的朝代史,要么是某一特定书籍的版本、内容的考据,很少有人关注书籍流通这一复杂过程中的趣事,这与资料的欠缺有着密切关系。
在书籍的流通过程中,印本书与藏书家的关系至关重要,藏家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千方百计的试图不断增加自己对包括印本书在内的各种书籍的占有,他们通过继承、借阅、物物交易、抄写(抄录)、购买等途径丰富、增加自己的藏书量。他们也试图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与家族永久保存作为重要财富的书籍,但不幸的是即使一宗藏书躲过了困扰官方藏书的自然灾害、政治动荡(如外族入侵、政治斗争破坏)、鼠啮蠹蚀和管理疏漏,以及中国分割继承的习俗实际上会使得藏书的继承者们很快瓜分藏书,并按其各自的意愿卖掉,其中政府藏书还受到皇帝、宗室、钦差、朝廷高官和其他获准接触藏书的公务人员的劫夺。那么士人如何应对这一难题呢?
三、关于文人的“知识共同体”
对书籍史的研究较为关注的是版本史、目录史和藏书家的个人传记,而少有对书籍与士人社会的深入研究。钱存训归纳了印刷术的功能和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存在“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他自己提倡的“相互影响论”,但在分析印本书籍与士人社会的关系方面则缺乏相应的深入研究。周绍明的这本著作,通过概念的引入加深了我们对传统中国士人社会与印本书籍关系的认识。周绍明认为,对书籍使用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帝国晚期国家和市场在满足读者和藏书家需要方面存在相对局限性的许多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知识共同体(本书原文为community of learning,译者译为知识共同体。因为本文没有出现epistemic community 的概念,这一概念为知识共同体,而community of learning 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译者将其译为知识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概念本身的严格性,但也对我们认识古代士人社群有一定的帮助,故此本文对以上两个概念不做深入辨析)的一些有趣的看法。
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重要类型,其主要特征是:有一套共享的信念,这是共同体成员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基础;共享的因果信念,这来源于他们对其所属领域相关实践问题的分析,并用来解释可能的行为与预期的结果之间的关联;共享的合法性标准,即在共同体内部对于相关的知识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群体成员有共同的行为实践过程;知识共同体是独立的,它并不屈从政府的权力以及威权。在本书中提到的community of learning 按照周绍明的说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在国家机构之外形成的对学问共享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则与书籍的获取困难以及政府对书籍的控制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极力促成了知识的非人格化。
一部书、一部手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这种共享学问的方式最终在传播和保存知识的过程中倾向于鼓励一定程度的知识的非人格化。书籍的印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相同的副本,以供传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知识的非人格化,即它与其创造者的分离,上升到主导地位,原因在于印本本身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最终到达藏书家和其他读者手中时,作者并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彼此之间也不相识。这些人希望根据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印本中的观念和信息,完全可以用原作者想象不到的方式变成他们自己的。
伴随着知识的非人格化的过程的是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占有与共享,如果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这种非人格化的知识并掌控了权力,那么就形成了伊拉斯谟所说的文人共和国(a republic of letters)(伊拉斯谟认为欧洲近代早期确立了文人共和国),与之类似的,周绍明认为中国有初具规模的“知识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虽然这个概念只是在描述一种理想,而不是1000至1700 年间中国学术世界的现实。一个广大的学术上的“知识共同体”在明末仍是一个远未实现的理想。最多有一些凝聚力不同的小圈子,其成员享受着借阅尊长或朋友藏书的程度不同的权力。这些圈子以血缘、朋友和同乡为中心。
这一共同体共享着对文字和书籍的尊重和一种近乎崇拜的信念。对于识字、识字者及其高尚生活方式的极度推崇,伴随着对印本这一作为识字能力及其社会地位关键象征的敬意的提升。比起明代的家族,清代的家族更经常地得到告诫要保有他们的藏书,以确保他们能够作为一个学术家族继续延续下去。似乎拥有和累积书籍的目的是释放一种紧张。有人甚至“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惶惶然如饥渴之于饮食”。读书甚至成为一种道德标识,一旦成为读书人就具有了某种道德的优越性,就如同周绍明引用陆陇其的话说所表明的“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除了把书作为一种社会和道德标杆来尊重之外,对书还有一种虔诚的、实际上带有宗教性的认识,认为书神圣性的东西。比如,孙从添就提出了书籍神圣性的观点:“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经籍会通》之“藏书记要”)学者和平民圈子的想象力和热情被其他两个民间宗教团体——惜字会和文昌崇拜——所吸引,它们提倡尊重书写和印刷的文字。惜字会最初在苏州地区形成,随后在整个江南和中国其他地区流行。尊重文字著述的习惯在这些团体内外广为传播。
 维系士人与非士人的知识共同体的另一元素是他们对书籍本身价值的判定,包括实用的和非实用的两个方面。这一共同体充满激情的看待读写能力和书籍本身,任何关涉文字和书籍的功能都被正面的夸大。识字、读书除了满足个人基本的精神需求之外,最重要的是给个人带来道德优越感和社会声望。由于知识共同体认为读书和学问对于培养个人的品味和鉴别能力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它们可能给一个人的事业带来机会,尤其是在科举考试和做官方面,所以读书和学问获得了荣誉和尊重。文字和书从体力劳动中纯化出来,成为一种拜物教,与书写和阅读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群体成为最值得尊敬的精英而受到礼遇。这不仅是对个人,而且是对整个家族而言的:对有些家族来说,尤其是那些无论在科场成功或失利,却能够将藏书维持数代的家族来说,这些藏书甚至有更多的意味:没有它们作为表征,他们对社会和文化合法性的拥有将会引起争议。 维系士人与非士人的知识共同体的另一元素是他们对书籍本身价值的判定,包括实用的和非实用的两个方面。这一共同体充满激情的看待读写能力和书籍本身,任何关涉文字和书籍的功能都被正面的夸大。识字、读书除了满足个人基本的精神需求之外,最重要的是给个人带来道德优越感和社会声望。由于知识共同体认为读书和学问对于培养个人的品味和鉴别能力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它们可能给一个人的事业带来机会,尤其是在科举考试和做官方面,所以读书和学问获得了荣誉和尊重。文字和书从体力劳动中纯化出来,成为一种拜物教,与书写和阅读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群体成为最值得尊敬的精英而受到礼遇。这不仅是对个人,而且是对整个家族而言的:对有些家族来说,尤其是那些无论在科场成功或失利,却能够将藏书维持数代的家族来说,这些藏书甚至有更多的意味:没有它们作为表征,他们对社会和文化合法性的拥有将会引起争议。
但这一知识共同体是脆弱的,它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因为印本可能逃脱了个人的牵系和作者的占有,但是他们在摆脱主人占有上肯定会有麻烦50。总的来说接近私人藏书是很受限制的,大的私人藏书非常排外,从它们那里借书更加困难。大多数藏书家对向有兴趣的读者开放其藏书的建议敬而远之。他们的文化中的“常识”教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政府的不作为和作为,又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决定的明智。这一切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书成为秘笈,插架之物成为私人财宝,不可分享。藏书家常常羡慕像天一阁那样有着高墙、护城河和书主人制订的规则保护的藏书。藏书家或者聚书人千方百计搜寻包括印本书在内的各种书籍,但是印本书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个人手中,它就从流通物变成了收藏物或者文物。所以就有了“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这是杨继振的一方印,钤在道光戊申蕴玉山房本《淳化阁帖考证》首页,文长达252 字)的说法。
周绍明的研究表明早期西欧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的情形类似,但他们在藏书上采取的是排他性模式,为了与之对抗,“公共”的图书馆逐渐显现,个人之间的学术资料的交换不断增多,各种鼓吹共享书籍的言论也渐渐流行起来,比如11 世纪初的一个拉比说: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的;13 世纪初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第六条戒律“不可杀人”的注释中写道:“不借书是一种自杀”。这些与同时期中国塑造藏书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模式似乎远不鼓励制度上的多样性。在中国,政府一般仅为官员和后备官员(即学生)提供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家一般限制其他读者利用和共享其藏书。无论是皇室还是私人藏书家都极力限制其他人对其藏书的使用,最简单的策略是除了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外,不向任何人暴露其藏书。正如15 世纪著名的苏州藏书家叶盛的《书橱铭》所说:“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了,惟学斆,借非其人亦不孝。”最终的结果是,一代到十代人积聚的家族藏书可能频繁散佚,图书易手成为常态,但无论是在旧主人还是新主人那里都没人保证或者鼓励这些书会向他人开放。而那些对书籍有着特殊情感的人们或者获得了死后的哀荣,留下一个坟头或者石碑供人凭吊;更多的人则成为默默无名群体的一员。
最后,伴随着雕版印刷书籍本身的消逝,传统的印本书走到了尽头,其中有些幸运者流传至今,其中某些静静地呆在图书馆或者博物馆柜子里,远离了喧嚣。与此同时,传统士人群体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共同体最终并没有形成,文人共和国依然在伊拉斯谟那里。
四、几点小问题
周绍明的这本著作给了我们反思中国书籍史、社会史的新的样板,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小的问题,比如:
周绍明说,在明代开初的这个世纪里印刷的重要史书很少,而且几乎都是官刻的,明初由私人印刷的史书很难找到。这个论点并不完全准确,比如明刊本《贞观政要》,在国内就有国家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分别藏有明初的书坊刻本。
周绍明说,3500 多年前,中国文字的创造帮助和强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使知识更加明晰和固化,使知识更成功地传播,并培育了知识的专家。关于中国文字创造的具体年代其实存在争议,3500 年这个时间点还有待考证,如冯时、廖志林就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3500 年这个时间点有较大差异。
另外一个问题是译本本身的问题,按照国内译本出版的惯例,该书将参考书目省去,节省了印刷经费,可是也为我们找寻相关资料留下了遗憾。(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