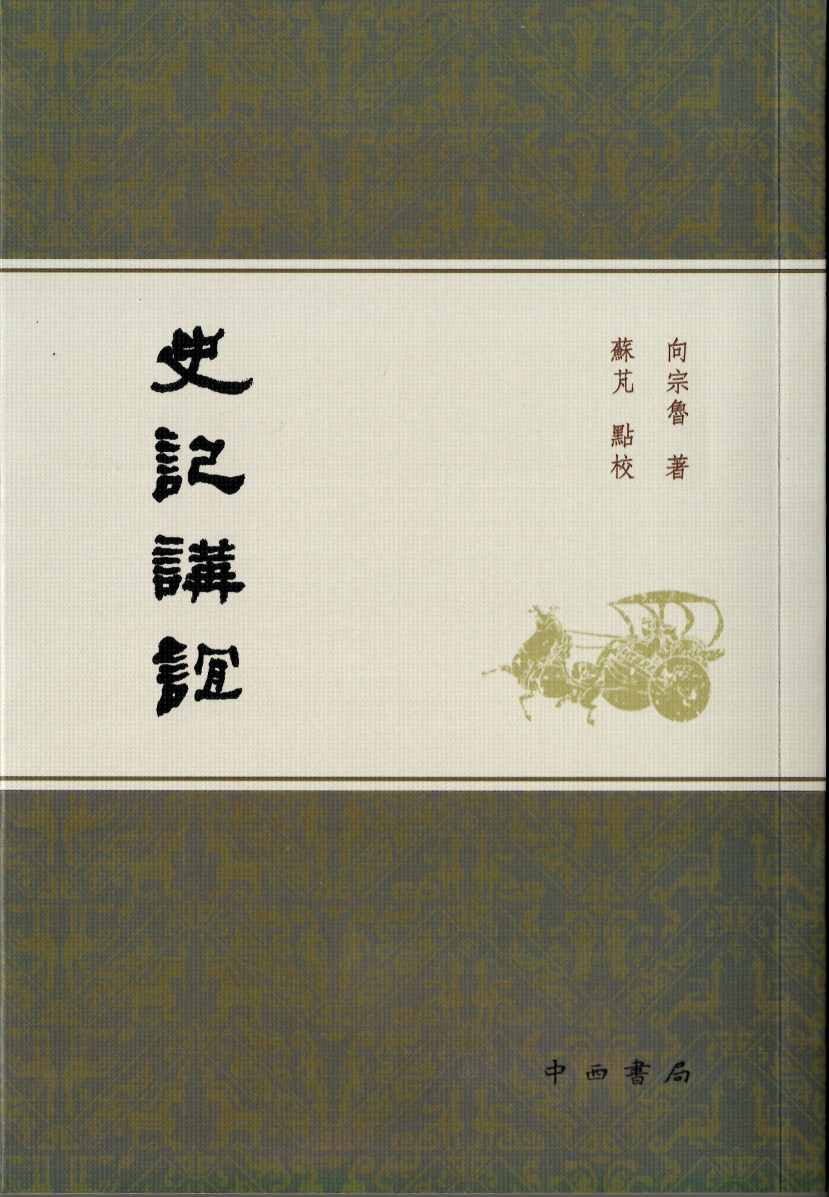|
按语
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2020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
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介绍近期由中西书局出版的民国时期学者向宗鲁先生的《史记讲谊》,该书由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芃发现、考订并点校整理。该整理本原为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石立善策划主编的民国古典学大系丛书之一,2019年冬天石立善教授不幸病故,这套丛书仅此一本得以出版。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转发苏芃教授为《史记讲谊》整理本撰写的前言,同时表达对石立善教授的纪念。
|
|
作者:向宗鲁 点校:苏芃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目录
向宗鲁先生《史记讲谊》的发现与整理
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或简称“国图”)藏有佚名《史记校注》一部,[1]笔者经过查考,发现此书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向宗鲁先生遗著。 向先生,原名永年,学名承周,字宗鲁,以字行世。1895年生于四川省涪陵县,祖籍重庆巴县,受业于文伯鲁(寿昌)、廖平(季平)诸先生,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并长期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41年11月去世,年仅46岁。先生博闻强识,刻苦笃学,自幼有“神童”之誉。[2]其著作等身,可惜传世的仅有寥寥几种,且多是殁后经弟子王利器、屈守元、杨明照等先生整理发表的,如《周易疏校后记》、《校雠学》、《月令章句疏证叙录》、《说苑校证》、《淮南鸿烈简端记》等。
图一:《史记讲谊》第一部分书影
图二:《史记讲谊》第二部分书影
图三:《史记讲谊》第三部分书影
一、国图藏佚名《史记校注》作者考证 判定国图藏《史记校注》作者为向宗鲁先生,主要证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史记校注》由大量札记组成,许多札记下都有“承周案”字样的案语,与向先生名讳吻合,且《司马穰苴列传》“晏婴乃荐田穰苴”条“承周案”旁批“向先生之名”。按覈《说苑校证》、《淮南鸿烈简端记》二书[3],其间亦多有“承周案”,可证当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史记校注》中有的版心处有“向授”字样,与向先生姓氏吻合。(参见图二)
第三,《史记校注》中有的版心处有“重庆大学印行”、“重大印行”字样,而目前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题有“巴县向承周编授”的《八代文讲义》(内题“选学丛录”)版心处亦有“重庆大学印行”的字样,可作类比。[4](参见图二、图五)
第四,根据向先生弟子回忆文章所述,先生曾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讲授《史记》。 一九三一年回重庆,应重庆大学聘,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即以《史记》《文选》《淮南子》《管子》诸书为教。(屈守元《精于校雠的学者向宗鲁》)[5]
一九三二年秋,先生去四川大学,执教中国文学系。次年春,即返任重庆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先生礼聘巴渝诸老师宿儒,开专籍专课。以文伯鲁先生主讲《毛诗》,陈季皋先生主讲《左传》,龚春岩先生主讲唐宋文,八代文及《史记》则先生躬任之。(何震华《忆恩师向宗鲁》)[6] 先生多识前言,熟精史事。举凡方舆典制,人物兴亡,莫不画地成图,抵掌可述。马班陈范,尤所究心。尝为生徒说《太史公书》,所造讲疏,精当难移,按条采录,即可成编。(屈守元等《巴县向宗鲁先生学行述略》)[7] 在重大、川大任课时,以《史记》、《管子》、《淮南子》、《文选》为教。简端批校,朱墨灿然。(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8]
综合以上四点证据,可见国图藏佚名《史记校注》当是向宗鲁先生遗稿,且极有可能是在重庆大学任教时讲授《史记》的讲义。另外,该《史记校注》后附有《说文解字讲谊》一卷。(参见图四)
图四:《说文解字讲谊》书影
图五: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八代文讲义》书影
二、向宗鲁《史记讲谊》撰写时间、性质、定名再判断 根据屈守元、何震华等弟子回忆文章可知,向宗鲁先生于1931年至1934年前后曾在重庆大学讲授《史记》、“八代文”课程,国图所藏版心写有“重庆大学印行”、“重大印行”字样的《史记校注》可能即此时的讲义,与前文揭橥川大所藏《八代文讲义》为同时之物。除了这点相关性外,《史记校注》性质为“《史记》讲义”尚有三点旁证:
第一,《史记校注》中有的版心处印有“中文系”、“中、史一年级”字样。(参见图二、图三)“中、史一年级”疑为“中文系、历史系一年级”的省称,大部分篇章的版心都有“向授”字样,结合起来看,当是教学讲义。
第二,《史记校注》中有多处批注记录。例如《司马穰苴列传第四》“晋伐阿甄”条下,“通典”二字旁有小字注“唐杜佑作”,“晏婴乃荐田穰苴”条下,“梁曜北曰”旁有小字注“作《史记志疑》一书”;又如,《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条下,“钱竹汀曰”旁有小字注“名大昕,清人”,“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条下,“初学记”旁有小字注“类书,徐坚著”,等等,这类涉及古代典籍常识的旁注,显然不会是“群经传记,洽熟无遗”的向宗鲁先生所记,当是学生或后人使用讲义时的批注。(参见图二)据此,亦可窥见该书性质为教学讲义无疑。
第三,《史记校注》后附有《说文解字讲谊》(此处“讲谊”之“谊”用古字)[9],二者既然合为一编,性质理当相同,亦可推知《史记校注》性质为教学讲义。
厘清《史记校注》撰写时间、性质、用途后,反观该书定名,“校注”之称似乎欠妥,可参考合编的《说文解字讲谊》,定名为“《史记讲谊》”。[10]因此,国图的著录应订正为:《史记讲谊》三卷,民国向宗鲁撰,附佚名《说文解字讲谊》一卷,民国线装油印本,一册。九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有圈点和眉批。 三、向宗鲁《史记讲谊》的内容特点及内部差异 向宗鲁先生《史记讲谊》为线装油印本,包含《五帝本纪》、《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太史公自序》七篇,用三种纸张抄写,据此可将这三部分析为三卷:
卷一是《五帝本纪》、《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合计四十五页(参见图一); 卷二是《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合计四十五页(参见图二); 卷三是《太史公自序》二十七页(参见图三)。
全书皆半页九行,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间有双行小注,行款较为统一,然而三部分字体却存在差异,是不同人誊抄的,可能并非向先生手书[11]。
从具体内容看,该讲义主要是对七篇《史记》“本纪”“列传”字句的训解、考证与校勘,三部分内容全以札记的形式呈现,“承周案”的案语贯穿全书始终。其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旁征博引,具列历代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张孟彪(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钱竹汀(大昕)《廿二史考异》、王怀祖(念孙)《读书杂志》等,并系连参照类书引文,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疏证。
其次,参考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卷三《太史公自序》里,征引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如“阬赵长平军”条下列有“日本枫山本‘阬’作‘拔’。见《会注》”;“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条,案语“《会注攷证》谓‘庆长本标记引刘伯庄云俭当作检,谓拘检人’,则唐人旧说已如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1932——1934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陆续出版印行,这部分讲义可能是在1934年之后写成的。
再次,不少条目没有案语,全引前人说法,甚至直接摘录几百字前人考证成果,例如《五帝本纪》“㠯征不享”条作: 洪筠轩曰:“《索隐》‘一本或作“亭”, 亭训直,以征诸侯之不直者。’颐煊案:《诗·韩奕》‘榦不庭方’毛《传》:‘庭,直也。’《国语·周语》‘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韦昭注:‘庭,直也。’《左氏·襄十六年传》‘同讨不庭’,‘不亭’即‘不庭’,古字通用。”
经查覈,此段文字与洪颐煊《读书丛录·史记》“不享”条[12]全同。这类情形在该讲义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又如《五帝本纪》“登熊湘”条全引成芙卿《史汉骈枝》八百多字,《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条,引梁玉绳《史记志疑》近千字、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李慈铭《越缦堂杂志》、朱一新《无邪堂答问》[13]各两三百字不等,而未下一句案语,都能反映出该书的性质不会是个人著述,而是教学讲义。
此外,对于三部分之间的内部差异,值得作些说明。三卷讲义之间互有参差,但无本质区别。参差之处如下:
首先,卷一、卷二里对《史记》正文关联的“三家注”(裴駰《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亦有疏解,标有“坿注”,第三卷主要是对《太史公自序》正文的疏解,不涉及“三家注”。
其次,前两卷引梁玉绳、张文虎、钱大昕、王念孙等人说法,皆称字或号,卷三全部直接称名。又,前两卷征引前贤旧说,只列作者,不具书名,卷三详尽标注书名。比如,引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卷二多作“梁曜北曰”云云,卷三作“梁玉绳曰”云云,段末用双行小注标“史记志疑”四字。卷三偶有标注引文起止,如“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条,案语引《史记索隐》与《尚书》孔疏,分别在引文之末标明“《索隐》语止此”、“《疏》语止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和讲义针对不同的学生有关,卷三的版心有“中、史一年级”字样,也许只是针对中文系、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教学讲义,所以对古人称名而不称字号,便于学生理解记忆,详注引文出处也是因材施教的需要。这些内部差异从另一方面证明《史记校注》必是教学讲义,因其为讲义,所以不求严谨统一,侧重追求实用性价值。另一方面,从这三部分讲义的誊写讹误来看,卷一《五帝本纪》篇尤多,后两部分较少。前面揭橥的学生批注记录,在卷二出现较多。 四、向宗鲁《史记讲谊》的学术价值 向先生《史记讲谊》在作为佚名古籍的前提下,已被编进《二十四史订补》,更彰显了其价值所在。笔者以为,其学术价值归纳起来约有三端:
第一, 对于研究《史记》的价值。
以《史记》研究而言,该书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解读《史记》的价值,例如:
《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条,向先生案语:“世衰谓末代君也。”
又如,“黄帝者”条,《史记》为何以“黄帝”开篇,前贤多置聚讼,向先生认为: 史公之书一以孔子为依归。《戴记》虽杂出汉儒,要多为七十子后学比所记,故史公据以为本。《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皆此志也。《五帝纪》赞曰:“孔子所传《宰予问帝德》及《帝系姓》。”《吴太伯世家》传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列传》曰:“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则史公述作之旨,已自言之矣。
再如,“湻化鸟兽虫蛾”条,向先生释作: 《说文》:“蛾,罗也。(在虫部)”又“𧒎,蚕也,飞虫也。或作䖸。(在䖵部)”二字义别,蛾即俗“蚁”字,郭注《尒疋》【《释虫》云:“蛾,罗。”】以为蚕蛾,非也。《礼记》“蛾子时术之”注:“蛾,蚍蜉也”。《左传·僖十五年传》“蛾”《释文》音“鱼绮反”,云“本或作‘蚁’”。《晋语》“蜹蛾蠭虿皆能害人”宋庠《补音》云:“蛾,音蚁。”以及《楚词 ·天问》之“虫蛾”、扬子云《长杨赋》之“蛾伏”、范书《皇甫嵩传》之“蛾贼”、《汉仲秋下旬碑》之“蛾坿”,皆其本义。【说详桂氏《说文义征》。】古音我声、义声皆在歌部,故“蛾”俗变作“蚁”,以别于“䖸”耳。【《大戴》“虫蛾”作“昆虫”。】。
诸如此类的诠释虽非确证,然而言之有据,至少提供了一种解读的新思路。
二是校勘《史记》价值。向宗鲁先生精于校雠,曾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开设校勘学课程,并撰有《校雠学讲义》。王利器、王叔岷等校勘学家皆从其问学。[14]《史记讲谊》中存有大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校勘成果。例如:
《孙子吴起列传》“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条,援引《韩子•和氏篇》“损不急之枝官”、《战国•秦策》、《史记•蔡泽传》“损不急之官”,结合文义校正“捐”是“损”字之误。
讲义中还有对三家注的校勘,五十余例“坿注”条目多有涉及,如《五帝本纪》“黄帝者”《正义》有“母曰附宝,之祁野”云云,向先生考校如下: 案:《初学记》九、《御览》七十九引《诗含神雾》曰“大电绕北斗枢,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又见《河图握拒》及《世纪》,而《文选•辨命论》注引《含神雾》“附宝”作“符宝”,未知孰是。《正义》“祁野”疑当以《诗纬》、《河图》、《世纪》作“郊野”。
此条据类书、古注引纬书证明“祁野”是“郊野”之误,较为可信。值得指出的是,向先生善于从类书、政书等资料中钩稽异文,又如《孙子吴起列传》“即三令五申之”条:“《六弢·教战篇》云:‘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今本作‘申之以三令’,从《通典》百四十九、《御览》二百七十九改。”可见他博闻强识,对与传世本不同的古书异文尤其敏锐。
第二,作为教学讲义的价值。
作为一份教学讲义,目前所见虽然可能未为全帙[15],但从现存的内容看,依然可以窥见向宗鲁先生教学设计的一些细节。比如,选读《史记》的篇次,五体中重点选择“本纪”、“列传”,《五帝本纪》和《太史公自序》一首一尾,都花了较多的篇幅讲解,这些现象应与向宗鲁先生的教学思想有关,对当代高等教育中的《史记》教学也具启发性。
讲义注重吸收当时新近的研究成果,如前文所例举,卷三里征引了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这部分里还使用了1916年王国维先生发表的《太史公系年考略》。
讲义常于细节处重点讲解学术疑案,比如,《五帝本纪》考证《史记》的书名问题,《伯夷列传》疏解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一事,《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为太史公等都着墨较多。
另一方面,难能可贵是讲义中保留了一些疑似学生上课时的记录与感想,呈现出民国时期文科教育的教学细节。如《司马穰苴列传》“晋伐阿甄”条: 《通典》百四十九、《御览》三百九十六引作“晋伐阿鄄。”有注云:“阿,今济阳郡东阿县。鄄,音绾,今濮阳郡鄄城县。”【张曰:“疑是《集解》文。”】案:鄄无“绾”音,“绾”乃“绢”之误。《通典》作“绢”,不误。《左·庄十四年经》:“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注云:“今东郡甄城也。”《释文》:“鄄,音绢。甄,音绢。”【一音真,或音狷,又举然反,或作“鄄”。】《襄十四年传》“卫献公如鄄”《释文》:“鄄,音绢。”《哀·十七年传》“卫侯自鄄入”《释文》:“鄄,音绢”,是也。《说文》:“鄄,卫地,今济阴鄄城。”【《襄十四年》杜注亦云“鄄,卫地。”】鄄城,是“鄄”为正字。疑《集解》本作“鄄”,《索隐》本作“甄”。
除了前文提到的《通典》旁注“唐杜佑作”这类常识外,“《通典》作‘绢’,不误。”旁注“下判断”,“《释文》:‘鄄,音绢。甄,音绢。’”旁注“一证”,“《释文》:‘鄄,音绢。’”旁注“二征[16]”,“《释文》:‘鄄,音绢’,是也。”旁注“三征”,“《说文》:‘鄄,卫地,今济阴鄄城。’”旁注“寻出根源”,这是对讲义考证“绾”乃“绢”误过程的解析,也许是上课随堂记录下的老师讲解内容。这条末尾处,还有一句批注:“说明鄄、甄两写之由。(考据文以实事求是为主,此节凡收三证,得鄄本读绢音之判断,又以《说文》总之,鉄案不翻,足为古籍校读之模范。)”这段话可能是学生上课听讲与阅读讲义的感想及评价。
总之,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讲授《史记》的讲义,该书对于研究民国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对于研究晚清民国学术史的价值。
关于向先生的著作,屈守元先生曾说:“《周易》、《左传》、《史记》、《管子》以及其他批校诸书,全都失去。”[17]可见作为及门弟子的屈先生是不知道《史记讲谊》存世的。因此该讲义的发现,对于研究向宗鲁先生与晚清民国学术史,以及日后整理向先生文集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史记讲谊》全书,常见向先生从《说文》出发,释读文字,尤其是借助《说文》研求本字、俗字,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折射出时代的烙印。
又如,向先生引《韩非子》几乎全称《韩子》,引《淮南子》某篇不称“某某训”,而用“某某篇”[18],这些细节都可反映向先生的学术素养与学术倾向。
再者,从向先生引书可以看出,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等晚近的研究成果,已经广为接受;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当时才印行不久,就已为中国西南地区学者教学引用。这份讲义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者而言,都将成为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回顾向宗鲁先生《史记讲谊》发现的过程,有两点启示值得重视:
一是考察佚名文献的作者,寻求内证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要细读文本,找出蛛丝马迹的证据,尽量做到见微知著。
二是民国时期学者的大量遗著、佚著尚散存于世,有待不断发现考证,如今发达的科技手段为此项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应当充分利用。
最后围绕该讲义的发现与整理过程略作说明,由于参加中华书局《史记》修订工作,《二十四史订补》是我的常用书,而其中的《史记校注》因是佚名作者文献,未有措意。直到2013年5月在认真阅读全书后,找出了与向宗鲁先生有关的线索,完成《向宗鲁遗稿〈史记讲谊〉的新发现》一文,6月底在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典籍、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上宣读,后投寄《文献》杂志,发表于2015年第1期,篇题应编辑部要求改成了《向宗鲁〈史记讲义〉考述》。2013年秋季,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为古典文献专业2010级本科生开设“古籍整理研究实践”课程,尝试把新发现的《史记讲谊》当作课程作业,分发给同学们作为古籍整理实践练习,没想到却低估了整理稿抄本的难度,作业很不理想,文字识读就有大量错误,在此基础之上,我重新校正一稿。2015年是向宗鲁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四川大学罗鹭兄编纂《向宗鲁先生纪念文集》将整理稿收入,然而遗留问题尚多。其后石立善兄听闻此事,说他正拟编纂民国古典学研究大系丛书,可以重新董理,单行出版。于是我又查覈引文,再加校订,并到国图覆案原书,将影印本漫漶之处一一落实,希望能够将这部湮没七十年之久的书稿完整呈现给更多的读者。因学力所限,整理稿舛讹之处实所难免,敬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正。承蒙川大罗鹭兄慷慨惠寄向宗鲁先生相关资料数种,研究生孙利政同学通读了整理稿,是正多处,在此并致谢忱。
2016年12月11日
附记:最近《史记讲谊》整理本已由中西书局出版,以上是该书前言。12月18日是石立善兄离世一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缅怀之意。 苏芃 2020年12月16日
[1] 被影印收入徐蜀选编《二十四史订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2004年由更名后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再次出版。 [2] 参见陈宛茵:《江城书香惠学人——记旅汉治学成名的向宗鲁教授》,《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8期。 [3] 详参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淮南鸿烈简端记》,刊于《新国学》第二卷,巴蜀书社,2000年。 [4] “重庆大学印行”的《八代文讲义》之所以目前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是因为1930年文伯鲁先生参与筹办重庆大学,向宗鲁先生应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5年5月重庆大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批准为省立大学,同年12月进行院系调整,将文学院调出,并入四川大学,向宗鲁先生及弟子此时又转入四川大学,因此重庆大学的讲义才会存藏在了四川大学图书馆。 [5]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9页。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巴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94年12月,第72页。 [7] 该文由屈沛仁、王利器、王振燊、廖履中、屈爱艮(守元)、王利仁合撰,屈守元执笔,1941年11月。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罗鹭先生提供。 [8] 向宗鲁:《说苑校证》,《序言》第9页。 [9] 《说文解字讲谊》中未能找到与向宗鲁先生有关的线索,向先生相关资料中也无讲授《说文》的记载,该书作者尚且存疑待质,疑或与向楚(仙樵)先生有关。 [10] 下文为了避免讨论纷歧,有时仍称“《史记校注》”,亦指本书。 [11] 比对向先生致庞石帚手札,与讲义三部分字体有别。 [12] 洪颐煊:《读书丛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3] 据笔者考证,李慈铭、朱一新两节引文或皆转自王先谦《汉书补注》,并不见于《无邪堂答问》,朱一新《汉书管见》有近似表述。 [14] 王叔岷先生在《我与斠雠学》中曾回忆:“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当时有位杰出的向宗鲁先生,他开讲《校雠目录学》,刚在编写讲义。我得到一点初步的认识,但不重视这门学问。”参见氏著《斠雠学(补订本) 校雠别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2页。 [15] 《伍子胥列传》“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承周案:““鸱夷子皮”非范蠡,说详《越世家》。”可见向先生讲义或有《越世家》部分,而国图藏的七篇中未见。 [16] 征,原稿如此,用“徵”字简化俗体。 [17] 向宗鲁:《说苑校证》,《序言》第10页。 [18] 宋代以前文献中《韩非子》多作《韩子》或《韩非》,后世可能为了与韩愈著作区分,渐称《韩非子》。《淮南子》篇名的“训”字,前辈学者研究或认为本专指高诱注,称引《淮南子》原文当言“某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