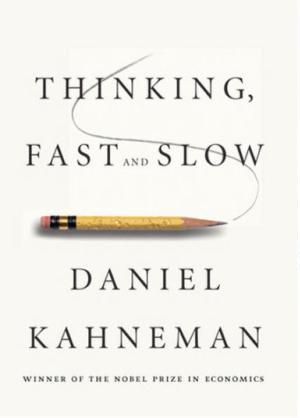|
按语
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2020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
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介绍近期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慢教授》,该书著者为加拿大女王大学英文系教授玛吉·伯格、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英文系教授芭芭拉·西伯,由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翻译。2019年秋季学期,田雷老师在文研院驻访期间,完成本书的初译稿。我们在此转发该书介绍,并附上本书结论一章“合作:在一起思考”,与读者共勉。
文研院一直提倡“涵育学术,激活思想”,我们希望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可以重新找寻逝去的人文传统,重建学术评价的标准。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慢教授》带来的启示值得深思,正如邓小南老师在该书的推荐语中所说:“自主地‘慢下来’,让学术过程更从容、回旋天地更舒缓,通过情感的融通和智识的韧性,激活学人交流对话与深度思考的能动力”。如此,学术才能健康发展。
|
|
作者:[加]玛吉·伯格 [加]芭芭拉·西伯 译者:田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目录
前言 导言 慢教授宣言
引言 第一章 不被时间所管理 第二章 教学与愉悦 第三章 研究与理解 第四章 同事与社群 结 论 合作:在一起思考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合作:在一起思考
言及大学环境的变化对同事关系的破坏,简·汤普金森曾写道,“你总不可能在简历中写上‘一次愉快的对话’”。虽然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探讨的,空无一人的院系走廊早已道出了真相,但《慢教授》这本书(可以确定,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学术简历中),却是对话结出的果实。整本书的写作,源头活水是本书两位作者之间的交谈,关于我们学者生活的体验,我们聊过很多很多。也正因为这场对话从未中断,不仅在我俩之间持续,又继而扩展到其他同道,这本书才能得以完成。同他人的交流也让本书两位作者清楚地看到,在大学公司化的浪潮内,如何做一名学者,不独是我们,许多同道也在寻求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同时交流也让我们认清现实,公司化的大学正在积极地制造障碍,以阻挠我们进行这种交流。科林尼曾著有系列文章,讨论了“学术研究……在当前所遭到的误解”(这些文章,后来重印收入在《大学何为?》一书内),有次谈及这些文章,科林尼告诉我们,“在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大量的读者给我写信,言辞之间,心潮澎湃,且来信之多,超过了我此前全部写作的回应。而且,在他们的信中,所表达的不仅有支持,还有一种我只能称之为‘欣喜’的情感——欣喜地看到,竟有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而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学术机构内,这样的信念却只能维持惨淡经营”。我们的经验也很类似,正是这种初心,激励我们将这本书写下去。写完它,尽管我们也知道,对抗机构文化潮流的逆行必定会带来令我们尴尬的代价。
在合写这本书的时候,两位作者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投身各自的写书计划,对我们来说,那又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经验。我们经常互诉心声,合作的经验让我们更快乐,更“放松”(在此借用“慢运动”的概念),想想我们此前所承担的任何项目,无一能及。甚至还不止如此,本书的两位作者都认为,若我们只靠单打独斗,也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于是,我们开始反思,《慢教授》的写作与我们单人独著的写作之间有什么不同,这时,一些关键的线索就浮现出来了。而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得益于前一章所述的“聚拢的环境”。将学术合作比作一种聚拢的环境,就会引发共鸣,呼唤关爱和保护。这表明,有些困难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我们要经受磨砺而信念不改。这也将产生希望,观念应当得到保护,加以培育,而不是被任意否定,丢在一旁;学术训练让我们往往善于否定,但传统的“严厉”观也需要被做出某种检讨。
 《慢教授》书影
我们都知道,写作可以说是很难的。总有一些挑战,不可避免,也无从躲避,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写作者的停滞、拖延、疑问、疲惫,以及自责。近年来,大学风气发生了诸多变化,既加码了对科研“产出”的期待,同时又加重了整体工作负担。这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面对着更紧迫也更具体的教学和行政要求,学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难抽出空来。对于上述这些压力,本书作者显然也无法免除(我们的编辑可以证明,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超出了一开始的预期),但我们对这些压力的体验却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写作项目,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遇到压力时,我们可以彼此交流。有人听你说,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用把这些感受憋在心中,或即便我们要暂时积压情绪,也不用等太久。合作缓冲了羞愧的能量。布林·布朗,一位研究羞愧感的权威学者,曾出版《纽约时报》畅销书《不完美之美》(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在书中,她将羞愧定义为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或者执念,认为我们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不配得到爱,也注定找不到归属”。根据布朗的研究,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种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羞愧感……只有一类人,他们没有体验过羞愧,也就缺乏同情的能力,不懂得人性之互连。”而且,即便我们所有人都有过羞愧的感受,但“我们却都害怕去讨论羞愧”,于是“我们越不去讨论羞愧,它对我们的生活就有越多的掌控”。如要培养出“面对羞愧时的坚韧”(因为没有完全治愈的方案可言),布朗写道,我们就必须“识别出哪些信息和期待会触发羞愧”,“通过用现实去检验这些信息和期待,练习批判意识”,“打开心结,把[我们的]故事讲给[我们]信任的人来听”,以及“多说……并多用‘羞愧’这个词”。虽说布朗的书并不是写给学术界的(不过她随后的一本书《勇敢做自己》,就提到大学文化存在着使人羞愧的基因),但我们不难借用一下她的定义,将它适用于学术界的具体语境。不妨跟我们念一下:“所谓学术羞愧,就是那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或者执念,认为我们不够聪明,或者没有能力,比不上我们的同事;认为我们的学问和教学都不够好,也比不上我们的同事;认为我们在某次会议或报告会上的评议不够精彩,还是比不上我们的同事。所以说,我们没有资格,不配加入卓越头脑的俱乐部。”但诚如雷蒂格对我们的提醒,羞愧是无助于写作的;事实上,写作者若不摆脱羞愧之感,甚至会无从动笔。
我们很幸运,能体验到这种聚拢的环境,其根基,在于信任。本书的两位作者都受过告诫,能不合作就别合作,我们当然听说过许多关于合作的恐怖故事,从因工作风格不同而受挫,到心头生起的剥削感。事实上,有人甚至这样警告我们,正因为我们是至交好友,所以不要合作。我们的经验,已经否定了这一切。我们相信,《慢教授》的合作之所以能做到善始善终,正是因为两位作者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而这是我们经年累月的交往所形成的。在我们眼中,对方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在某个学术问题上的一种“位置”,或者是学术网络中的某位能用得上的“联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彼此都更有耐心,当生活琐事或工作压力导致对方延期交稿时,我们也有更真诚的同情理解。原来我们相互给予的理解和关爱能激发出我们最好的潜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让我们在面对学生时能有更多的同情理解。我们不仅相互鼓励,激励对方保持写作的势头,而且彼此宽容,允许对方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当作一种正当的目标。对于学者来说,这种平衡是尤其脆弱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研究题目越是有信念和热爱,就越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画出一道分界线。而且,这意味着我们是真正在互相倾听。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卡尼曼评论了他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的合作:“其中一大乐趣就是……在我的想法还模糊不清时,阿莫斯总是能看到其中的观点,他所发现的,比我当时想的还要清楚得多。”什么是真正的合作者?就是在恐惧和焦虑很可能抹杀某一观点时,他能挖掘出这一幼弱观点的潜能。能与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合作,可谓天赐良缘——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就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你来我往,完成了这本书。当一位作者认为某一观点或句子讲不通时,她可以如实告知另一位,但又不至于像同行评审那样经常把对方压垮。我们之间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才使得意见交流的开诚布公得以可能:我们之所以彼此倾听,是为了去理解,而不是如学术训练所指示的,要去寻觅他人的缺陷。而理解对方,发现其力量所在,同样可以产生好的作品,并不是非得要吹毛求疵。
《思考,快与慢》原版书影
重读《慢教授》,我们发现即便在合写的章节中,也不乏某位作者独自完成的段落。虽然如此,我们做过的报告,以及这本书,却可以说是我们的(ours)。在这本书中,太多的部分(比如说引言),我们早已记不起也分不清哪里是谁的贡献;我们坐在一起,互相完善对方的句子。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论述时间管理的那一章),最初的写作是由我们分头进行的,在各自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后,我们再一起进行修改。到了教学和科研那两章,我们各自认领一章,基本上是独立完成的。一方面,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两章之间可谓心意相通,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发现,这两章是整本书中最难写的部分。我们甚至意识到,在各自独立写作自己的那一章时,我们会把对方变成我们“内心的恶魔”,或者陷入某种恐惧,搞不好出版社的审稿人就会挑出我单独写的这一章,将之作为整部书稿最弱的一环。当一位作者感叹她的这种感觉时,另一位则如释重负,脱口而出,“我也是这种感觉!”
基于本书写作的经验,我们在此建议,为了让学术合作可以更好地进行,合作应当发端于下,起始于学者之间的交流,而不应采用项目经费拨款的模式,由上至下地强行推动。如范汉奈尔所言,公司化的大学崇尚研究集群与合作,这是对“硅谷模式”的仿效,关键在于把专业知识汇聚在一起,以此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若是转向学术合作,只是为了推进生产力,把科研过程变成一条流水线,那么这种合作很容易造成同事之间的怨恨:甭管有没有道理,参与合作的每位成员都会觉得自己做得“更多”,超过了团队里的其他人。让我们颇为感触的是,所谓合作,并不是要分切任务,以此“减少”工作。虽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但长期看来,这并不是激励合作继续下去的初心。什么是合作?合作就是在一起思考。在合作发端于这种精神时,我们的合作就能去挑战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反思学术界的重新男权化。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卡尼曼又一次谈到了他与朋友兼同事的合作,那情形在他笔下是如此美好,令人神往,“阿莫斯和我都感谢这段不平凡的好运,我们都知道,两个人的思考分享,超过了我们个人的头脑,而合作关系也让我们的工作既有成果结出,也随时欢声笑语”。这就是在一起思考——最美好的那种。
在一起思考的乐趣,对我们而言构成了一种保护,让我们免遭“快生活所导致的伤害”。回头去看,我们意识到,写作《慢教授》这本书,也是将“慢原则”付诸实际的过程,而且我们也有所领悟,过程和结果总是不可分的。放宽视野,“慢哲学”应做何解?诚如佩特尼对我们的提醒,它与其说是“在缓慢和速度之间的——慢或快之间的对比……毋宁说,对比发生在用心和分心之间;事实上,所谓慢,与其说是一种时间持续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能力,要能去区分,去评估,以及一种习性,要去培养愉悦、知识和品性”。心神不定和碎片化,是当代学术生活的缩影;我们相信,慢的理想可以让我们找回共同体的感觉,重新发现学术的乐趣——“友谊以及力量的交汇”——也正是这种感觉,支撑起学术界的政治抵抗。正如我们在本书开篇宣言内所憧憬的,慢教授总是有目标,并为之付诸行动,培育着情感和智识上的坚韧,抵抗高等教育公司化所带来的腐蚀。
 2019年11月,田雷老师在第七期邀访学者报告会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