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周五)晚19:00,“北大文研讲座”第33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 “以顶层概念整合中国经验:以政治统一体为例”。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徐勇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院长燕继荣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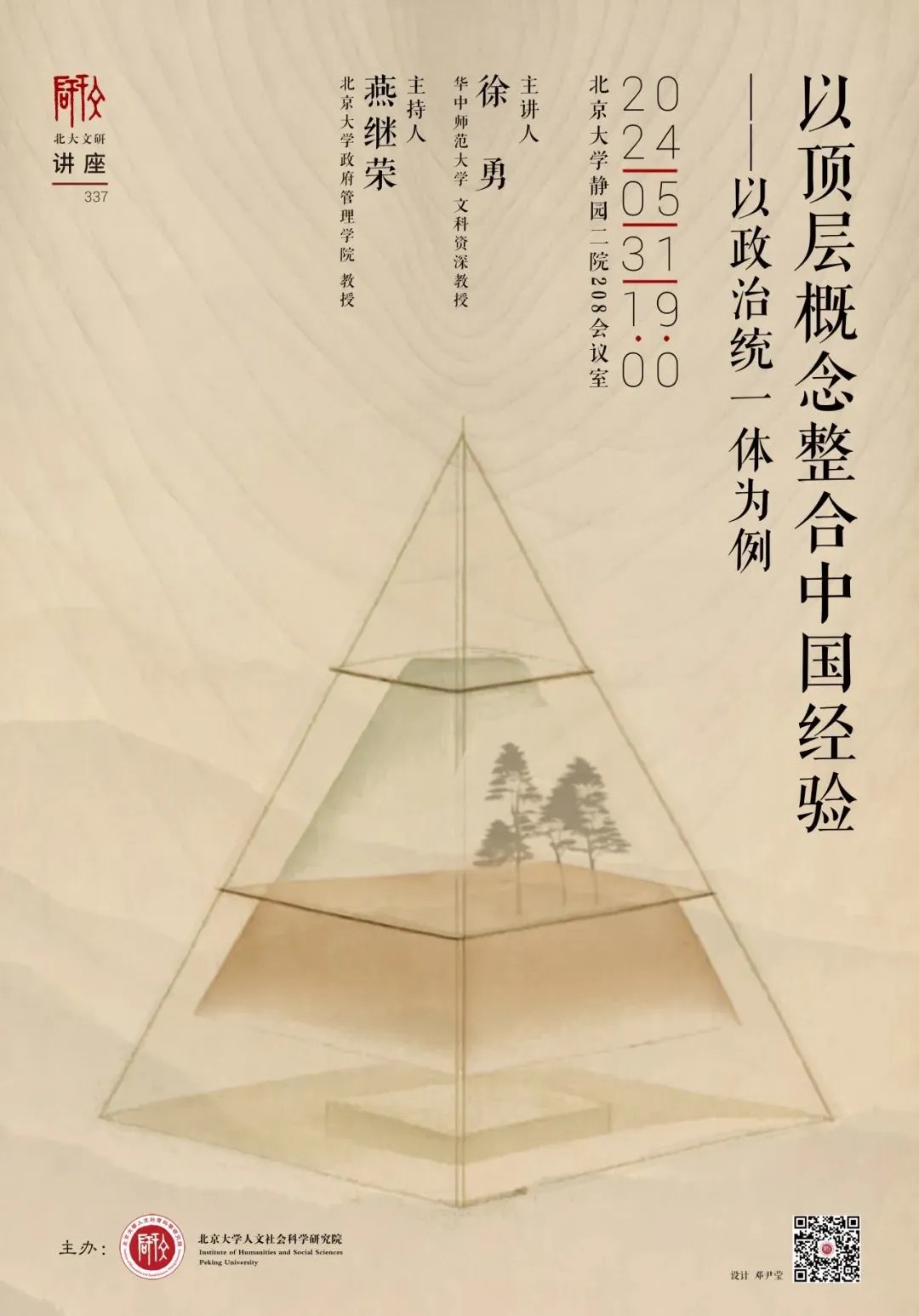
讲座伊始,徐勇老师点题,中国政治科学的理论成果要想走向国际社会,就需要建构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整合中国实践和经验。以“政治统一体”为案例,徐勇老师从六个层面探讨了研究顶层概念及其体系的路径。
一、将概念组合作为分析框架
徐勇老师首先明确了概念体系的定义。概念是对具体事物抽象而形成的知识。知识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的系统。在知识系统中,根据对事物的抽象程度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概念层级,并形成概念体系。顶层概念是概念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概念,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关系性概念,具有一般性、共识性、普遍性、包容性,是从各种“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共在”,比如“现代化”就是一种顶层概念。
顶层概念之下还有中层和底层概念,中层概念是在顶层概念之下由事物实体产生的实体性概念,具有个别性、价值性、特殊性、排他性,如“中国式和西方式的现代化”。底层概念是由事物的底层逻辑产生的,它是在分析个别性、价值性、特殊性、排他性如何产生的机理过程中产生的概念,主要探讨因果关系。“中国式和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如何形成的”就属于底层概念的范畴。
概念是对事物的认识工具和方法。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将各种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形态的知识整合为一体,形成结构化、清晰化和可共享的知识体系,使之成为一种认识和分析框架。它是基于问题研究的需要人为构建的,主要用于分析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机制。构建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目标在于使不同历史、文化和经验背景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并在同一个平台讨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明确含义和边界的知识共同体。徐勇老师希望它能够成为连接“知识孤岛”的“知识之桥”。
二、费正清提问及解答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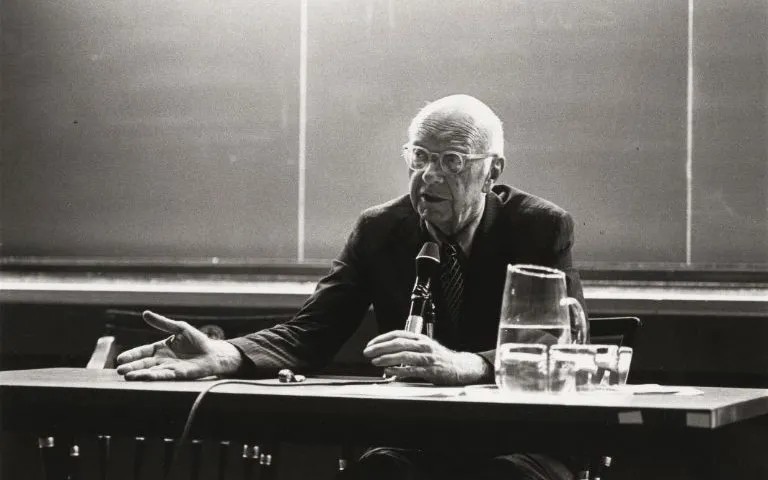
▴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作为一种顶层概念,“政治统一体”有助于将中国经验整合到普遍性学术体系之中。徐勇老师回顾了著名的“费正清提问”,即为什么中国始终维持了政治统一体,而同样疆土广袤、各地千差万别、人口众多的欧洲却没能做到?近年来的学界对此多从中国内部进行解答,从中国历史中发现和论证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面对各国的不同国情,只有将中国事实和经验置于普遍性的命题中,才能充分发现其价值及其因果机制。这就需要引入顶层概念体系的方法进行回答。
三、统一体:国家结构系统的顶层概念
有关国家结构的知识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知识系统。在这个知识系统中,由国家整体与国家部分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统一体属于顶层概念。无论各自历史背景如何,任何国家都会存在地域整体与地域部分的关系。统一体便是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问题的结构性顶层概念。它将多个地域部分合为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地域整体,并形成以整体为上的稳定制度体系和行为模式。
具体而言,统一体得以成为国家结构的顶层概念,是由其反映的问题、人们所讨论的议题和价值尺度的普遍性决定的:
1、统一体所反映的国家问题具有普遍性,即只要是国家,都会存在统一性问题。统一体是统一性的制度性规定和表达。随着公共权力将不同地方的人联结为一个整体,便产生了“多”和“一”的关系。这种关系会一直伴随着国家。
2、统一体作为人们认识国家的议题具有普遍性,即只要有国家,就存在人们对国家统一性的认识问题。即如何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获得统一性、一致性和一体性。
3、统一体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一价值是由国家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只要是国家,便存在国家整体大于或高于国家部分的价值。
四、统一体形式:
作为不同国家实体的中层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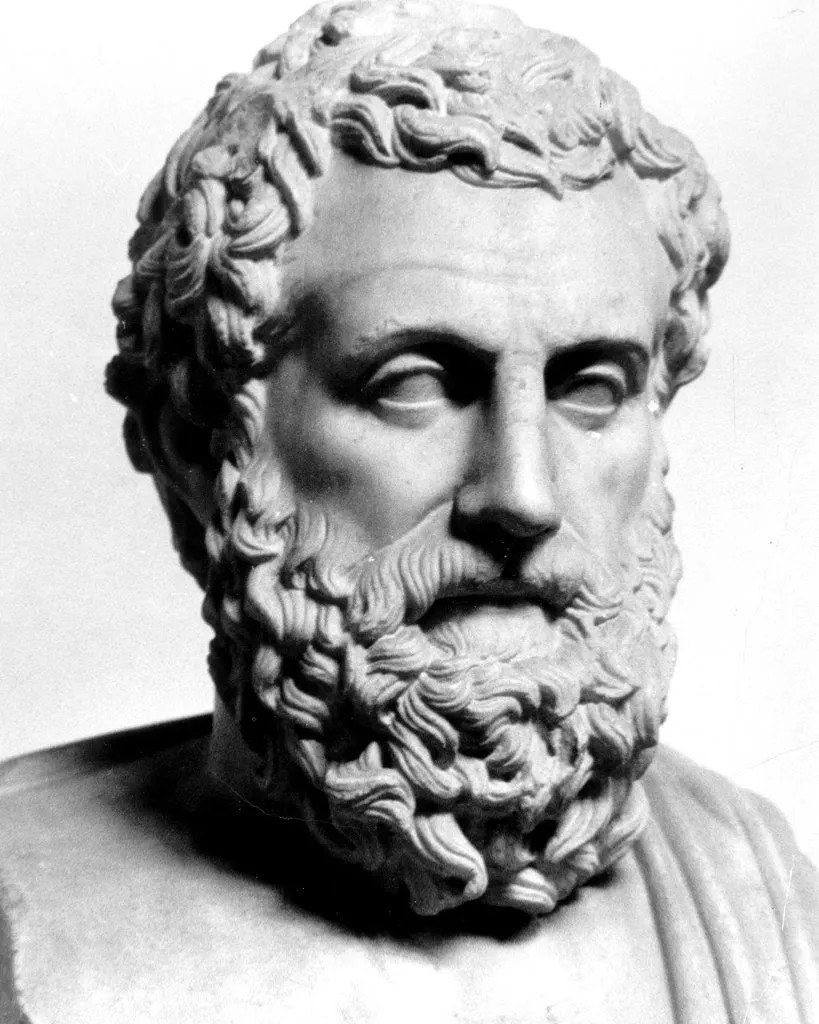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
国家整体与国家部分间的关系与国家地域和人口规模及特性相关。每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性质和配置、地域和人口规模及特性不同,造成国家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格局不一样,并形成相应的政治统一体形式。政治统一体形式正是人们认识不同国家实体对于国家整体与部分间关系的处理及统一体形式特点的中层概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讨论和列举的多种政体形式、中国古代的国王分封制、皇帝郡县官僚制、“定于一”“大一统”等,以及主权在民、神权政治等都属于中层概念。
五、统一体如何构成与巩固:底层概念
造成不同政治统一体命运和结果的原因是所谓底层逻辑,即决定事物结果的基础。由底层逻辑而生成底层概念。通过底层概念有助于认识政治实体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不同结果及其原因。徐勇老师随后重点讨论了如何从底层概念出发进行中国研究。
西方学界对中国作为持久统一体的好奇肇端于黑格尔,而在马克思处得到了光大。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支持者,马克思提出了有别于欧洲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徐勇老师将马克思的论述总结为:统一体是凌驾于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总和的统一体便是指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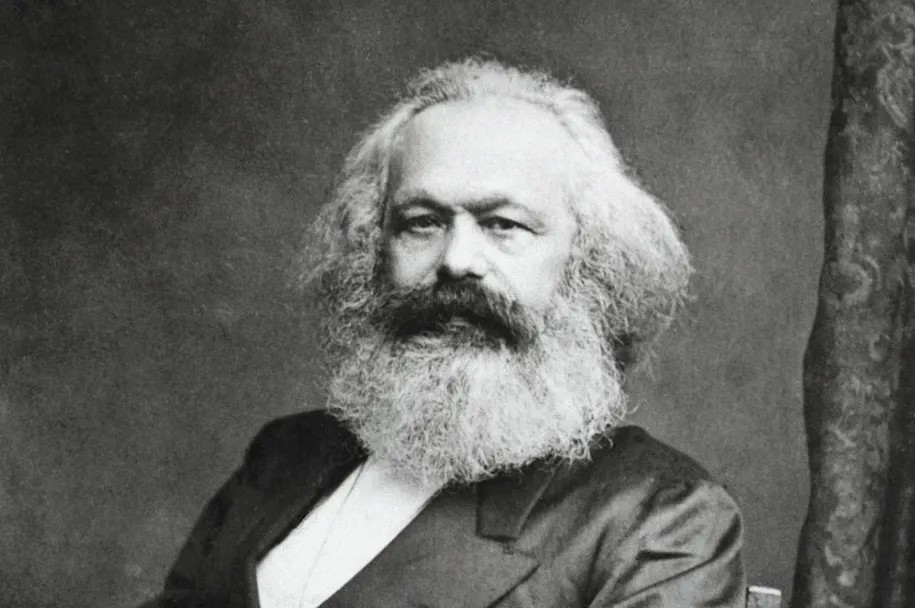
▴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
“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为中国形成稳定的政治统一体提供了四点内在的基础。首先,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分散的小共同体。正是通过凌驾于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力量,才将无数个小共同体总和为统一体。由此有了作为统一体代表的国王和皇帝。其次,各个小共同体得以构成总和的统一体的特殊力量,在于统一体是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统一体所有意味着任何地域部分都不能将地域整体分开。国家整体之下的人们可以占有,甚至世袭占有,但无法最终所有,“王土”仍然还是“王土”。统一的地域整体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再次,公共工程是人们生活必须的,也意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代表统一性的政府。最后,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有顽强的再生产属性。尽管凌驾于小共同体之上的王朝经常变换,但小共同体不会改变,继续为统一体提供社会基础。
由此,“国家所有、政府公共性和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是理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的底层逻辑,也构成了相应的底层概念。

▴
“大禹治水”画像石拓片
东汉
现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马克思视野中亚细亚形式的统一体,具有稳定性,也会趋于停滞性。但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除了决定性条件以外,还有治理性因素。即如何通过治理可持续地获得并巩固统一性,由此还可引进治理的视角。
中国政治统一体的底层逻辑是立足于土地的家户制。“土”是国家主权者垄断的领土,“地”是用于生产并能获得收益的田地,二者相互分离。商鞅变法中的“分家立户”,使中国率先从村社小共同体中走了出来。家户制既是由家长代表的小统一体,又是共同生活、共同情感和共同责任的小共同体,可以更充分调动个体家庭的积极性,能够为统一体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家户制是理解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不同于印度那样停滞和静止的底层逻辑。

▴
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
以家户制为基础,中国探索出一种“统分结合”的治理模式,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注意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的地域规模大,由中央直接治理困难,为此采用中央统一授权和地方分级治理的模式。周朝地方分治的治权太大,统一的王权衰败,造成数百年的战争。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官僚制,不同的官僚行使皇帝赋予的权力,守土有责,并经营地方。此外,中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大规模国家。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并不实行核心区域一样的制度,而是实行依靠“当地人管当地事”的间接治理。像这样的主权统一和治权分立,有助于在保持一定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获得可持续的统一性。
六、将中国经验带入普遍性
在完成上述五个环节的分析后,徐勇老师展望了构建顶层概念统领的概念体系所具有的学理和现实意义。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小规模和大规模统一体都有失败经验。尽管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多个地域部分与一个地域整体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即便是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着由整体再分裂的问题。对中国而言,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仍属于中层概念,并未克服与“小而美”国家模式的张力。只有通过将中国经验置于统一体这一顶层概念之中,通过比较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的独特价值和丰富经验,提出更具有包容性和竞争性的标识性概念。

▴
希腊雅典卫城遗址
最后,徐勇老师希望,构建顶层概念统领的概念体系可以避免过度以西方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两种片面学术倾向。既不能将西方视为普遍性,认为中国只有特殊性;也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的自我证成,将中国的特殊性置于世界普遍性之外。
讨论环节

▴
讲座现场
左为主讲人徐勇老师
在讨论环节,燕继荣老师赞扬了徐勇老师为中国学术思想“走出去”所做的探索。他同时也思考,在统一性的选择背后是否依然是现代性与传统性之争。现场观众提出了东西文明如何在顶层概念实现交流互鉴、所有制概念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顶层概念效力的边界、概念工具与田野调查的先后关系等问题,徐勇老师都予以了解答,并补充说明中国的特点是把政治能力植入家庭单位,从而纵向上链接起了国家统治能力和基层的家户。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