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6日晚,“文研讲座”第362期通过zoom平台在线上举行,主题为“非理性的理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得失”。本次讲座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理论和哲学教授莱纳·福斯特(Rainer Forst)主讲,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文研院副院长段德敏主持。

讲座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福斯特教授检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传统,并阐释了他的理论主张。福斯特教授认为:批判理论是哲学反思和社会科学分析的综合;它试图通过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辨析存在于社会和政治中的支配形式,并尝试勾画出克服这些支配形式的不同可能性,以实现“解放”。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发展出了一套对“社会非理性”(social unreason)的系统性批判,即那些被意识形态化地、至少是单方面地被包装为合理性形式(forms of rationality)的非理性,即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处于支配地位的理性的非理性”。因此,批判理论致力于同时理解非理性以及非理性如何、为何被认为是理性的,因此试图去想象或还原一个更加理性的秩序。如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所声称的:批判理论是一个“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关注合理生活境况的理论”。
福斯特教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立足于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观念,并将其和对社会力量的结构性、经验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以辨析社会中的合理性形式。特朗普近期的演说已表明,理解社会非理性的理论计划现今已愈发具有现实性。霍克海姆1947年的著作《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区分了客观主义的、形而上的理性概念和主观主义的理性概念。但霍克海姆没有发展出一套面向有关理性的批判理论。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批判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经由阿多诺、霍克海姆到如今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发展,以重新定义“理性”的积极意涵并以此来分析社会非理性。在《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哈贝马斯分析了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或策略理性的发展及其对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的入侵。这是对理性问题作的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理论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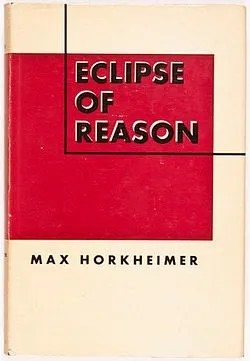
▴
《理性之蚀》
霍克海姆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
在规范性反思和社会科学分析、事实和规范之间,批判理论需要一些中介术语(mediating terms)以更好地反思规范原则与社会现实,反思社会中的各种理性形式——比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抑或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承认”(recognition)。对福斯特来说,这个中介术语是“证成”(justification)。证成有两个用法:其一是规范性的用法,即何种证成是合理恰当的;其二是描述性的用法,即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既有证成。在规范性上,福斯特将社会秩序中的规范性秩序视为“证成秩序”,由此来分析“证成的基本结构”,以描绘社会秩序的正当(justifiable)形式;在事实层面上,福斯特也试图提供一套理论工具以分析和批判既存的证成秩序。对福斯特来说,证成首要地是一个用来批判以及分析所谓“意识形态”(ideology)的术语。“意识形态”正是那些不能被证成(be justified)的证成(justification),但却指导着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这些证成,或由于事实错误、或由于在规范性上再生产和证成着支配,因此是禁不起批判分析的。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福斯特教授尝试在证成秩序的框架内就许多社会和政治哲学的概念作出梳理和再定义。福斯特表明,他的理论的核心是康德式的。他认为:康德对于“批判理性”的描述迄今仍是最为激进的;康德将理性形式化到某个程度,使得理性不仅是某种形而上真理的实质表达,也是所有互相作为规范性的、证成性的平等个体(justificatory equals)来尊重的自治者(autonomous persons)的内心声音。这是康德理性概念的批判性要义,也是批判理论应该坚守的思想精髓——若我们不坚持此递归性的理性概念,那么社会中被奉为合理的僵化形态(reification)便无法被批判。福斯特承认,证成的问题处于具体的文化与社会的语境中,但与此同时也部分地超越了这些语境。理性是一种批判性的“证成的能力”,帮助我们反思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这种批判并非把人带入本体的形而上空间(a metaphysical space of the noumenal),而是将我们和我们成长于其中的、视为理所当然且天经地义的社会实践保持一定距离,对现状提出疑问。

▴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
福斯特提醒我们,这种批判有可能是内含了特定价值的批判,即“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许多理论家忽视了内在批判的问题——批判,为何要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和原则?没有任何内在于某个社会的规范是绝对真的、正确的。并没有任何独立的原因以让我们坚守这些价值。因此,理性原则本身必须是批判的。若我们承认理性的原则是平等个体之间的证成原则,那么批判必须将实质性和程序性结合起来。内在批判所拥护的价值和原则,也有可能最终成为支配性的。正如阿多诺所言:“内在批判的局限便是:内在语境的法则,最终也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幻象。”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主义的浪潮中发展了他们的激进思想。
关于“正义”(justice),福斯特认为:既往对正义的讨论局限于将其和以下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人类需要多少以及何种资源以成就一个有善的生活的问题。在这种理解中,人类被理解为物品的消极接受者。福斯特认为,这种基于福利(welfare)、安乐(well-being)的正义理解是不正确的,是对正义概念的一种减损——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或一个政治机器来确保着人们有充足的资源(如医保、住房)以过上丰足的生活。这是一种专断统治,无疑和“解放”相悖。正义是一种德性,是社会和人的德性——作为正义的主体(agents of justice),人们集体地、自治地结合在一起以在他们之间主动地提出一种正当的社会秩序,而非被动地接受某些所谓“正义”的安排。正义是一种自治性创造,不仅仅是相互承认为证成性的平等个体之间的创造,也是将外国人视为证成主体(agents of justification)的人们的创造。这些平等个体需要给出自己的证成,以向政治体之外的他人证明他们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社会。这即是跨国正义(transnational justice)的概念,其建立在正当的多元性的基础上,也承认诸如人权等基本标准是人类社会不可侵犯的。

▴
《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关于“权力”(power),由于正义是证成性个体之间的集体创造,那么在这些平等个体间的权力及其分配就成了关键问题。福斯特认为,权力可以是物质属性的,也可以是精神属性的。权力可以产生一些特定形式的证成,封闭他人运用理性的空间,促使他人不带批判地接受抑或产生恐惧而被迫接受。因此,对于权力的批判必须把握对于特定形式的证成的批判。福斯特表明,他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批判并不在“真正利益”(genuine interests)的框架下展开。他的批判是康德式的,有关于“要求证成的权利作为基本权利”(a right to justification as a basic right),即证成性平等个体有权去质疑他们所服从的规范。福斯特认为,权利观念比利益观念是更加重要的,我们无需在质疑证成的过程中去寻找某种“真正利益”。
关于“异化”(alienation)问题,福斯特表明:“异化”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人以来的哲学史的重要关切。许多批判理论家认为,异化阻碍了人类以充分发展自我潜能的方式生活。这根植着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的哲学传统。福斯特认可这个声称的一部分,即异化意味着人生存在某种政治和社会境况中,这个境况使得人们难以成其所是。但福斯特并不认为,对异化的批判需要一种关于善的特定伦理观念。我们需要摒弃以上的看法而采取一种康德式的思维,即异化意味着我们无法成为规范性的平等个体,甚或由于意识被意识形态塑造而不认为自己是平等个体。福斯特认为,这种异化概念不仅对于青年马克思如此,对于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被证成的无力感(powerlessness),被证成的与他人、与自己的劳动的分离。

▴
《资本论》第2卷手稿
福斯特随后切入到他近年来着力研究的“宽容”(toleration)、“团结”(solidarity)和“信任”(trust)概念。他表明,存在着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宽容和团结形式。关于团结,福斯特表明,存在着好的团结形式,如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团结——也存在着不好的团结,如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团结。宽容也是如此。若我们并不被视为平等个体而只是被看作二等公民而被宽容,那么这种宽容便只是部分具有解放性且带有约束性。在宽容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反复地出现。对于信任来说,比如某个基于某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团体,其内部也存在信任。这种信任对于组织内的个体以及组织本身或许是正当的,但并不能推及其他的平等个体。因此,正当的宽容、团结、信任之形式必须非歧视性地承认个体的平等。简单地将共同体变得更具囊括性(inclusive)并不能实现平等而使社会更加正义。
最后,福斯特对自己的批判理论做了总结。他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对社会中证成关系的批判——在这些关系中,一些不正当的证成被生产出来。因此,我们所实践和采纳的证成以及生产着这些证成的“结构”,始终需要以“可证成性”(justifiability)作为标准。福斯特还讨论了社交媒体在当代的处境。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视作一个批判、探讨、争论、理性和立场交流的领域。而现如今的社会媒体则愈加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断地生产着刻板印象和错误声称。这无益于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和恰当的证成关系的形成。
评议环节
在评议环节,康德研究专家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教授提出,福斯特的理论批判性地检视了一些概念,但其本身的概念也需要被检视。威廉姆斯质疑,理论自身是否需有一个“容身之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曾因流亡而与学术机构疏离,但在当下假新闻泛滥、公共领域受到极端言论冲击的背景下,批判理论是否仅能依赖知识分子的个人思考,还是需要制度性的支持来保障理性讨论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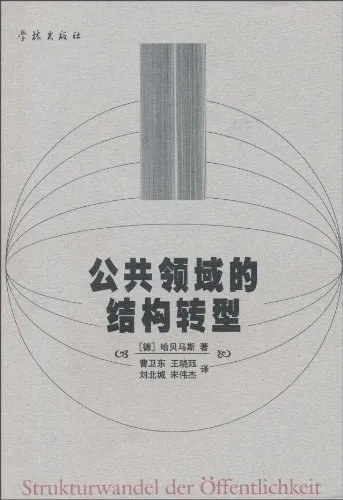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著,学林出版社,1999年
福斯特回应道,理性空间和独立思考始终和康德式的批判理性结合在一起。而批判理性只能是公共理性。阿多诺在上世纪60年代便和传媒联系紧密,他不仅在电台上发表演讲,也偶尔撰写政治评论。在那个时期,由于人们认为政治制度或多或少地陷于封闭,因此他们转向其他平台以寻求理性空间。大学是这些空间的一种,也是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的一个类型。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中对传媒持有着批判态度。但他现在转变了观点:电台、电视现在已经成为抵御假新闻和意识形态的阵地。福斯特完全认同威廉姆斯的判断,即应该重新思考所有的让公共讨论和证成交换得以发生的制度平台,包括大学、媒体。在如今的时代,这些平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福斯特教授也与听众就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理性和规范性秩序的关系、权力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