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9日下午,“文研讲座”第38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大时代转型与现实社会建构:一个知识社会学视角”,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周雪光教授主讲。周雪光教授在制度社会学、中国官僚体制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积累,此次讲座他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探讨了19世纪以来社会演变与现实建构机制的深层关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孙飞宇主持本次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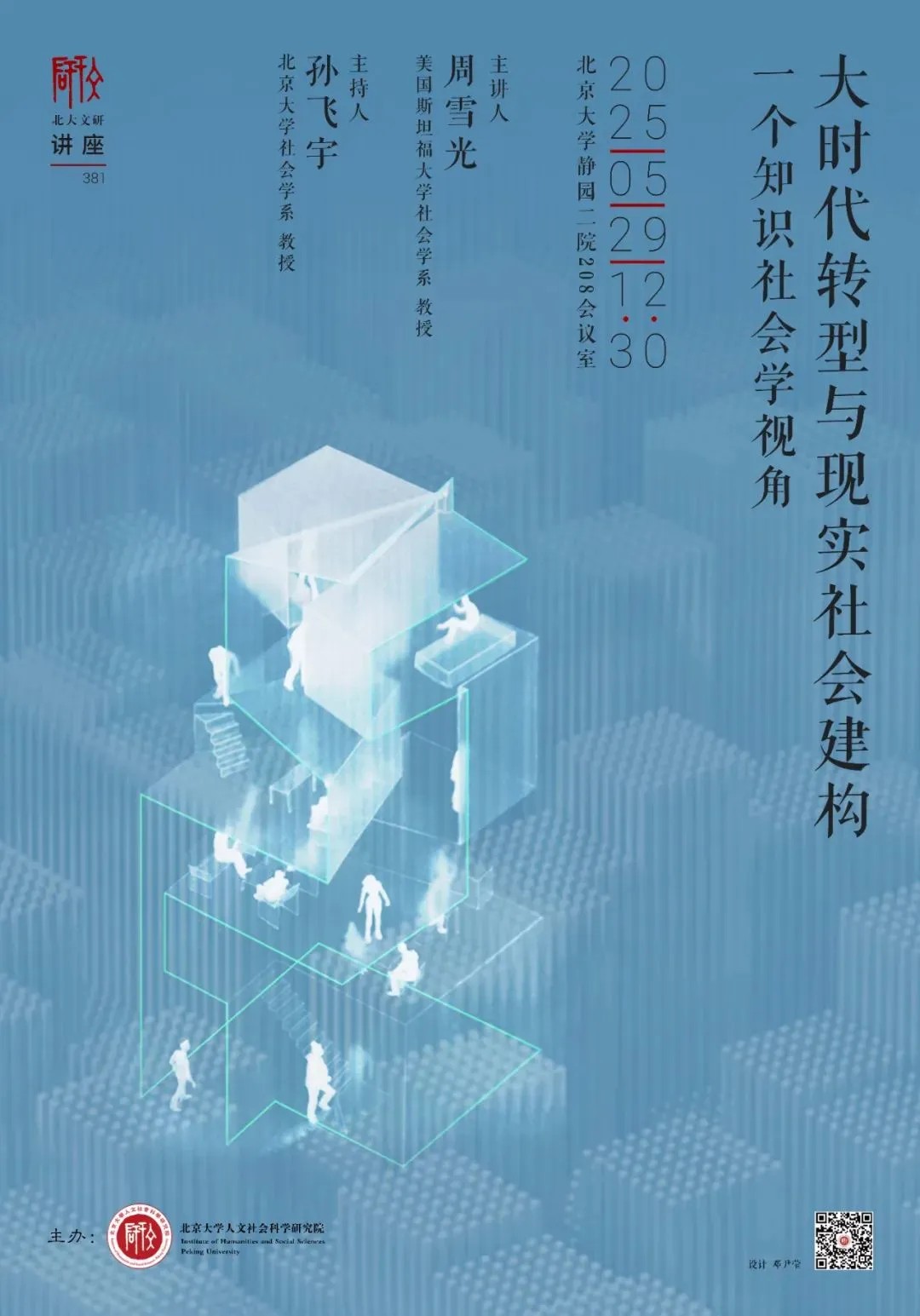
讲座伊始,周雪光教授指出,我们身处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正经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他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眼于社会建构机制的演变,围绕社会“兴起”和“转型”这一历史线索和“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这一学术线索,追溯近代以来社会的兴起、建构和演变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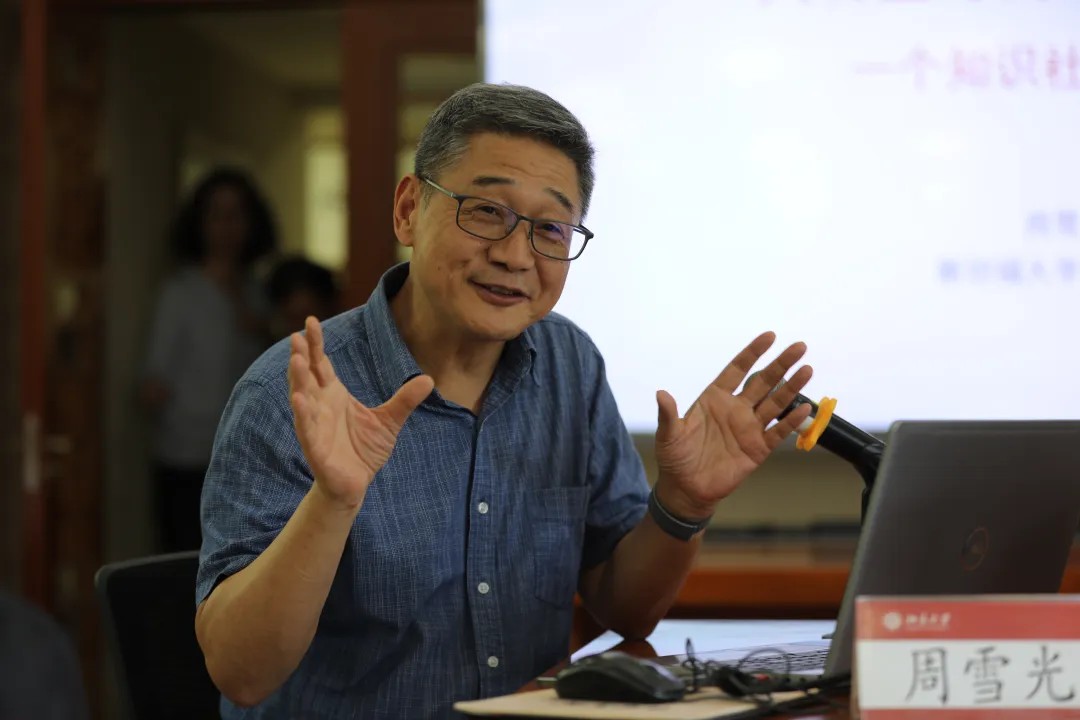
▴
周雪光教授在讲座中
首先,周雪光教授以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为主线,阐述了19世纪“中心化”的波兰尼时代,并介绍了后波兰尼时代的社会的几个演变脉络。周雪光教授将中心化进程划分为“传统社区-民族国家-全球化”的递进链条。前现代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附近”共同体,社会整合依赖习俗、宗教和地方性权威形成传统社区。资本主义兴起后,市场化和城市化打破地域壁垒,农民涌入城市,传统社区的情感联结和面对面互动逐渐消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社会,通过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信仰、种族等一系列象征资源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在从封建割据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中,市场自发秩序瓦解了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引发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在此过程中,国家扮演着积极参与的角色。一方面,国家建构和扩大市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各种法律保护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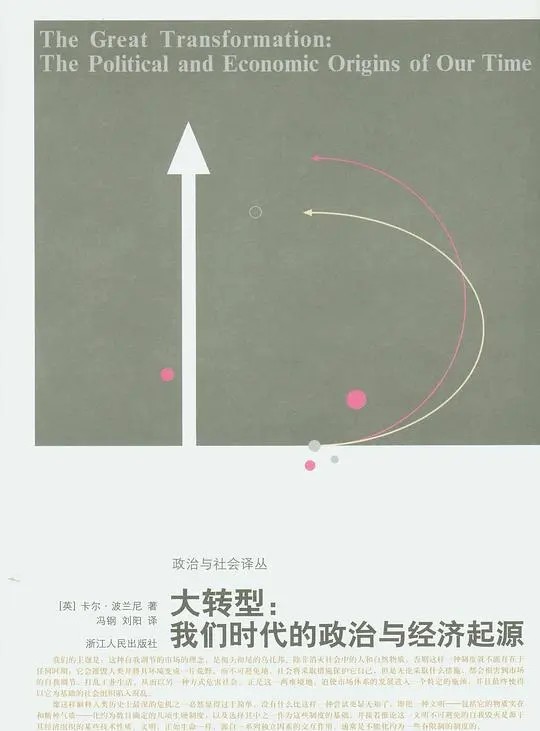
▴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卡尔·波兰尼 著, 刘阳、冯钢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科学理性和工业化社会的兴起,19世纪的组织、话语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进入了“去中心化”的后波兰尼时代。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中心化”的波兰尼时代和“去中心化”的后波兰尼时代高度互动,此消彼长,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社会。周雪光教授还讨论了现代性及其引发的抵制。在从“中心化”到“去中心”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也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民众以“主体”形式进入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与批判思潮瓦解了中心价值和权威文本,人在这个过程中解构了主体意识形态,推动了去社会中心和去宏大叙事的趋势。
接下来,周雪光老师以现实的社会建构为线索讨论了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演化。从社会学经典理论出发,韦伯提出社会行动基于主体间的意义建构和相互理解,这一观点奠定了诠释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的基础,强调意义建构的主观维度。随后,舒兹深化了“主体间性”的概念,指出共享意义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面对面互动,为社会建构提供了现象学的视角。伯格与卢克曼系统阐述了社会建构的“外化-客观化-内化”机制,揭示制度化将人为建构的符号转化为“客观现实”的过程。从知识建构的历程来看,19世纪的知识建构结果推动了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人们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20世纪中叶,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建构的态势,这一时期的知识建构主要围绕中心化过程中的国家建构与社会建构展开,并体现在学术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制度主义在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兴起,推动了社会科学对制度层面的深入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制度的“物象化”接受导致忽视了制度的人为建构性和个体在制度中的能动性。
随着知识建构的完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也沿着不同的走向发展。例如,经济学沿着中心化的趋势往前发展,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思想线索也受到了去中心化的影响,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转向中层理论和微观层次,强调对具体社会过程的机制解释。反观当下现实的社会建构,周雪光老师还特别强调了数智时代的语言在社会建构中的新角色,他引用了项飙教授关于“附近”的理论和邱泽奇教授关于“重构关系”的思考,并进一步指出,互联网虚拟社区的突出特点是自我选择,选择的结果与每个人的兴趣偏好密切相关。因此,理解现实的社会建构需超越19世纪的思想遗产,从传统社会“自下而上”的建构、现代社会“自上而下”的建构,转向数智时代的“平行多维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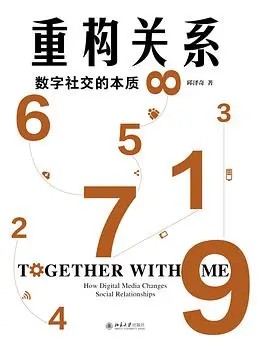
▴
《重构关系 : 数字社交的本质》
邱泽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最后,周雪光教授指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与传统社会很是不同的建构过程,传统研究无法完全解释“谁的现实?谁的附近?”等新兴议题。因此,未来的社会学研究需要直面现实建构机制断裂的挑战,在坚守经典理论洞察力的同时,以开放姿态拥抱技术变革与社会多元化,立足于历史的遗产,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组织形式,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从“解释过去”转向“理解正在生成的未来”。
评议环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孙飞宇教授就本次讲座提出了几点思考。他认为周雪光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除了针对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现实建构之外,社会学在不同的时代如何兼顾自身其实也是一种知识社会学,而这是关系到社会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进而他指出,“去中心化”的趋势使得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逐渐消解,甚至可能“消失”。对于社会而言,如果个人仅凭自我而成为自我,那么涂尔干式的社会学内核将遭受冲击,若“社会”不再是可测量的实体,社会学是否需要重新定义研究对象?正如米德提出“基于相对论的社会观”暗示需突破牛顿式机械论思维一样,当代社会学是否应构建更具流动性的理论框架?

▴
讲座现场
其次,对于“上帝已死”和“读者诞生”的这一观点,孙老师认为,当社会中的个体成为意义中心,传统社会学对“人”的定义也在逐渐失效。例如,数字时代的“同伴”可能是300公里外的网友,而非物理共在的亲友,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共享时间意识流和共同成长经验瓦解,个体在算法和商业逻辑的影响下看似实现了一种“自我建构”,实际上是被动地接受着外部塑造。进一步而言,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学问题,乃至于哲学问题是,当理性化使人成为“符号”,人能否仅凭理性建构意义?如果没有经典文本的滋养,仅有理性的人如何学会思考,又该如何定义思考?什么叫做思考?
针对周雪光教授所提出的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单向趋势,孙老师认为,当今社会学发展是要超越19世纪的视角,还是保留着历史的永恒循环,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除此之外,周雪光教授强调语言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但是孙老师认为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存在和不同的意义建构,随着大模型语言的发展,人的意义又该如何定义?
评议过后,现场观众围绕讲座内容提出问题,周雪光教授一一作出回应。本次讲座在精彩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