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之间”系列
2021年5月25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远主持。本次讲座系“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本次讲座主要关注早期罗马帝国(1世纪到2世纪末、3世纪初)的状况,所涉人群大多数为相对于元老阶层、骑士阶层、奴隶而言的“平民”,即拥有自由身份的普通人。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刘津瑜老师围绕两个问题——流动人口的经历(尤其是个体的经验),以及流入人口和接纳地区的互动——进行了重点讨论。
刘津瑜老师首先以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小塞内加所写的《慰母篇》为例,介绍了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对家乡和人口流动的态度。被卡利古拉皇帝流放科西嘉岛期间,为宽慰自己的母亲,小塞内加从几个层面论证了离乡远行的益处,如提供了学习哲学的机会,令他得以集中精力“思考更高层的东西”。小塞内加同时认为,很多人也出于公务、访友、求学、展示美德、出卖技能等不同原因处在流动之中,更换居所属于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
刘津瑜老师随即对文中出现的“patria”一词进行了重点分析,指出罗马人并未放弃“家乡”的概念,但对它的态度和道德判断较为复杂。在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patria”指的是“polis”,即出身的城邦,与个人的身份与权限息息相关,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而在帝国时代,“patria”的指涉范围变得更加宽泛。罗马帝国的形成对patria概念起到了解构的作用。如西塞罗所说,人可以有两个家乡——一个是罗马,一个是自己的城邦。在这一时期,patria成为一种比较流动的、不完全固定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构建自己的身份并得到认可、由此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空间。简而言之,家乡/故土概念在帝国时代依然存在,铭文等相关史料也反映出时人对家乡的情感和牵挂,其中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定义。
至于patria概念复杂性的另一方面,刘津瑜老师同样援引小塞内加《慰母篇》中的句子。在他的patria罗马城(其实他自己出生于西班牙,但在罗马长大),居住的外邦人比拥有公民权的罗马人还多,由此表现出“他者”的概念。从哲学层面来说,尤其是就塞内加倡导的斯托葛主义而言,人被赋予了变动的、不安宁的精神。也正是心中“天然的不安分性”驱使着他们更换居住地,将飘荡的想法发散到已知和未知之地。这一理论对思想和人员的流动给出了正面定义和哲学包装。但刘津瑜老师指出,需要为这些现象进行辩护本身已经表明,流动并不是一种想当然的状态;家乡和流动的概念在帝国时代均表现出复杂性。
随后,刘津瑜老师将话题转向不参与哲学思考的普通人,分析他们如何讲述自己流动的经历。据她介绍,早期罗马帝国人员流动的种类比较丰富,其中包括参军、商贸、求学等系统化的流动模式,而这些人口仍与家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哪一种流动,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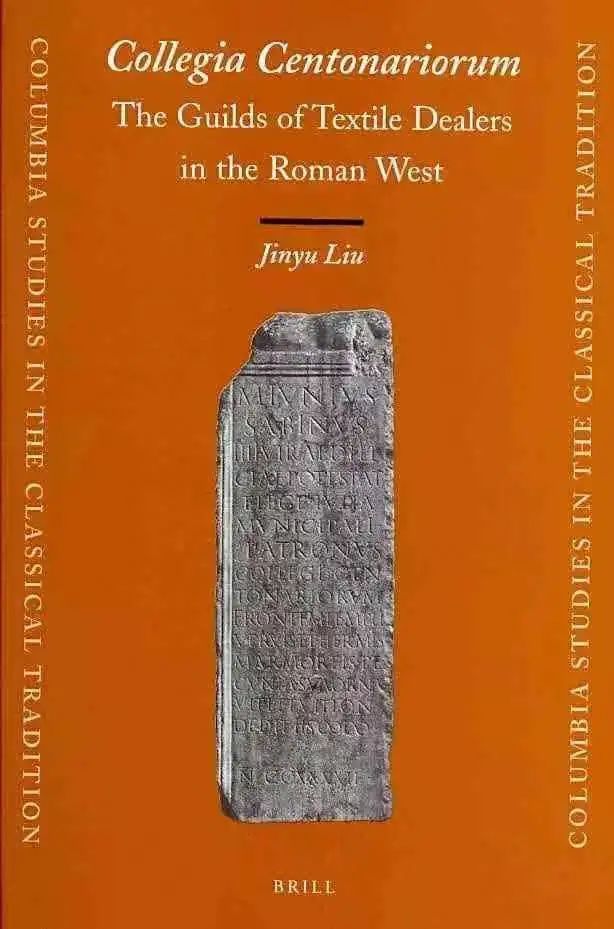
Jinyu Liu, Collegia Centonariorum: The Guilds of Textile-dealers in The Roman West,Brill, 2009.
刘津瑜老师首先以士兵的薪水单、墓志铭为例证,分析留存史料的种种细节,生动展示了罗马军队制度与人员流动。根据文字可以判断薪水单上的士兵属于辅助军;使用拉丁语记录信息、刻写墓志铭,则说明军队的拉丁语化和罗马化程度相当高,反映了士兵在军队中的切身体验。对他们而言,参军可能意味着语言乃至文化的变迁,军队的地域流动也是强大的文化流动。
接下来,刘津瑜老师着重分析了达奇亚之战部分阵亡将士的名录。名录记载了约3800名士兵的姓名与家乡,他们来自帝国各个地区,包括意大利、高卢、雷提亚、西班牙、埃及等。为阵亡将士刻名是帝国的官方行为,一方面是对个人的纪念,另一方面则是用地名构建罗马帝国的概念,说明征服战争是帝国的事业。征服达奇亚之后,帝国将大量人口迁移到当地耕种土地、建设城市,来自罗马各地的移民也加速了达奇亚的罗马化进程。
在介绍军队带来的人口流动之后,通过对以弗所出土的两篇希腊语墓志铭进行剖析,刘津瑜老师展示了另一种流动的类型——求学。两篇铭文均以韵文格式写就,或采用文化隐喻阐述了归乡主题,或说明死者本人与家庭的流动过程。雅典、罗德岛、小亚细亚、罗马城都是当时求学的热门地。著名诗人奥维德就曾被父亲送到罗马学习修辞,而所谓“学习修辞”有时是为了增添个人的文化价值,有时则是为了求取升迁之路。简而言之,以求学为目的进行的流动和对文化价值的追求联系到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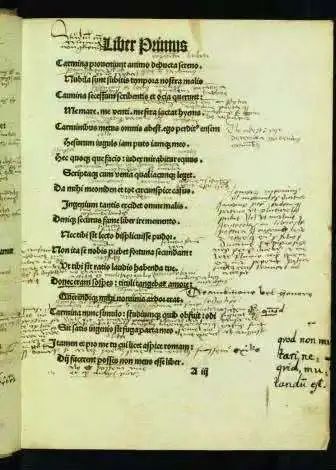
奥维德 《哀怨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约16世纪
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流动同样常见,且与罗马帝国的整体运作息息相关。刘津瑜老师引用了斯特拉波《地理志》(或作《地理学》)对(今)尼姆和纳博讷两座城市的对比,表明罗马世界的文化人在衡量地区繁荣程度时,会将外地人和商人的数量当作指标。她进一步援引公元1—3世纪的人口流动数据,概括两座城市流动人口来源的变化过程,证明人口流动和罗马帝国经济发展、城市消长之间存在相当的关系。
刘津瑜老师随即对罗马帝国早期人口流动的利好因素进行了总结。她认为,相对安全且便利的交通降低了陆上和海上的交通成本;罗马法对人口流动涉及的多种情况有所考量,相关规定虽然增加了一定负担,但也规避了部分风险,为公民节省了成本和精力。
相较于其他研究者,刘津瑜老师更关注人口流动在各种媒介中的呈现,特别是流动人口如何融入移入地,又在其中遭受了何种排斥。碑刻铭文作为被研究的史料,存在“发表偏差”等缺陷: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留下铭文,且这一公共媒介用于沟通和构建身份时,一般会记录值得书写的荣誉、身份的向上流动、参与的公共活动等正面内容,“不值得一书”的其余细节则容易被忽视。因此,研究者虽能从铭文中发现大量商人和手工业者,却无法了解他们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难以从名字判定“本地人”或“外地人”的身份,人口流动的方向也不明晰。刘津瑜老师特别提到,“释奴”(获得自由的奴隶)对铭文的利用频率较高,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他们在经济世界占据上风,而可能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用公共媒介构建自己的身份。因此,对于从铭文当中得到的结论,研究者需要多加考虑和打磨。

罗马公民内部的等级划分
根据高卢铭文记载的相关信息,刘津瑜老师指出,虽然人口流动的比例在数据中显得很小,但每个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个体,还需考虑人背后的网络——每个人的移动都离不开社会经济资源的支撑。刘津瑜老师列举了透过铭文辨识个人信息的方式,以几名衣商的墓志铭为例,简要分析了死者的个人生平、流动轨迹和社会身份,并进一步从纺织业者在高卢和意大利的移动轨迹出发,证明了罗马帝国的纺织业交易不是以羊毛为主,而是以成品为主。
对于在铭文中得以展现的行会组织,刘津瑜老师借用“贸易离散社群(trade diasporas)”一词进行概括,因为它们符合以下几项特点:此类组织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贸易促进经济福祉,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要素;离散社群是所在地的少数群体,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群体系统中的一部分。另一些组织则不用商业或职业命名,而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表明其身份。但这些组织可能只是换了种方式描述自己的存在,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分成“宗教群体”和“商业群体”。
刘津瑜老师列举了来自里昂的一些案例,以说明一人同时从属于多个组织的情况。除了跨地域、跨组织的平行关系,当时还存在“恩主”与商人组织之间的纵向关系。以罗马骑士盖尤斯·森提乌斯·雷古里阿努斯为例,他本人即是属于多个行会的商人,同时也是行会的恩主,作为中间人、担保人为组织及其成员提供帮助、福利和庇护。刘津瑜老师提到,部分学者认为行会、社团可以视作非正式的信任网络和声誉机制,降低商人的交易成本。但她同时对行会的正面意义表示怀疑,认为这些网络和机制未必一直有效——商人结社行为可以产生和维持“信任”这一社会资本,也可能对群体造成伤害,导致社会资本的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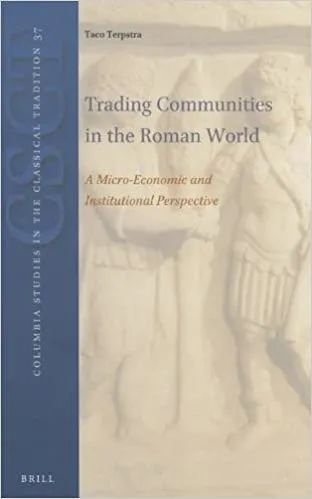
Terpstra, Taco T. Trading Communities in the Roman World. Leiden: Brill, 2013.
讲座最后,刘津瑜老师引用了亚历山大里亚驱逐“乡下人”(基本等同于亚麻织工)的案例,以呈现某些职业头衔如何成为“他者”的标签。相关纸草文书曾提及如何通过口音、外貌和性情、生活方式对“埃及乡下人”和“城里的/文明的(人)”进行区分。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除了融入本地社会,还存在遭受排斥的一面。在铭文等古代史料当中,研究者更容易看到成功的故事,但外地人遭受的排斥依然有迹可循,对家庭、行会、恩主等社会网络的描述正反映了流动人口的抗阻策略。
通过与线上听众进行交流,刘津瑜老师就部分问题作了进一步补充。对于恩主与庇护制度之间的关系,刘津瑜老师进行了区分,指出庇护制度中的恩主和门客属于心照不宣的不对等关系,具有非正式化、甚至婉言化的特点,比如用“友谊”这样美其名曰的言词来描述这种关系;而讲座涉及的恩主关系主要是个人和群体的正式关系,在“不对等”之中存在对等的要素。在回答不同类型身份标识的重要性问题时,刘津瑜老师表示,罗马公民的身份带来的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保护,还意味着个人或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乃至对帝国构建的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