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5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73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危机与再生:人类学田野方法、知识和伦理”。文研院学术委员、中研院史语所通信研究员王明珂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主持。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 系列讲座第五场。

讲座伊始,王明珂老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背景。他表示,至少在台湾学界,自己的学术身份不算是人类学者,也不是历史学者,甚至不是历史人类学者。这种现象类似于人类学中的“原生家庭”概念,即一位学者本科、研究生毕业于哪一科系,则被认为是这一专业的学者。但就个人而言,王明珂老师很早便对人类学感兴趣,并从1994年开始对青藏高原东缘的羌、藏族进行长期的田野研究。王明珂老师强调,自己对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知识和伦理的思考,是一种从学科外围、边缘角度观察得出的见解,有如在庐山之外看庐山。

▴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书影
接下来, 王明珂老师分享了两段自己进行田野研究的实际经历。其一,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些专家指出龙溪沟地区存在紧迫的安全风险,当地村民应被迁出,进行异地安置;而一些羌族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者及羌族长老、知识分子,则认为迁移可能使得羌族人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语言及认同。此事促使王明珂老师思考,当各个学科发挥其知识专长、以期重建一个遭受严重打击的社会,建构安全理想生存环境时,人文社会科学家除了以其知识告诫世人什么都不比失去文化及自身民族认同重要之外,还能做出怎样的贡献? 其二,王明珂老师曾在台湾主持一个农村社会文化调查计划,在访问台湾原住民的过程中,一位农民介绍自己采用传统农作法种植小米,但这一作法难以抵御虫害,更无法与价格低廉的进口小米竞争,经济上面临较大困难。当被问及为何不改变农作方法时,这位农民表示经济不重要,保存本民族文化比较重要。由此,王明珂老师想到,为何没有听到任何非原住民的农民谈保存文化比经济效益更加重要?在以上两个事例中,十分在意保存民族文化的均为少数民族、原住民。民族、文化概念与少数民族、原住民的知识捆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若要解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回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人类学发端于近代殖民帝国全球扩张的时代。西欧殖民帝国的航海者接触到广大世界中不同的人种、语言、文化、体质的人群,试图探索、了解这些人群的落后与原始本质,以此解释并合理化西方人自己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进步、优越地位。强烈的知识探求动机,促使许多探险家、传教士深入偏远的丛林、海岛。他们或是将这些地区的环境、资源、人群、社会、文化的相关知识带回西方,或是留在这些地区对当地人民展开他们自认为无法推辞的管理﹑教化与救赎使命。早期的人类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殖民地官员、军人、探险家或神职人员。在王明珂老师关注的羌族分布地区,便有一位名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的传教士,于1910年代在汶川附近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一本讲述羌人历史、习俗与宗教的民族志。

▴
陶伦士(Thomas Torrance)
陶伦士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即羌人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这一学说至今在一些基督教团体及犹太民族文化团体中仍颇具影响力。王明珂老师认为,陶伦士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受到了风行的演化论与传播论的影响。当时西方知识界普遍认为人类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在宗教信仰上,则是经历了由泛灵信仰到多神信仰、再到一神信仰的转变——一神信仰的基督徒站在演化的最高阶梯上。然而,陶伦士在深入的田野研究中与当地羌人建立起十分友好的关系;他爱羌族,并认为他们是本地多神及泛灵信徒中一支特殊的一神教民族。事实上,这是由于他在汉化程度较高的汶川一带传教,本地羌民接受汉族文化中的玉皇信仰,将玉皇大帝与本地一神祇阿爸木比结合在一起,于是后者便成了最高天神。陶伦士抓住这一点,认定羌人是一神教教徒。不过,在陶伦士的逻辑体系中,这套解释仍然存在问题:在诸多野蛮的多神教信仰信徒之中,为何会出现一群高贵的一神教信徒?传播论,即相信羌人是古代由西向东迁徙的以色列人的后代,填补了这一逻辑漏洞。无论是演化论还是传播论,均旨在合理化其时西方知识分子所认识的 “现在”——何以西方文明发达进步,而世界其他角落仍存在很多原始落后人群。演化论被用以说明人类如何一阶一阶地步向文明,传播论被用于解释一些文明与文化因素,如宗教、语言、神话、重要的发明等,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怀抱这两种理论的陶伦士,在田野观察中找到大量羌人是以色列人后代的证据,但实际上它们都很牵强。

▴
祭司在还愿回来的途中
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摄
王明珂老师进一步指出,以上陶伦士的羌族田野故事,正表现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它们分别是:(1)亲身参与实地调查的田野方法,(2)“他者”与“我们”相互映照的知识体系﹐以及(3)学术伦理问题。
一、田野方法
田野是人类学的根底。看起来,人类学家学习本地的语言,与本地人共同生活,在参与及交流中认识本地社会,如此产生的知识当然是非常深入的。但王明珂老师对此保持了一点怀疑。首先,人类学家依据自己的记忆写作田野日志,而记忆本身是选择性建构的结果。人对外界世界的观察、认知、记忆,常常受到自身主观世界、社会情境和学科法则的影响与扭曲。其次,人类学家虽然学习了本地语言,但掌握程度未必能够支撑对本地社会的深入认识。就王明珂老师自身的体验而言,即便是多年学习英语、可以和美国邻居沟通无碍,但若要研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仍然会有问题。最后,人类学家的深入观察、参与,往往是带着特定问题意识与理论系统的选择性观看,因此也会忽略一些不寻常的事物。

▴
建在山腰上的碉楼石室
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摄
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常常希望选取处于孤立海岛或偏远丛林中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将其建构成一个结构完整、各个制度功能分明且互补的社会文化体,最后写出一本漂亮、经典的民族志。王明珂老师整理史语所前辈学者在云南进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文物时,发现它们大多皆为渔猎工具,而几乎没有农耕工具;但事实上,云南的几大族群,如白族、傣族、彝族都有较长的农耕历史。可见,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注意到的,往往是符合他们心目中原始社会落后印象的事物;对这些事物的发现与陈列展览,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社会大众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讲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篇旨在通过台湾原住民的编织文化来探讨台湾原住民人观的论文。人观是人类学的概念,指人们对于自身存在于社会、历史与生死世界之间的基本想象与预设。然而,该作者研究的村落距离城市仅二十分钟车程,村民与城市关系密切,村中的编织者只剩下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如此建构一个与汉人完全不同的原住民人观文化,其实是很牵强的。此外更普遍的是,有些人类学者进入田野后,受到典范概念的牵引,倾向于寻找最地道的民族文化地区、访问最了解该民族文化的人,最后做出的研究同样会是刻板的。

▴
台湾原住民鲁凯族编织
二、“他者”与“我们”
相互映照的知识体系
所谓知识体系,包括人类学家从田野中得到的知识、民族志的书写,以及什么样的读者及其在阅读民族志时获得的知识。无论是民族志的读者还是作者,在不同时代的人类学发展中,始终存在一个“他者” 与 “我们” 相互映照的观点,影响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书写,也影响其读者的阅读民族志所得。早期人类学家的“自我”是进步、理性、文明的,被观察的“他者”是落后、迷信、有待文明教化的。在早期的民族志中,一个普遍且重要的主题是土著的宗教和神话,因为这一主题能够凸显“他们”的落后迷信、“我们”的理性进步。后来出现了一些旨趣相反的民族志,将土著所在的原始社会描述为远古、和谐、高贵的社会,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与这个“他者”相对的,是失去了淳朴自然本性且对此感到遗憾与惆怅的“自我”。还有一些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倾向于将“他者”建构为一个有着特定社会文化与人观的民族,与之相对的是永远生活在历史尖端、不被文化捆绑的“自我”。进入20世纪,西方人类学家开始以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中的原住民和少数民族为“他者”,关注其在国家霸权主义之下遭遇的文化与民族认同丧失危机,与之相对的是后现代、后殖民时代有反思性的“自我”。当下全球环境恶化与气候变迁危机下,又流行一种认识田野中落后他者的模式,那便是将原住民建构为与土地、自然关系密切、和谐相处的“他者”,与之相对的,是在全球暖化危机下渴望更好地保护地球环境的“自我”。

▴
电影《阿凡达》
在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中,存在许多此种“我”与“他”对比鲜明的想象与关怀,最有名的即是“冷社会”与“热社会”。“冷社会”一般指土著社会,其社会结构、制度、功能和信仰、人观密切结合,形成一个整体,鲜有变化。“热社会”则是“我们”不断变迁的现代社会。在“热社会”中,人们想法各异、相互竞争,事物多元驳杂,推动社会不断变化、进步。当然,已有人类学家对这一刻板、二元的想象进行反思。著名的人类学家科马罗夫夫妇(Jean Comaroff, John L. Comaroff)就曾提及:为什么我们用民族志来研究“他者”,而用历史来研究“我们”(指西方人)?总之,当我们阅读民族志时,要注意其背后的各时代人类学家之自我认同与文化想像,如此才能理解他们为何采取特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以及此中的偏见。
三、田野学术伦理问题
王明珂老师强调,人类学知识的说服力,在于其研究者深入的在地田野调查﹔我在那儿,你们不在,你们只能相信我。但问题也在此,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很难被他人验证。我们应该相信,民族志资料造假的情况非常少。然而普遍的是,人类学者不知不觉地选择性观看、选择性忽略。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反思社会学》一书中提出三种偏见:社会偏见(social bias),即由个人的社会身份、阶级、民族、国家、文化认同造成的偏见;学科偏见(academic bias),即一些被视为学科基本的方法、概念,从不被怀疑,但反而容易造成学科系统性的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指把学术视为精深、复杂的拼图版,学者着力于解决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不去关注现实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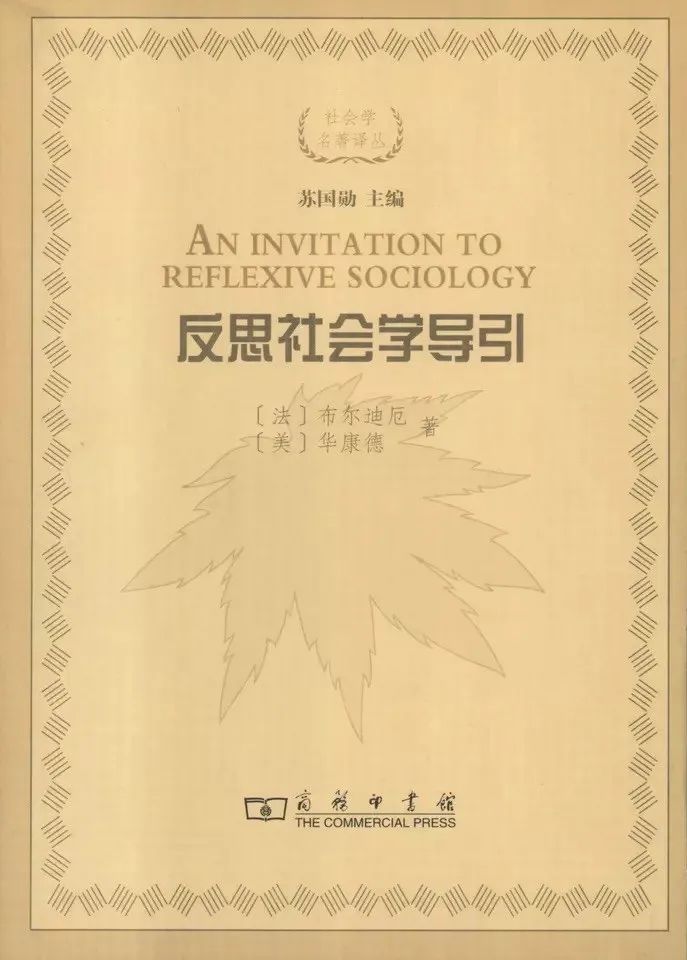
▴
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
商务印书馆,2015年
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伦理问题。首先,人类学家在研究对象的家里居住一两年,很可能影响后者的生活作息。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人类学家难免将一些概念传送给研究对象、促使后者重新认识自己;而这种重新认识最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人类学家或许并不在意、更无法掌握。其次,人类学家建构了文化概念,并给世人留下了文化只能被理解、但无法被改变的印象。事实上,一些文化传统可能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仅仅是理解其为何发生、但对其表示无可奈何,显然是不够的。第三,人类学、社会学为了保护其研究对象,建立了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制度,要求每个研究机构成立体制内审委员会,规定研究者必须向委员会提交研究计划、说明在田野中如何保护研究对象。然而,审查要求中最核心的两点——知情同意与资料去联结化,实质上都未必能对研究对象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所谓知情同意,指研究对象需要知道研究的内容、背后资金的来源、研究的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问题是,如果被研究者文化水平不高,或许根本无法理解知情同意书的具体含义。所谓资料去联结化,即研究结果不能让人追踪到信息来源;但在实际经验中,一位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接触了哪些人,当地人非常清楚,隐去真名不能真正阻碍有心的读者找到给他提供讯息的田野报导人。反过来说,有时 “使人无法追踪验证讯息来源”,反而成了扭曲与假造田野经验的正当借口。如此,田野研究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自然应受到质疑。王明珂老师指出,更糟的是,若我们细读IRB之各项原则及规定,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旨在保护研究对象的办法,反而是保护研究者及其机构,使其规避法律责任、求得道德心安的工具。
面对这些危机,人类学如何再生?对此,王明珂老师介绍了学界对于人类学田野、知识、民族志书写的反思性探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的影响。历史学促使人类学家不再将土著社会描述成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而是将其放到更大的世界体系,以及时代历史变迁之中。文化研究则改变了人类学过去对于文化之典范化、结构化、功能化的解释,而更多地对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例如,乔治·马库斯(George E. Marcus)在《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中指出,批判性的人类学研究应遵循两条路径:首先理解自己不熟悉的社会如何产生、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信奉何种宗教等;然后再用这一套逻辑,审视自己所在的、熟悉的社会。这种设想与王明珂老师之《毒药猫理论》一书的研究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明珂老师说明,他正是先发掘催生羌族毒药猫传说(文本)的社会背景(情境本相),而后以此与我们熟悉的中国或西方类似的 “女巫故事” 及其背后社会情境本相作比较,以对此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及现实有较深入的认识。

▴
王明珂《毒药猫理论》书影
王明珂老师最后强调,本次讲座所谈的危机,大部分是针对刻板、落伍的人类学而言,并不适用于最优秀的那批人类学家的研究。然而优秀的人类学者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学术目标﹕是否应一味追求高深而曲高和寡的理论?或着力于解决前辈人类学研究遗留下的一些让今日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仍深受其害的人类学知识问题?
评议环节

▴
线上会议现场
问答环节,王明珂老师就线上观众提出的如何理解凌纯声的湘西田野研究和黎光明的川康田野研究的区别、如何在田野调查中保护研究对象、人类学与历史学如何相互影响、民族志与自我民族志的追求与限度等问题作了详实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