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9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如何‘美美与共’——以历史社会学为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评议。本次活动为“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系列讲座第三讲。

讲座伊始,李里峰老师首先从社会史面临的两大挑战讲起。其中一大挑战来自于历史学内部,主要是20世纪末异军突起的新文化史,其强势发展的劲头盖过了社会史;另一大挑战则来自历史学的外部,即历史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冲击。基于此,李里峰老师本次讲座主要围绕社会史(社会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展开论述。
李里峰老师指出,大多数概论性历史社会学著作,都没有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而会将多位社会史家的贡献纳入历史社会学之列。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主编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一书中,介绍了九位历史社会学家。在这九位学者中,有五位通常被视为社会学家,分别是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但另外四位,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汤普森(E. P. Thompson)、波兰尼(Karl Polanyi),则更多被视为历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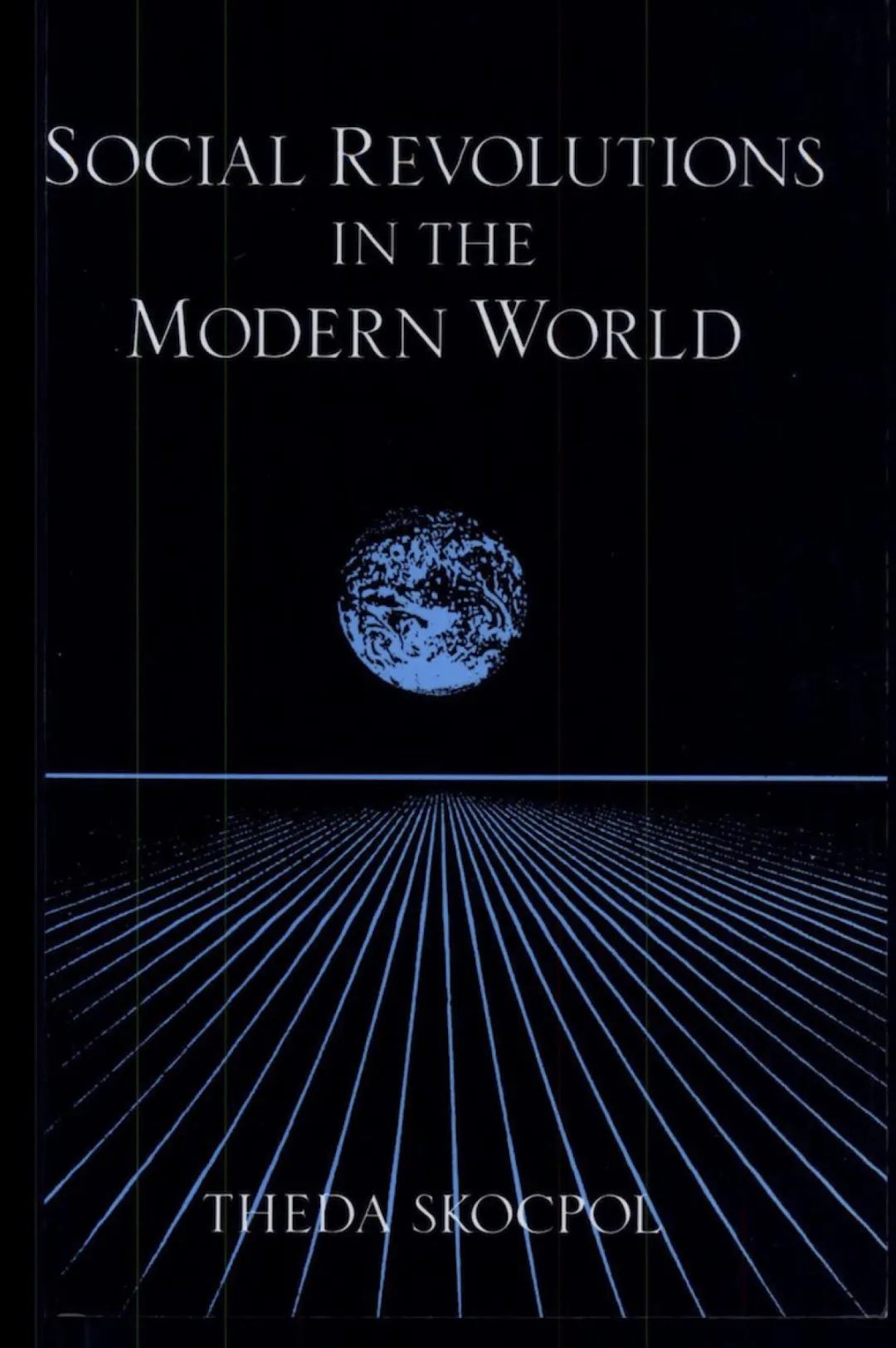
▴
Theda Skocpol《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 1994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1991年出版的《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史密斯介绍了十八位历史社会学家的思想及著作,并将上述学者大致分为三类,即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二者兼具的历史社会学家(典型的如查尔斯·蒂利)。蒂利是社会学领域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在蒂利去世之后,有评论说他最好的作品是《旺代:对1793年反革命的社会学分析》(The Vendé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1793)。此书最大的优点和特点是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学的研究和写作方法有机地融合至一起。以致于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说道,蒂利后来的作品再也没有超越这本书,他越来越关注宏观历史进程和概念化,而失去了处理一般与特殊之间“创造性张力”的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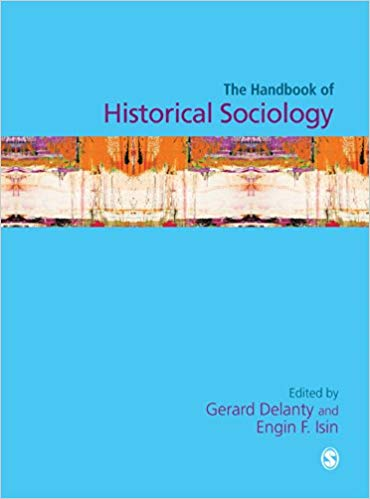
▴
Gerard Delanty and Engin F. Isin (eds.)《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在此,引发我们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本重要的历史社会学的概论性著作会收录这么多的历史学家?借鉴SAGE《历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的观点,李里峰老师认为,这大概说明了历史社会学存在两种发展脉络。其一是美国传统,旨在分析现代性的起源和转变,体现为宏大理论、比较分析和对解释的强调,将历史学著述用来服务于社会学目标,代表人物为蒂利、斯考切波、曼(Michael Mann)、沃勒斯坦等。其二是英国传统,保留了更多历史学的特色,呈现为更具经验性、与过去相连接的形式,也更具有阐释色彩,代表人物为汤普森、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这里提到的两种研究路径,显然正代表了通常所说的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分野。
随后,李里峰老师对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讨论。这种差异首先体现为共相与殊相的分野。对规律和模式的偏好,是几乎所有历史社会学著作的显著特征。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的前言中,对此做了非常直白的说明。他写道,该书旨在“运用社会学的概念,通过对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体系的比较分析,来对历史社会进行解析”,作者的目的不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或政权在时间上展开描述”,也不是“运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单一具体社会的历史”,而是“对可以在不同社会之中发现的一种共同类型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这种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发展的某些模式或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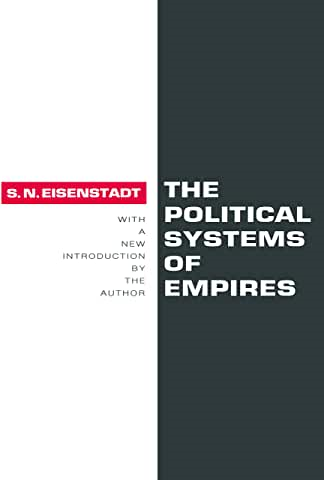
▴
Shmuel N. 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社会史家并不反对理论建构,但其概念和模式具有显著的历史性(特定时期)、差异性(特定社会)、有限性(特定目标)。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例,他大概是社会史家中借鉴社会科学意愿最强烈的一位,他明确主张历史学家去做“模式化”的工作,并强调他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使用模式。可他又表示,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同,“历史学家在处理一个模式时总是喜欢把它放到偶然事件中,使它漂浮起来,如同一艘船在时间的特殊水面上航行”。
其次,二者对“比较”方法运用的不同。历史社会学家的主旨不在于对历史本身的探究,而是要借助历史分析揭示现代社会及其各种特质(资本主义、理性化、民族国家、革命等)的起源和形成机制。绝大多数历史社会学著作所用的都是分析性比较,其目的在于“因果机制分析”和“历史类型学建构”,试图“从历史环境和历史先决条件中去解释或对一定的社会结构、体制、心态、辩论、时间、决策进行模式归纳”,从而更好地把握历史转折和变迁的原因,并从经验性比较中构建出具有解释力的历史模式。例如,艾森斯塔德对官僚帝国不同类型的比较,摩尔对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三种道路的比较,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的比较,都是如此。因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比较”便成了历史社会学的灵魂,甚至可以将历史社会学等同为“比较历史分析”(analysis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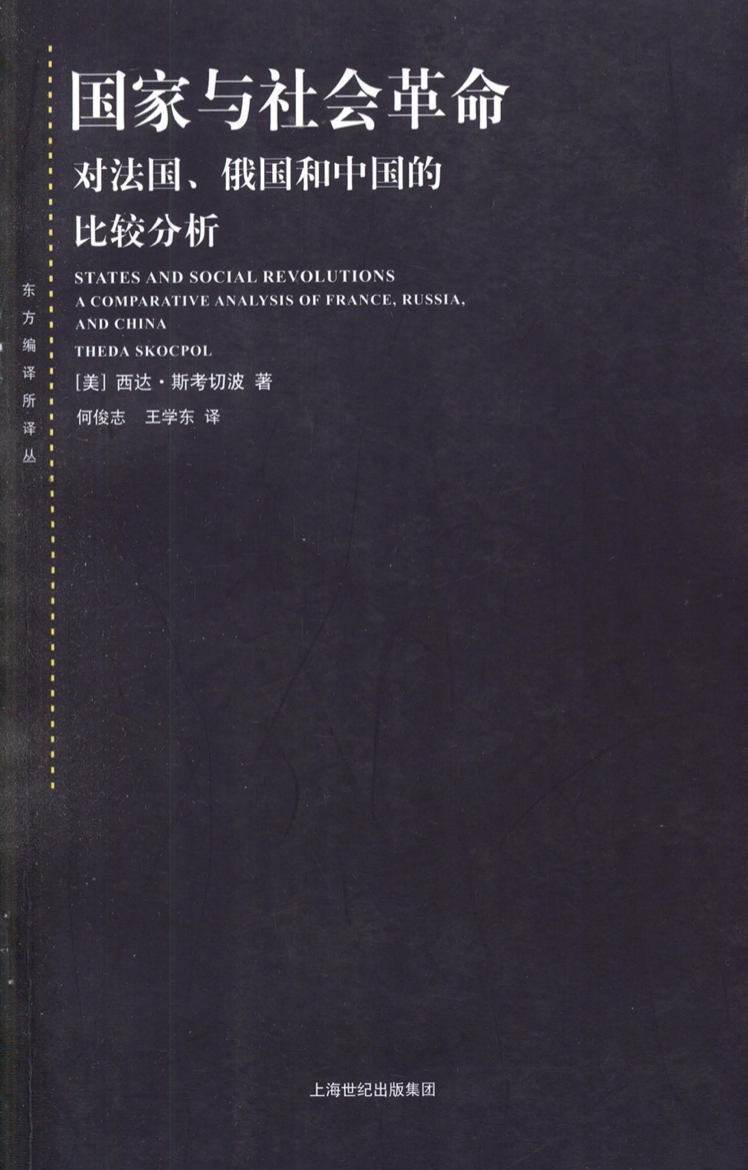
▴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何俊志,王学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社会史家当然也会采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在其研究中的目的和意义却大不相同。社会史家采用的比较方法,通常属于理解性比较,其目的不在于寻求“不同社会之间差异的解释”,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不同的社会,它们的独特性、特有的制度、心态和结构中的逻辑性”,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另外的社会,更好地接近它们”。以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为例,该书虽然采用了比较方法,但无论从结构还是篇幅来看,比较分析都不是其核心所在,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利用翔实的资料对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等诸多结构进行准确而深刻的剖析,其基本取向毋宁是综合的而非比较的。
最后,二者在资料使用上的不同。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能够全部或者主要使用第一手资料来探讨自己所选择的案例,实际上,绝大多数历史社会学研究都是借助二手研究文献完成的。斯考切波那本被誉为“革命起源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就是如此。作者采用结构化视角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进行比较历史分析,书中讨论中国旧制度和革命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但该书参考文献所列的大约180 种与中国有关的文献,几乎全都是用英文和法文撰写的研究性论著,全书没有使用任何中文资料。然而资料使用的缺陷丝毫没有影响这本书赢得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声誉,面世40年后仍被视为历史社会学的典范著作和比较革命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相比之下,历史学家要再现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特定事实,必须竭尽全力去搜求各种类型的第一手资料,所用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往往是和一部史著的价值成正比的。只要随便翻阅一下《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包括了多少原始档案资料和形形色色的其他史料,便不难想象一部经典史学著作“是怎样炼成的”。即便在资料上非常讨巧的社会史名著《蒙塔尤》,也是建立在内容极丰富而又非常系统的富尼埃审讯记录,以及同时代及稍晚时代的其他档案资料基础之上的。
尽管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分享着两个共同的关键词,但它们对于社会和历史(或时间)的理解很不一样。李老师指出,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社会概念首先意味着一种外在于个体并具有结构性和强制性特征的“社会事实”(这是社会学奠基者涂尔干赋予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个体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在特定的社会中扮演特定角色、发挥特定功能。另外,有趣的是,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理当关注历史中的社会,许多经典著作却把社会的对立面——国家——作为研究重点。艾森斯塔德对官僚帝国政治体系的研究、蒂利对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斯考切波对革命原因和后果的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国家中心论色彩。究其原因,恐怕仍然与历史社会学的主旨在于借助历史理解现代社会(而非历史本身)有关,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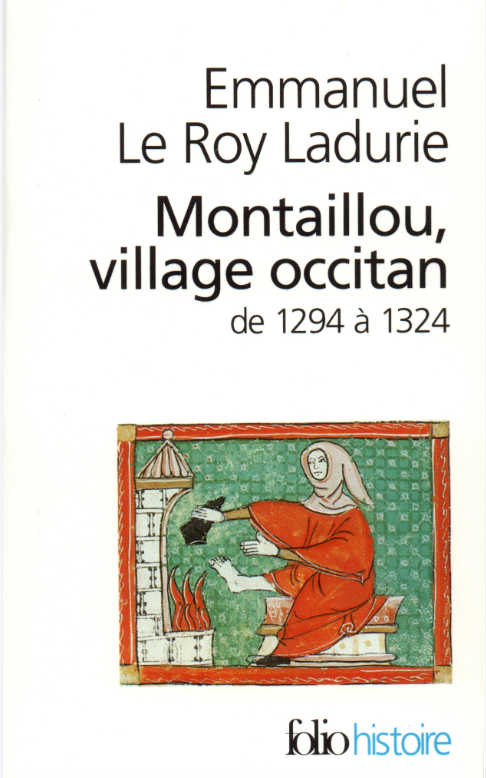
▴
Emmanuel Le Roy Ladurie《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Gallimard, 1982
社会史家关注的则往往是社会中的人,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群体)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区分。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史家对于社会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并无不同意见,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会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社会与个体的一致性,而不会过分执着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区分和对立。社会史是在对传统政治史进行质疑和反思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对政治、军事、外交等题材往往有一种拒斥心态,注重社会之于国家、民众之于精英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史早期曾一度被等同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而与以国家、政治、精英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划清界限。
不仅如此,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对于历史/时间的理解也有不同。历史社会学虽然以过去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旨趣却和关注当下的社会学家别无二致,主要是为了回答现代化/现代性何以并如何发生的问题。历史社会学旨在“关注现代性的形成和转型”,其学科定位在于“研究现在”,它“既为过去所塑造,又型塑着过去”。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历史/时间维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现代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时间首先是因果链条中的时间:一方面,要到过去的时间(time)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的起源(宏观因果机制);另一方面,重大社会变迁何以发生或何以如此发生(微观因果机制)也需要用特定的时机(timing)来解释。
对于社会史家来说,时间则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历史学家从来不能摆脱历史时间的问题:时间黏着他的思想,一如泥土黏着园丁的铁铲。”在社会史家那里,时间的意义不仅在于将眼光投向过去,还在于过去是绵延的而不是断裂的,是一条河流而不是一道峡谷。布罗代尔对三种“历史时间”的区分和实践,堪称历史学家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他在《地中海》这部巨著中将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类型,分别对应深层的地理时间(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中层的社会时间(群体和集团的历史)、表层的个人时间(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可见,历史学家(尤其社会史家)对于历史时间之复调性和延续性极为重视。
在此,李里峰老师将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差异性总结为以下四种维度:

即便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存在多个方面的差异,但二者仍然可以互相借鉴和交叉融合,实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美美与共”。从学科界定的依据来看,历史社会学又是和社会学的其他交叉或分支学科全然不同的。我们不能一般性地把历史社会学视为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或分支学科,其学科属性应该在历史学与社会学、历时性与共时性、差异性与规律性等多重的二维交互中去界定。
更重要的是,学科交叉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催生了历史社会学的繁荣,二者却无须也无法相互替代。站在不同学科领域的重叠区,或许《论语》所谓的“和而不同”,或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是更合理的态度。那么,对于历史社会学者来说,历史学和社会学究竟“美”在何处呢?李老师认为,历史学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坚持历史感和复杂性,社会学的优长之处则在于其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能力——这绝不是说历史学不用概念和理论,或者社会学没有时空观念,只是在比较中寻找二者的“美”点所在,以求得“美美与共”之效。
一方面,作为一门“时间的科学”,历史学最值得社会学家乃至社会科学家借鉴之处,便是对既有绵延又有变迁、既有惊涛骇浪又有深海暗流、多声部、多节奏的历史时间的准确把握,此即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历史感”。 简单说来,就是要具备“设身处地”的“移情”能力,而不能不加反思地“以今度古”。警惕发生非历史(ahistorical)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的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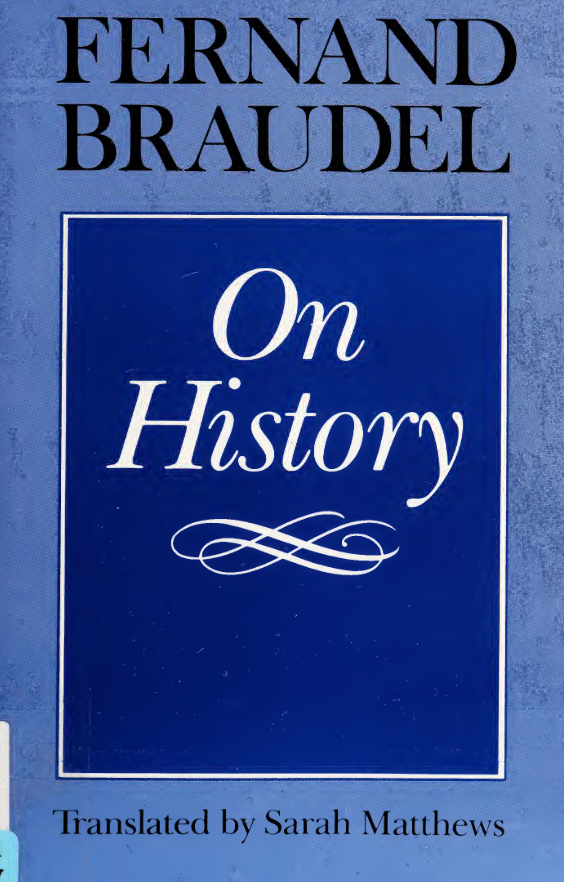
▴
Fernand Braudel《O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另一方面,在借鉴历史学、培养“历史感”的同时,历史社会学者又须坚守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通常所说的理论其实是一个意涵颇为宽泛和含混的概念,严格说来,应该对视角(perspective)、理论(theory)、方法(method)进行必要的区分。其一,每一种特定的视角都有其优势和盲区,只有把各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接近研究对象的本相。其二,社会学的理论有多种,在使用理论解释事务之时要时刻有理论自觉之心,警惕理论缺失的碎片化和理论过剩的同质化。其三,具体的方法和抽象的方法论都只是研究者所使用的工具,工具本身是没有好坏、高下之分的,只有合用与不合用之别。研究不能纠缠于方法论之辩,要走出“方法论强迫症”。
李老师最后总结道,社会学与历史学要相互借鉴,又要各司其职;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应该相得益彰,而无法相互替代。换言之,社会学和历史学均应坚守学科的基本定位,挖掘各自的长处,繁荣自己学科的同时,与其他学科共享优势。在此重温似乎已经过时的社会史研究,正是期待历史学和社会学能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为人类知识探索带来更多的灵感,实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美美与共”。

▴
李里峰老师在讲座现场
随后,讲座进入评议环节。郦菁老师首先展开评议,她对本次讲座进行两点补充。第一,根据朱丽叶·亚当斯(Julia Adams)等人编著的《重造现代性:政治学、史学和社会学》(Remaking Modernity:Politics,History,and Sociology)一书的观点,历史社会学至少有三个世代:马克思、韦伯等人被视为“第一波”,斯考切波、蒂利等人被视为“第二波”,朱丽叶·亚当斯、休厄尔等人则属于“第三波”。最重要的是,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思潮中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对于行动主体和历史或然性的关注逐渐取代了对于超级结构主义(hyper-structuralism)的迷恋,而对于事件和过程的重视则取代了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研究方法。
更具体地说,“第三波”从传统的有关现代社会形成与变迁的政治经济议题转向了文化,导致了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从对国家强制和制度权力的关注转向日常生活中毛细血管般权力的运用;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压抑和贬低的所谓“非理性”面向,如宗教、情感、习惯等,也在“第三波”重新复兴;最后,政治和经济精英之外的多元社会群体,如庶民(subaltern)、女性、LGBT 群体、少数族裔、非西方社会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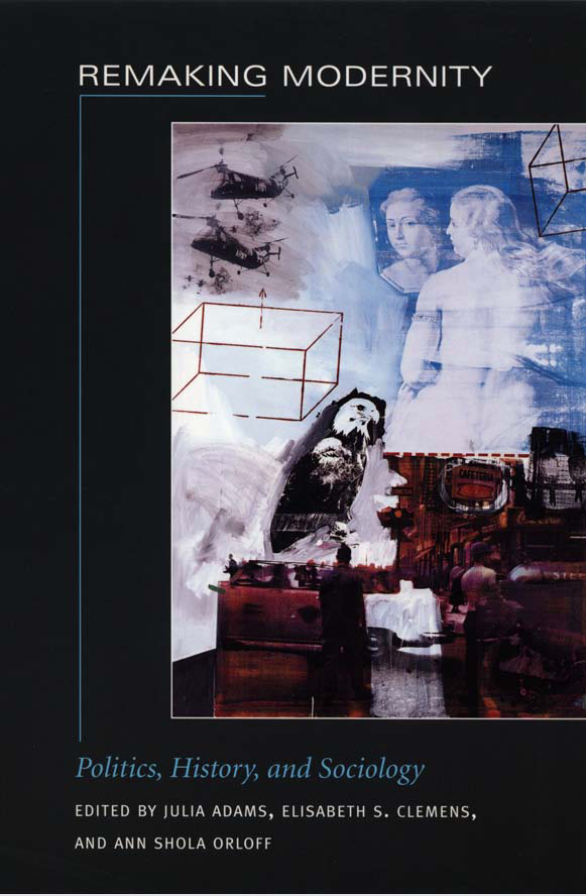
▴
Julia Adams, Elisabeth Clemens, Ann Shola Orloff《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5
第二,理解历史社会学内部出现的多元性,以及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两种学科对于历史不同的关照,要回到现代西方学术传统的发展史,或者说要回到现代性诞生的过程中来看待这一问题。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有着共同的发展起源,处理的均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再现和重塑。这两大学科在19世纪末开始分野,历史学开始更多地处理具体而多元的历史事实,抽象的历史法则在历史学家面前逐渐崩塌;而社会科学仍在坚持原来的道路。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兴起,它在面临历史学挑战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向历史学进行学习,愈发体现出二者不断纠缠和交融的复杂关系。像今天,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在边界上逐渐靠拢,当然,靠拢的过程中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分化。处于这一阶段、这一时代的学者如何处理和把握,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刘永华老师的评议主要围绕两点疑问展开。第一个疑问是关于“比较”的问题。在本次讲座中,“比较”不是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展开,更多的是在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之间展开。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对等的比较尺度和比较空间?例如,社会史中的“社会”和历史社会学中的“社会”,二者的概念内涵并不是一致的。社会史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对抗政治史、外交史而提出的一种新的领域和研究方法,所以社会史中的“社会”并非是社会系统意义上的“社会”这一内涵。而历史社会学中的“社会”,更多指向的是“社会体系”,包括了狭义上所说的社会和政治国家等内涵。

▴
讲座现场
第二个疑问集中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上。虽然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差别,但是经过20世纪两大学科之间种种的接触和摸索,两者之间的界限,至少从历史学的立场来讲上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主线索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历史学者并未完全放弃概念化的努力,像汤普森(如“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霍布斯鲍姆(如“社会性盗匪”/social banditry)、黄宗智(如提出的“第三领域”“没有发展的增长”“集权的简约治理”等理论化概念)等人,都鲜明体现出了这一动向。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考察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并与之展开对话。
李里峰老师作出以下回应。首先,李老师表示自己的研究主要以“第二波”的历史社会学家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考虑到这一波的学者产生了一大批的经典作品和经典理论,代表了社会大众及学界对于历史社会学的固有印象,而“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还处于理念发展和研究设想的阶段,能否产生像斯考切波、巴林顿·摩尔所著的经典作品,值得期待和观察。其次,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起源、发展和变化,的确需要回到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中去做考察,以此来审视两者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趋势和样态。再次,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虽然共享了某些相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但其中特定的内涵(如历史社会学中的“社会”与社会史的“社会”)需要再做明晰的界定。最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需要概念化,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但历史学的概念化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化仍是不同的,简要来说,历史学更多是一种有限的概念化,富有时间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