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三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天可汗及其时代——初盛唐的经籍、文学与历史”,从文献典籍、文学、思想、艺术、历史等跨学科多重角度,重新审视初唐之诸面相。论坛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论坛召集人为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副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程苏东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副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副教授等学者先后参与讨论。

邓小南院长介绍了文研院情况,认为此次本次讨论的议题从经籍、文学等角度重新审视“天可汗”形象,具有开阔的讨论空间。文研院愿意全力类似活动,鼓励沉潜、个性,营造健康纯净的学术风气。

孙少华老师以“《贞观政要》与初唐文本书写问题刍议”为题,根据《贞观政要》的文本书写,指出文本研究不能单纯留意文本的文字歧异,还要关注“人”在文本中的作用。他强调,事实上,所有的文本都出自“人”的制作或改变,也都由“人”来阅读、接受或传播,必然造成文本内容与形式的千变万化。其中,文本的编纂者或书写者对文本的作用最大,他们对文本的“特殊用心”,决定着文本的性质、功能、目的、意义,甚至左右着文本材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程度,如唐太宗亲自审阅当代国史,就对史书文本的书写者有一定的心理干预作用。同时,纸质文本将“事件”局限在“一个”维度里面,而无法呈现多维的历史动态变化。在文本设计上,《贞观政要》也以“德行”为先,而不甚重视“文学”,甚至或有不合史实之处,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秩序,探索出一个符合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理想的教育、文化、经济、军事管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单纯从“文本”角度苛求编纂者遵守历史的真实,而应该对其“文本编纂用心”或“文本写作用心”予以特别的尊重。借助文本“义在惩劝”的功能,为构建一个合理、公平的社会秩序提供历史经验,则是中国历代文本书写者的共同理想。在此,个人命运屈从于国家、社会的需要,“历史真相”让位于“公平正义”,成为文本的“道义真实”。

程苏东老师以“从‘定本’到‘正义’:帝国文本与文本帝国”为题,讨论了《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从“帝国文本”到“文本帝国”的巨大反差。“帝国文本”,与“圣人文本”、“私人文本”相对(谷口洋语),是指那些展现国家意识形态、并以其存在本身宣示帝国形态的文本,这可以追溯到《诗》、《书》。《吕氏春秋》就是初具规模的“帝国文本”,其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旨在改变秦“无文”的文化局面。这一类“帝国文本”,将现实世界中的时间、空间转化为一种文本结构,从而将现实中的各种知识、思想收纳到这一充满秩序感的文本结构中,森严的体例结构把各方面的“碎片”整体化了。一方面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国人均有机会参与文本的编定;但另一方面在文本编定之后,就如同国家的各项制度一样,不可更易,“永为定式”。唐人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了出色成就,也需要通过“帝国文本”的编纂来彰显帝国的复兴和权力的有效性,“定本”与“正义”都堪称初唐的“帝国文本”,“一元化”或许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一反汉晋以来的多元师法,唐太宗在经目确定上选择了一元化的师法体系,《五经正义》的编纂及其“疏不破注”的原则使得唐太宗的文化统治更显精细化、标准化和单一化。当视角从“帝国文本”转向“文本帝国”的时候,便会发现这些外面看来恢弘气派的“文本帝国”并未达到编纂者的意图。“定本”虽然经过严格的程序勘定、颁布,但成效难以令人满意,更受关注的《五经正义》其文本内部的失序、错讹同样不容忽视。“文本帝国”与“帝国文本”的巨大反差,可以归因于唐太宗对于“君权”的过度自信而忽视了经学史自身的复杂传统、写钞本时代文本书写、传播的基本特点和衍生型文本在生成过程中隐含的巨大风险。

仇鹿鸣老师以“怀柔远人:出土墓志所见入唐吐谷浑、吐蕃家族”为题,就出土的归附唐廷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家族墓志及吐蕃将领论氏家族墓志为例进行讨论。首先他指出,唐帝国北方敌人突厥、回纥等都逃不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宿命,真正对唐帝国构成长期挑战的外族政权是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吐蕃对唐长时间、持续的威胁,与其并非是纯粹的游牧帝国有关。由慕容家族的墓志,可以看出吐谷浑王族归唐以后,基本上仍然集中在灵武一带,但从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演变为以附塞部落形式存在;唐王朝对吐谷浑王族长期采用和亲策略,这一和亲在武氏时代仍在延续。同时,还发现慕容氏有与汉人士族的婚姻,但不符合当时的通婚规则,可能与皇帝赐婚有关系。结合新近发现的《论惟贞墓志》和之前的研究,可以作一些补充。论氏出自吐蕃噶尔家族,其先为主导与唐廷争夺吐谷浑的关键人物——松赞干布时期名将禄东赞。其子钦陵继任为大论,长期经营原吐谷浑故地,后招致吐蕃赞普器弩悉弄猜忌而被杀,其子论弓仁率部下投唐。论氏投唐之后,率领的吐谷浑部落七千余帐,反映了其家族对于吐谷浑故地的长期经营。投唐之后其维持部落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了玄宗后期,在安史之乱战争中原有部落被逐渐打散。

耿朔老师以“天可汗的纪念碑:略谈昭陵六骏和十四蕃君长像”为题,从视觉形式角度对其进行讨论。首先他指出,唐昭陵所立的六骏为太宗身前征战四方所骑,图形刻石全过程来自太宗的授意,后者虽是在太宗归西后所立,但记录的是贞观年间周边邦国君长“擒伏归化”重大事件,二者都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与主要体现朝代特征的绝大多数陵墓石刻不同,昭陵的石刻可以被看作是天可汗个人功业的纪念碑,与贞观朝的政治特征和唐太宗本人的政治意图关系密切。六骏和十四蕃君长像被陈放于北司马院南部两侧廊房之中,谒陵者需入内近观方可明辨。人物圆雕通过五官、发饰、服饰展现个性,并借助题名予以提示,也不同于一般石刻对文臣武将的概念化表现。他强调,理念或文本到视觉形象的转化过程也值得探讨,就十四蕃君长像而论,有些君长未曾来过长安,可获取到的信息相当不均衡;也不是截取一个真实的时间断面,而是刻意将年龄差别很大的十四人在外形上塑造出彼此“和谐”的效果。六骏采用高浮雕形式,在技术上也有着合理性:相比线刻能生动体现战马身体的立体感,并能表现透视,如果用圆雕的话,对动作幅度较大的作品来说,非直立的马腿将无法支撑上方石材的重量。此外,太宗为六骏刊石意在“为镌真形”,但六骏中什伐赤、青骓和白蹄乌所做四足腾空状并非马奔跑中的常态,不是来自对现实中奔马的真实观察,而是一种精彩的艺术表现。

徐建委老师以《汉书注》、《文选注》为例,讨论了初唐注释的二次整理问题。他指出,李善《文选注》引书多达1607种(清汪师韩语),以当时物质文本的流传状况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记载,其很难备齐他所需的千余种古书,甚至有些在当时已经失传。《史记》三家注、《汉书注》同样引书宏富。这些集注,都是在前代储备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一个二次整理的过程。一是参据前代的注疏,如东晋蔡谟的《汉书注》。这个注本成为了后来《史记》注、《汉书》注、《文选》注甚至《水经注》的重要知识资源,属于颜师古等人的“原创性”注释并不很多。在涉及《汉书》相关部分时,《史记集解》、《文选注》等大书,也几乎抄录蔡谟注本。由于唐代流行的集注本往往都是晋人注本,故而唐人集注多引晋以前古注,基于此可对唐初文本生产方式深入讨论。第二,这些集注的编纂还参据了类书。如《齐民要术》引《隋志》未录书四十余种,这些书几乎全部见于《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史记正义》所引唐前已佚地志书籍也应当源自类书而非地志总汇。此外还可参据通行的单一注本。这都是唐以前制作集注的便捷之途,实质上是一种古注的二次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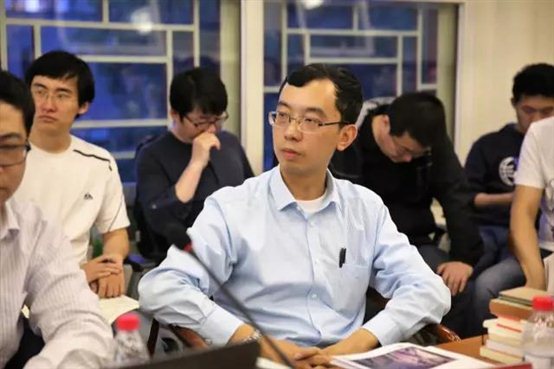
童岭老师以“天可汗的光与影”为题,讨论了读谷川道雄著作《唐の太宗》(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年版)的一些体会。首先,他介绍了谷川道雄的生平著作、京都学派的学术思想。《唐太宗》是宫崎市定监修的“中国人物丛书”第二期12本中的一种,这一系列两期共24本,大多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执笔者多为京都学派的中坚学者。这也是谷川的第一本“少作”,可以用于理解其学术思想之缘起和演变轨迹。谷川探求唐帝国形成轨迹的努力,在此书中也有所体现。书中的起点是“被背叛的青春”(唐太宗16岁时,隋炀帝于雁门被围),在第一章第三节从“六镇之乱”剖析了唐帝国的远流,这种长线条的做法也是京都学派的传统。谷川道雄认为“所谓唐宋变化,本质上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研究具体的人是从《唐太宗》到《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以贯之的思路。此外,虽在此时,谷川道雄与川胜义雄联合倡导的“六朝贵族制”鼎盛期尚未到来,但其对比“隋炀帝的低劣与他们的崇高”,对坚持不降唐,最后为降唐的部将所杀的尧君素的推崇,标举这样独立与君王之外的人间大义,可以说是他今后“中世共同体”理论的先导。同样对于“义”的存在,其笔下对窦建德也十分推崇,这或许也有日本武士精神的影子。在叙述李世民时,谷川赞许其性格中的“智而不奸”,跳出常规的李世民魏征君臣相得的视角,重点分析“天子无私”的概念,也可看到“共同体”的影子。在第八至九章,谷川描写了“天可汗”光辉之下的“阴影”,贯穿了其“完整人间相”的构思。



